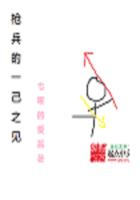那时候村北有一条河,暑假的日子里,我们出来割草全是围着小河转,忙乎一上午,出一身臭汗,割一大篮子草交到生产队里喂牛,十几斤草才能换一分工分。我和小伙伴们热了就会脱的光光的下水游会泳,有时一个下午要下三、四次水。
女孩子割草有时也愿到河边来,热了蹲在河边洗一把脸,在河水不深的地方,卷起裤腿下水降降温。坝里的水清澈透底,看着很浅,下去一不小心就湿了裤腿。
我们男孩子最不愿看到女孩子到河边来,有时刚从水里爬上来,有时把身上的水才凉干,一支腿已伸进了短裤里,发现有女孩子从附近的庄稼地里出来,害怕的不是她们,倒是我们,没穿衣服的还好说,吱的一声钻进了水里,正把一只腿伸进短裤的,越着急越穿不上,没办法,只能慌慌张张的脱掉短裤,重新跳回到水里去。
平常里女孩子也是不敢随便得罪的,她们要是说一句:开学后我告诉老师去,你们天天去洗澡。男孩子会害怕好几天,因为老师知道了真会罚你站的。大部分女孩子只是说说,到开学时早把自己说过的话忘掉了。
随着下水次数的增多,我们游泳的水平也越来越高,胆子也越来越大。有时想到河对面去,就把衣服放到篮子里,把篮子顶在头上,用两只手轮换扶着,向对岸游,这时两只脚摆动的频率要比平时高好几倍,游一段距离后觉得手累了,就只用两只脚活动,这叫踩水,整个身子几乎是直立在水中的。河的最宽处要有四、五百米,游到中间最害怕的是腿部抽筋,要是真抽筋了,游不动了,人就会沉到有好几米深的水底去,别的伙伴想救也救不了你。快到对岸时,每个人的力气都用的差不多了,篮子里的衣服湿就湿一点吧,活命要紧。有先游上岸的,看后边的实在不行了,就赶紧回头去帮一把。等都上岸了,大家会坐在岸边喘好大一会粗气。
河边有水分,河边总有我们割不完的青草。每当割草累了还是玩累了,我们就会静静的坐在河边,望着蓝蓝的天空,想象山外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每次回到故乡,望着已干涸了十多年的河底,我想念小河,怀念小时和伙伴们一起在河边度过的日子。悠悠父子情那天母亲把从部队回来的我和妻儿迎进家门,刚放下行李,我就问,爹呢?娘说,到地里干活去了。我说,我去喊爹。妻说,我跟你一起去。儿子叫,我也去。母亲锁了门也跟了来。我们拉着家常来到地头,望着在地里忙碌的父亲,我喊了几声爹,竟无反应,我让儿子喊爷爷,仍然没有作用。娘说,你爹耳朵背了,听不见。我含着泪向父亲走去。这时在地里干活的一个老乡对父亲说,有人叫你。爹停了手里的活,向地头这边看了看,收起一把翻下的断秧子,向我走来。我迎上去又喊了一声爹,双手抱住父亲的胳膊,眼泪流满了脸颊。天哪,怎会是这样,父亲的脸上满是老年斑,头发几乎全白了,背也有些驼了。父亲说,真没想到,你们回来,走,咱们回家。我想接过父亲手里的锄头,他不肯给,我强夺过来,扛在肩上。走到地头,妻子喊爹,儿子喊爷爷。父亲一一答应后问儿子,你们都回来了,你爸爸怎么没回来?我心酸地咬住嘴唇,但眼泪还是不听使唤地流了出来。弟弟也是军人,也在我所在的城市里服役。母亲说,看,你爹耳朵不行了,眼也花了,我在家忙着时让他拿点东西总是拿错,说话也是你说东他说西。母亲比父亲小几岁,虽然身体也很虚弱,但看上去气色比父亲好些。
一路上我一直抱着父亲的胳膊不肯放。就是这双胳膊这付肩头,抗日战争中扛过枪,拼过刺刀。父亲当过八路军,在枪林弹雨中拣回一条命。
父亲曾当过十几年生产队长,我记得唯一沾的公家光,就是用从生产队会计那儿拿来的用完的桨糊瓶做了两个煤油灯瓶,一个扁的,一个圆的。我曾端着那个扁的到村东的破庙里上过晚自习。那时候在队里干活的父亲样样都走在别人的前面。在一个工才值一毛多钱的岁月里,收工后父亲叫上二姐和我到山上去割草,回来晒干后,冬天每一百斤卖五元钱,那是姐和我的学费及全家整个冬春的盐钱。
我还记得老家的那几间老屋,怕的就是夏天的连阴雨,父母把家里大大小小的盆盆罐罐都摆出来还不够用。那雨滴敲击各种盆罐的声音像首感伤的曲子,唱的让人心碎。
我更记得我高中毕业后,跟人出外干石匠活拉石头,晚上收工时已是八、九点钟,独自再走十多里路回家。早晨五点,鸡刚打头遍鸣,父亲起来背上干粮袋子送我一程。
父亲像一盏明灯照亮我成长的足迹,二十多年的军旅生涯,我所得到的每枚军功章里都溶有父亲的心血。
进了家门,洗了把手坐下,我忙掏出烟给爹点上。爹深深吸了两口,突然睁着昏花的眼睛看着穿军装的我说,你们回来了,你哥怎没回来?娘说,你看,你爹还没认出你是谁来。我又一次泪流满面。我呆呆地站在那儿,望着苍老有些木讷的父亲,任咸咸的泪水流进口中,流进脖子,流进心里。
父亲,过去,您是一座山,是全家人的依靠;现在,您依然是一座山,是儿女们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