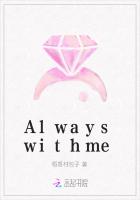辛亥革命以后,天一阁藏书大量失窃,其经过情形,陈乃乾《上海书林梦忆录》记载颇详,文章说:“民国三年,有乡人冯某串同党徒夤夜越墙而入,窃出书籍千册,陆续运带至沪。”其中一部分售于六艺书局,“每册仅二角许,后散售于藏书之家”。此外,大部分售于来青阁书肆,来青阁又转售于食旧廛书肆。这批书籍正打算寄往日本,不久事发,“遂归乌程蒋氏,得价八千元”。商务印书馆曾搜集了四五百种,放在涵芬楼,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不幸又遭日机轰炸焚毁。
当初,窃贼从屋顶挖去瓦片及椽子,潜入阁中,历时数十日,范氏子弟竟未觉察。过了三个月,学者缪荃孙得知消息,急驰函范氏究其事。涉讼经年,冯某及窃贼薛继渭虽已捕获,但被窃书籍无法追回。当年在上海设书肆的罗振常,曾就个人目睹之书撰为提要,成《天一阁藏书所见录》一册,记有二百四十种之多。
事后,缪荃孙编有《天一阁失窃书目》二册,记录失窃书一千七百五十九种(其中科举录四百七十四种),并在序文中讲到此次失窃书籍的经过。从失窃书目的编制体例来看,他是以薛目为底本,对照阁中劫余存书,然后把未对到的一一抄录下来,所以其顺序完全和薛目一样,甚至连各类的统计数字,往往也照薛目抄了下来,时间匆促,失误颇多。例如被列入目录的三十一种明代地方志中就有《建阳县志》等七种,并没有失窃;四百七十四种科举录中,也有三百二十八种不曾被窃。所以,缪目只能作为一个参考。
此次浩窃之后,天一阁存书情况,可以从下列三种书目中得到反映。
一九二八年,林集虚编《目睹天一阁书录》四卷附编一卷。卷首缘起云:“阁中之书被窃,当时范氏后人将存书目用红圈标识,除登科录、乡试录外,所存不过八百种。”林集虚于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日登阁,以十天为期,在吴文莹等三人帮助下,匆促成书,故遗漏较多,又迁延十载,才用木活字排印行世。书目仍分经、史、子、集四部。对于书籍的版本,包括刻抄本、时代、年号、行格、牌子、刻工、装订、钞补、脱页、书纸种类、藏书印记等,记载比较详细。卷末附编,首次记载了天一阁的匾额、联语、禁牌规例等。
一九三〇年,杨铁夫等根据当时宁波地方政府的意见,重编《宁波范氏天一阁图书目录》。范氏例规,非合各房人氏,不能登楼,又因“陪伴同查,致碍生计”。所以,当时以一日为限。卷首杨铁夫序云:“时虽迫促,大体已自了如,合计范氏自行清理所写目,当不大谬,通计为书九百六十二种,共七千九百七十一册(各省试录未计),比薛目约得二分之一,其中完璧者尚有三百一十种,比薛目约得四分之一,然全者多属数册,至册数愈多,其存者愈少,有百数十册,止存一二册者,故种数似有可观,而册数实属无几。”“此外,碑拓本一无所存,石刻十余具尚无恙,《图书集成》尚存四千零七十四册,约得原书之半”。可知,自光绪十年薛福成编目以来四十多年间,藏书又散佚过半。
杨目为油印本一册。一九三二年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丛刊在发表陈登原《天一阁藏书考》一文时,将此目作为附录铅印,所以至今流传较广。因编目时仅仅花了一天时间,动员四五个人依照书籍的牙签抄录,除记录书名册数外,别无著录,所以分类杂乱,错误百出。
一九三五年冯贞群登阁编目,历时六月,于次年三月完成初稿,一九四〇年铅印问世,称《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他在范氏子孙范盈藻等人的协助下,“整理残编断简,拂尘去蠹,聚散为整”,记载了当时天一阁的全部藏书,甚至连仅存数页不复成册的也加以记录。《内编》刊印前,鄞县开文献展览会,于一九三六年选印了《方志目》和《明代试士录目》各一卷,称《天一阁简目两种》。
冯目共十卷,依四部分类,前四卷记明代及明以前旧本一千五百九十一部,计一万三千零三十八卷,卷五收录清初以来书本二百十四部。《古今图书集成》八千三百二十卷,卷六至末卷为附录及补遗,包括图像、书影、志传、额联、碑石目等等。冯目编成以后,藏书稍有散出,主要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书籍运至龙泉的往返途中失散,计明刻本八部,清刻本四部。冯目在解放以后的一段时间内,仍然起着现存书目的作用。
此外,一九三三年赵万里先生为重编天一阁书目,于七月二十五日登阁观书。他在《重整范氏天一阁藏书纪略》中说,当时以一星期为限,“用预定的一种较精密的统计法。无论行款、边口、版心大小,属于机械方面的,固非一一记载不可,就是序跋和内容的特点,也得在极短时期内缩写下来,以便日后作书志时参考。……这一个重整天一阁现存书目,我预备叫它作内篇。此外,还有一个外篇,附在内篇之后。外篇是将历次散落在阁外的书,作一次总结账”。一九六一年,赵先生函告笔者,此目当时未曾完稿,所抄录的原始资料,在抗日战争时期已散佚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