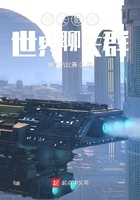梦蝶冷不丁的身子一掬连,脸骤然冷落下来,铁青得瘆人,“二哥,你为啥不问问我这些年咋活下来的呢?我为啥在这噶达这个样子呢?” 吉增正色地说:“是啊,俺哪倒出空儿问了?对呀,你一会儿一出的,差劈的像变戏法似的。摇身一变,由光巴出溜的野人娘们变成了金凤凰,这未免像神话似的太离奇了吧?俺心里是画个魂儿,可还没等俺画完呢俺的魂就让你牵萦绕到花灯红烛的极乐天堂了,俺还咋问你吧?” 梦蝶掖巴套上衣裳,两腿蹬进裤筒,系好丝带,陡然起身,双手掐腰,凝眸飞射威严寒光,俨然尤如穆桂英转世,花木兰再现,一身豪气凛然,“二哥,我实话告诉你吧!朱大嘞嘞心怀祸心,要加害于你?他见利忘义,图财害命,串通魁三,要想在你接货之时‘插了’你,然后掩尸灭迹,分赃肥己。” 吉增赫然得出了一身白毛汗,浑身起满的鸡皮疙瘩都掉渣儿,嗔嗔地拿眼仁盯着梦蝶,阙疑发狠,“耸人听闻,不可能?俺俩多年的哥们交情,他咋能做出这种草菅人命的事儿来呢?梦蝶咱俩‘露水夫妻’一场,你别编派瞎话蒙骗俺?俺可不是小米粥堆的,苞米面捏的,狗熊揍的。你还记得小四儿吧,他睡了你还当俺面卖谝,俺废了他,让他终身断子绝孙,还得养活别人揍的孩子,受王八气。你听明白了吧?” 这梦蝶也叫粉莲,大牌花名,就是吉增钟爱的小杏。梦蝶急了,“二哥!你听我说个来龙去脉,我就不信你不信?咱长话短说,兔子找尾巴掐。我装疯卖傻逃出回春堂,笼络些对我这个大牌痒痒,而又处心积虑靠不上前儿的穷光棍儿,叫他们尝到甜头,死心塌地顶礼膜拜我,虔诚的孝敬我,纠集三十几号人树绺子,我做了山大王,当上了大寨主,道上号称雪上飘,外号画眉鸟,道外人赠送的雅号叫女魔头。多条钢枪一盘磨,众星捧月似的,好不快活。我养精蓄锐,敛财买枪,立志报仇雪恨,洗刷我的耻辱。我就盯上了来钱最快,赚头最大的黑货,‘别梁’后,捣腾到上江一带,再咕倒回枪支弹药啥的。我利用美色,屡屡得手,也有马失前蹄。我屡踣(bó)屡起,拼打出一番天地。魁三儿贩大烟土可是个行家老手,道行深遂,我有时也羼入其中。魁三儿倒也买我的账,逗些嘎麻的。这回我正和魁三儿鬼混,偶听大嘞嘞和魁三儿的谈话,才知二哥你搀和其中。我就一番乔装打扮,试探你对我的心境,如你一见如故,不嫌弃我,我就救你。如你不搭稀我,厌恶我,我就兴风作浪,顺水推舟,送你回山东黄县老家。这也是我复仇的一个步骤。凡是睡过我的,忘恩负义,我就废了他?当你把一包牛肉递给我那一刹,我的泪水就止不住了,决心救你。我回绺子上做了一番安排,返回阻止你和大嘞嘞一道上三星观。你倒奸个透顶,压根儿就没想去,这正中我的下怀,一恕衷肠,又能保全你的性命。我这回是要黑吃黑,一勺烩,连锅端,‘插了’不仁不义的大嘞嘞。” 吉增忙阻止,“大嘞嘞他不仁咱不能不义,拖孩带崽儿的一大家人家,他鳖咕了,可咋整?” 梦蝶怒不可恶,不憷地说:“他这叫咎由自取,罪该应得!二哥你叫啥人呐,没做成野鬼冤魂呐?人有你这样的吗,你给我快走!大嘞嘞这个害群之马,祸害星一个,不除对不起你对我的一片真情厚意,不除不知还有多少人成了冤死鬼?你走,不走就来不及了?你也不要再找我,做完这个活,我也要挪窝打那万恶的小鬼子去了。为了摘清你的身儿,不让魁三儿和官府往后找你的麻烦,纠缠不清,我已安排手下的崽子,在大嘞嘞身上留下标记。这儿,用不了五更天儿,魁三儿就会找上门来。好!我先走,咱们后会有期。” 梦蝶说完,忍痛割爱,头也不回地跑出地窝子。
吉增紧追两步,梦蝶早已消逝在黑幕中了。
吉增一下悬了空,又悲又憷,感叹人生没定数。返回地窝子,抓起酒坛子,咕咕地喝个底朝天,然后嗷嗷的狂嚎几声,一屁股排在地上。昏昏沉沉中,嗅到一股强烈的烟火味,熏得他立马清醒过来,搂起钱袋,冲出熊熊烈焰的地窝子。吉增上马,看见几个黑影在树林子里一蹿就不见了。吉增慌不择路,可老马识途,照原路返回。
到了桥头,一彪人马打着火把,早等候于此了。周大掌柜先开了腔,“我说姑爷你咋整的,送点儿皮货起五更爬半夜的,多让家人惦记呀?这还多亏了徐排长,要还不知你打哪旮儿走的呢?瞅你喝的,都成一摊泥了。” 吉增惊愕地睁大眼睛,迷惑不解地刚要发问。周大掌柜向徐排长拱拱手,“徐排长多谢了。改日我做东,八仙居见。姑爷快走吧,小胖儿吵吵的遥哪找爹爹呢。” 周大掌柜一路沉默无语,吉增也没敢多言,只感觉有些蹊跷。
到了家门,吉增一见铁将军把门,心里有些凉快,回头问周大掌柜,“爹,美娃咋没回来,住你那哈了?” 周大掌柜下了马,等吉增打开锁,吩咐伙计回去,留下三个侄儿,跟吉增进了屋。吉增放下钱袋子,嬉皮笑脸地说:“收点儿陈账。嘿嘿。” 周大掌柜拎拎钱袋子,阴阳怪气儿的说:“嗬,挺有货呀?一回就收回万巴块的大洋,你挺趁的呀你?我正缺钱用,先串换给我,我付你一分利钱,出手够大方吧?我瞅你那铺子也用不着啥钱了,狗皮帽子山羊皮啥的,都挺精巧的,精品呐!再加上你会弄外捞,富可敌国了呀!你小子唉,出息大发了,敢在我面前撒谎撂屁了?我问你,你今儿个到底干啥去了?说真话,别扒瞎?” 吉增听出周大掌柜的冷嘲热讽的不善之言,搓搓手,摸摸后脑勺,装糊涂地说:“要账吗嘛!爹你要缺钱,拿去!咱翁婿俩有啥说的,啥利不利的呀,咱谁跟谁呢,俺不再乎?爹,你也太小瞧你姑爷了,你姑爷多暂那样小气过?再说了,俺还欠你的钱呢。” 周大掌柜嗬嗬了声说:“小子唉,还冠冕堂皇的骗我啊?你还跟我装蒜呐?你还真把自个儿当棵葱了?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见真佛不磕头啊?还得我点拨点拨你吗?” 吉增很委屈的样子,“爹,你说的意思俺还真的听不懂?不过,俺想倒出空咱们再好好唠唠。俺得把美娃和小胖儿接回来,不知咋的心里老闹巴蹬的,好像有啥事儿似的,呢呐!” 周大掌柜伸巴掌就要打,“我看你小子就是欠削,还执迷不悟……”
“大掌柜!大掌柜。” 周大炮慌三惶四的进了屋,气喘吁吁的说:“没用咱们动手,大嘞嘞,还有十了个魁三儿的人,不到一袋烟功夫,就叫一伙蟊贼给咔喳了。黑货,也劫走了。” 周大掌柜高兴的叫了声“好”,冲着低头的吉增说:“小子,你听见了吧?算你奸,也亏了梦蝶这个****,救了你一条小命。你还死硬不了?哎,周大炮,你估摸这是哪伙人干的呢?是不是黑吃黑呀?” 周大炮看了眼垂头丧气的吉增,不含乎地说:“可不咋的。听他们馇咕话,好像雪上飘的人。舵把子叫画眉鸟,女魔头嘛!” 周大掌柜冷眼扫了下吉增,“啊,这就对上了茬口了,杀人越货。你说梦蝶这个瓦子娘们,当姐儿那会儿多柔顺个人儿呀,不知勾去多少爷们的魂儿?别说,当了胡子还真的镇唬一阵子,这都是世道逼的。不过,她入道不深,凡心不改呀?对老相好还是有情有意的。都那时候了,还不忘了老本行,放骚!妈的,早晚逮死那上头?”
吉增此时此刻那心呐,火烧火燎的,五脏六腑就跟架到大火炉上烤似的难受。那脸臊得像紫茄子似的呼呼冒火,有个地缝就想钻进去。完了,啥事儿都没瞒过千里眼顺风耳的老泰山呐,吓,火眼金睛!老丈人你呀神掐妙算,嘎咕的很呐!让老丈眼子抓个现行,那还会有好?还有啥说的,等着挨……扑嗵,腿一软,“爹!爹!” 磕头如捣蒜,哭嚎的认错,“俺、俺错啦俺?俺错啦!您老别拿你的女婿俺当人,也别憋着,该骂就骂,愿打就打,出出气,解解恨!” 周大掌柜攥得手指头嘎嘎的响,踱了踱,狠狠地下决心,“揍他个熊玩意儿!”周大掌柜斩钉截铁的话音刚落地,他的几个侄子就冲上去拽起吉增,按到炕沿边上,扒下裤子,拿起笤帚疙瘩,照吉增肥肥胖胖的屁股劈劈叭叭打开了。眨眼儿功夫,屁股蛋子就被打得红肿菖了起来,足足有发面饼那么高。吉增咬着牙没有吭一声。周大掌柜一挥手,“行了!你小子还有没有记性了?走,背上钱袋子。”
吉增挨老丈人一顿揍,那种负罪感减轻了不老少,心里轻松了许多。一大早爬起来,屁股肿肿的还疼得钻心。心里琢磨,这事儿会是美娃下的舌吗?美娃咋会知道的呢?美娃不会的。俺一点儿蛛丝马迹也没在美娃面前露过,一定是老丈人听谁说啥了,背着美娃搞的鬼。不管咋说,得把美娃接回来。吉增没敢骑马,也没叫人力车,一拐一拧的朝老周家挨。
半道上,碰见了那婶。那婶见了吉增想躲闪已躲不开了,拧搭地硬着头皮,强挤颜笑,“是姑爷啊,上哪旮儿去呀?美娃好些没有啊?” 吉增没捋会儿,“哦,那婶呀。这不美娃回娘住了一宿,俺去接她娘俩回来。那婶,你这是干啥去呀一大早的。”
“啊?你、你还不知道美娃出事儿了?”
“美娃,美娃出啥事儿?不在娘家待的好好的吗,能出啥事儿?”
“姑爷呀,要说这事儿可寸了,也不怪你那大哥?美娃被你那大哥马车撞了一下,不碍事儿,住两天医院就好了。你那大哥心里可愧疚了,昨晚黑里陪了一宿都没回家,我还念叨要去看看呢,敢情你不知道啊?”
“俺病了,没听说呀?那婶,美娃住哪个医院?小胖儿咋样?”
“瞅你吓的,不打紧。要是打紧,不早告诉你了?昨晌午的事儿,你老丈人和你那大哥送的,在协和医院,就老程的中医堂。哎哎,姑爷别着急上火的,有你那大哥呐!……” 那婶瞅吉增没等她把话说完就蹽了,纳闷的自语道:“这孩子,一瘸一拐,你瞅他猴急的样儿。嗳,这老二咋会不知道呢?啊,病了,周大掌柜没敢告诉这个活牲口。瞅我这破嘴,多嘴多舌的,这不说漏了吗。嗨,这虎小子,指不定做出啥唬事儿呢。哎呀不好,我得瞅瞅去。唉!姑爷,等等我,咱一块去。”
吉增听那婶说的,如同掉进冰窖,浑身凉个透,木木的直奔协和医院。吉增心想,美娃撞了,这么大事儿,老爷子为啥牙口缝没欠,铁桶似的瞒着他?这是生他的气呀,要不能下手那么狠揍他,俺这是造的啥孽呀?
医院门口,一辆漂亮的花青马车停靠在雨搭下,吉增抹了一眼,“呸!汉奸!” 一扭头,瞅见那蜰从屋门走出来,吉增虎目圆睁,眼中窜火,拐了几步,拽过那蜰的脖领子,那蜰“你……”字没等说出口,吉增的拳头已削在那蜰的脸上,嘴角就淌出了血。吉增又是一顿拳脚,把那蜰打趴在地。这功夫上来两个挎盒子炮的,照吉增屁股就是一脚,来的突然,又加上屁股的伤,这真是雪上加霜,吉增一下就被踹趴下了。两个狗腿子饿狼扑食似的扑了上去,吉增就地十八滚,一个黑鱼打挺棒子了,回身飞起两脚,踹倒一个,踢飞一个,吉增叉个腰骂道:“那臭虫,你不要欺人太甚!屁眼儿里插大葱,你装啥大尾巴狼你?你等着,你二爷俺这事儿跟你没算完?” 两个狗腿子呛呛地爬起来,掏出了枪,胆怯怯的向吉增凑过来。
车老板儿扶起那蜰,那蜰痛苦难堪地向两个狗腿子挥挥手,捂着青肿的脸,挪着步,费劲巴拉地趴上车又下了车,朝另个房屋走去。吉增嗯了声,掸掸身上的浮土,吊儿啷当地进屋看望美娃。
美娃一个人静静地躺着,脸色苍白平和。一条腿用白绷带打着夹板,悬起打着牵引。吉增鸟雀地推门,鸟雀地走到病床,鸟雀地立在床前。
“你咋还没走啊?” 美娃闭眼地说。
“……”
“走吧,那大哥,都待一宿了?”
“……”
“你咋……他爹?……”美娃说着睁开眼,又合上眼,两颗泪珠从眼角流出。
“好些了吗,美娃?”
美娃点点头,又有几颗眼泪成串地淌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