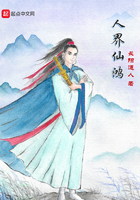崔武身穿半新不旧的蓝斜纹大卦,脚上穿着啃了边的破皮鞋,手里拿着飞了边的黑礼帽,满面憔悴,一头的雾水,眼里带着重重忧虑,心急火燎的朝日军司令部趖(suo)行。侦缉队的两个跟屁虫,紧随其后。
崔武自打被龟河大佐软禁在医院里洗脑,后经吉德多次出面和杉木交涉,才允许以镇长身份回家‘养病’,由一名日本女护士监护,侦缉队两名保镖日夜守护在大门外。这几个月,崔武一直隐居在家,没有露面。今儿个,听外出买菜回来的崔太太说,日军围剿马虎力山王福队,带走了吉德和小鱼儿两口子。他如坐针毡地再也在炕上坐不住了,吩咐崔太太快弄点儿饭,胡乱扒拉两口,就要出门,日本女护士以各种借口,百般阻拦。崔武最后以我去上任为托,才得以成行。
崔武看北大道三街口日军司令部附近,花搭地站着三五成群的镇民,嘁咕嚓地像虫子嗑苞米叶子似的,鬼头鬼脑地交头接耳。挎着大枪的警察,嗤皮懒肉的仨俩聚在一起,哈刺打掌地抽着低劣的卷烟,有痰没痰地咳着嗓子,消磨无聊的时光。炮楼上站岗的日本兵荷枪实弹,两挺歪把子机枪枪口,黑黑地对着人群。崔武触景生情,已是物是人非了。
马六子心里有事儿,眼睛就比别人的奸,一眼就叨上了崔武。心说:呀,出活神了!这倔巴头,今儿个是咋的啦,貉子改变‘昼伏夜出’的习性了?在家待腻歪了,还是被日本娘们软化寻思过味了呢?嗯,崔武这一反常态的举动,是没雨披蓑衣,这是防雨又求雨儿呀!嗯,这个,哞吗,肯定是冲着吉德这事儿来的。王八要硬上树喽,可有好戏看了,不是成精就是翻盖子?我这大盖帽沿下,还是马王爷多长一只眼吧!日本人都拿他煲汤,不是长白山人参日本勒他?看来这人参,要逗小红兜兜孩儿玩了。茅庐披雾难见真面目,崔武这人城府深着呢。从常理讲,崔武为人还真是个正人君子。为官清正廉洁,刚正不阿,经渭分明,于民做主。可就是太迂腐了,拧劲得****橛子,给麻花都不换?嗨,太不识时务?与世风是苞米楂子煮小米,不和如!我与他是阳关道独木桥,走的是两条路。同舟共济,殊途同归,还是分道扬镳,那是老天爷的事儿喽!马六子的想法,随着崔武刷刷地来到眼前,倏(shu)尔而逝。
马六子陪着笑脸儿,忙躬身颠嗬两步上前和崔武打招呼,不尴不尬地随着崔武的身后,就像小孩儿见了娘,啰嗦开了。
“哈,崔镇长呀!你‘老’好多日子不见了,哈,鬓发如初啊!你这急匆匆地这是上哪旮子呀,用不用小的陪陪你‘老’?我这些日子净瞎忙活了,也没抽空看看你‘老’去。嗨,你‘老’也知道,日本人的饭碗不好端呐,整天整夜不是这事儿就是那事儿,整得你像烂头苍蝇似的团团转。我没去看望你‘老’,你没生气怪我吧?这世道变了,哪赶上民国呀!这满洲国,换汤又换药,都变味啦!明里吧是执政说了算,其实吧日本人早在暗地揣咕好了。溥仪也就是鹦鹉学舌,八哥学话,汤瓜儿一个。哈哈,我多嘴,我多嘴!崔镇长是啥人呀,哈,有眼识珠,就给它泡蘑菇,遭那洋罪呢?哈,你不像我,我哪有那钢条啊,吓唬两句,就浑身塞糠。我妈说我,打小没营养上,腿就软,好攥筋。这不,啥作损的事儿不得干呀?吃人眼下食,还不为了半斗米,东北爷们的这腰啊就叫日本人说了算了,你不点头哈腰的也得点啊?整天价围着日本人的屁股后转,黄泥掉进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呀?你就不同啦,啊,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你‘老’大好人一个。日本人敢小瞧你吗,你姐夫唐县长那么一罩,谁敢哟,打狗还得看主人呢不是?老百姓更是高看你‘老’一眼了,有骨气,尿性!只戴满洲国的乌纱帽,不替日本人办事儿,这多好事儿,可谁敢跟你‘老’比呀?殷会长那个脾气仗不,还不得拧着鼻子给日本人当狗似的使啊?吉老大咋样,愣不愣?你胳膊没有日本人大腿粗啊,还不是铁匠大锤砸砧子,硬碰硬!震裂了虎口不说,现如今身陷龙潭虎穴的边儿上,两手扒不紧,松松手,就掉进去了。蜜蜂蜇人的结果,伤之小痛,自个儿却付出五脏而亡。小日本阴着呢,像扒苞米似的,扒完皮再扒瓤儿,这报纸上喧噪表彰吉老大繁华市场的功绩墨迹未干呢,就明请暗绑的给两口子整到沙场上去了。这黄鼠狼拜的啥佛念的啥经,还用蟑螂臭虫说话呀?你‘老’再两耳不闻窗外事儿,蹀躞(xie)走道,吉老大凶多吉少。我这箴(zhen)言中不中听,你搁心里好好掂量掂量。杜鹃能借巢下蛋,咱就不能海螺壳里藏身,当回寄居蟹,那螯是白长的吗?蜻蜓点水为的是产卵繁衍后代,蛤蟆鼓泡为的也是招偶生子,咱人活着争霸斗狠,为了啥?人生一世如同草木一秋,无非臭名远扬,遗臭万年,或者留芳千古,万人传颂。像我吧,不伦不类,非人非鬼,人鬼之间,阴阳人,二乙子。哈,嗯,我多此一举?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老’心中早有个小九九啦!”
崔武目不斜视,听完马六子胡诌巴扯后,挑挑眉毛,一板一眼,文绉绉地说:
“啊,待我寻绎(头绪)。好矣,毋多言!”
马六子多会察言观色呀,眼珠子转了十八个个,从崔武有板有眼的腔调中听出了玄妙之音。他的露面确实是为了吉德之事儿,并且打定了主意,下定了决心,非救吉德于水深火热不可啊?嗯,好家伙,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俩儿尤物,又要携手并肩喽!小日本哟,请神容易送神难,这是往自个头扣紧箍咒呢。一个榆木脑袋,一个花岗岩头,都四楞八箍,哪个经过眼儿钻了?难整!马六子脑子飞转,忙说:
“嗯哪!那是。贵人金口玉牙,一字值千金呐!小的明白,定封住我这张烂嘴。哎,崔镇长,你瞅殷会长那帮人,还扒眼抹眼地碓在那噶达呢。咦,川岛队长也在啊!我就画了魂了,他咋没随龟河大佐走呢?啊,留后手呢。”
崔武不再听马六子啰嗦了,独自两步并作一步走。殷明喜也看见了崔武,忙迎上前去。两人同住一个镇上,好像远离千山万水。几个月没见面,尤如隔了三秋。四只大手紧紧握在一起,四只眼热泪盈眶,相互端详了好一阵子。殷明喜颤巍巍地说:
“崔镇长你好啊?啊,枪伤都好利索了?你始终是俺心里那个好镇长,俺老想你啦!见着就好!见着就好!”
崔武噙着泪花说:
“好了!好了!你咋样啊?身子骨儿还过得去?”
殷明喜悲喜交佳地说:
“能咋样,还凑付。心不静啊?老是咯咯秧秧的,成天价像吃了大蛆似的,倒酸水。你这家伙,小日本一来,你就让人家当缩头乌龟‘养’起来了,连个照面也不打,咋的,怕啦?爷们,俺死去的老娘有句话,说的好啊,‘人死了也要迎风站!’天变了,塌不了,俺还盼过舒心日子呢。这些烂蒜泥鳅,能掀多大浪啊?这美丽的家园,早晚还是咱们的。咱占碾子,不推它的磨,得和他们穷搅和,你不叫俺舒心俺让你不得消停,成天价和你搅混?管它啥啥呢,汉奸也好,日奸也好,啊,还有满奸,反正俺小时晚没少吃大煎饼,那俺就是大煎饼了?拍拍胸脯,挺挺脊梁,问心无愧就行。大家伙心里都装着一块镜子,你哪顿焖的啥饭做的啥菜,是焖的高粱米饭炖冻豆腐,还是苞米面窝儿头蘸大酱,还是捞的二米饭猪肉炖粉条子,谁咂巴咂巴嘴不留点味道和渣渣儿?日子长了抠抠牙花子,还能想起点儿啥呢不是?咱们都眯在家,当顺民呐?那小日本可乐了,大大的良民!俺说爷们呀,你这是撒尿呢还是拉屎去?哈哈!”
崔武看殷明喜这么豁达,心里也开朗了许多,压在心头里几个月的一块铅坨落了帖。他舒展舒展眉头说:
“大掌柜,我想在浑水里再嗤泼尿,拉摊屎,臭死这帮没安好心的黄皮子?让小日本声名狼藉,成为不耻人类的狗屎堆。当鬼的面是秦桧,当人的面是岳飞。举手时喊吾天皇万岁,背下里喊还我河山!当面是鬼,背后是人,是人是鬼自个儿明白。卖个脸能咋的,无非拿唾沫口水黄粘痰洗脸罢了,这屁股还不坐在自家炕上吗?”
钱百万和二掌柜等商家掌柜的,也凑过来和崔武寒喧一番。
钱百万拱手说:
“崔镇长,你算是拨开迷雾见晴天了,明白就好?殷大哥一辈子少言寡语,今儿个说的话够他一年说的啦!咱是啥人,谁都清楚。占着茅楼不拉屎,放空屁谁还不会呀?连尿炕的小崽子都知道,断了腿的癞蛤蟆能蹦达几天?你占人家热炕头,又欺男霸女的,谁不硌应啊?哑巴都要说话啦!冯家铺子那小哑巴,当邓猴子面比比划划骂了几句日本人,邓猴子让人抓到侦缉队去了,至今还关着。听说要整到矿上去挖煤。崔镇长你说,要让邓猴子这号畜生当权,还有咱好吗?遇到噎脖子的事儿,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你吧,当过张大帅大绺子的镇长,还当过小六子的镇长,又当过民国的镇长,最嘎咕的是还给小绺子胡子当过几天镇长,这满洲国的镇长你是当还是不当,牛匹也耍了,日本人的热脸也贴了你那冷屁股了,小日本算是领教你那宁折不弯的体性了,还绷着乌纱帽一条道跑到黑呀?那你晒的不是日本人的台,你晒的是大伙儿的心了。不管咋说,木已成舟,生米煮成熟饭,爹死娘嫁人你就不活啦?大山咱搬不动,小来小去的,横上一杠子,小日本也得寻思寻思?都惹翻了,有他好瞧的。不有那么句话吗,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心静水自清,智者见混浊能澄清,仁者见邪恶能摆平。人都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反正你要真戴上了那个人人痛骂的乌纱帽,心态得平和,人家把你当乌鸦,你就是乌鸦,不吃腐肉就得了?你这不倒翁,四朝元老,凤毛麟角啊!当朝的把你当菜板上的一块肉,咱把你当成能挡箭的挡箭牌。话又说回来了,不能瘦驴硬出恭,啥啥都打拨楞鼓,量力而行,摘星揽月不现实?怕,就怕你能做到的事情你不做,当和尚不敲钟啊?咱做了,没办到,那是又一回事儿?”
崔武听了各位前辈语重心常期盼的话,心里波澜起伏,痛快淋淋,可又感到与鬼为伍的艰辛和愁苦。明里看上去是给日本人赶网,暗地里当个钟馗。咱这心里的一根小竹竿儿,能挑起这千斤秤砣吗?两挂马车一个道上跑,我能驾驭得了吗?栽了跟头咋办?小日本我倒不怕,大不了以死相搏,死都不怕了还怕个啥?怕就怕,好心办错事儿;怕就怕,办了好事儿让人当不是说;怕就怕,违心办了一些自个儿不愿办的事儿;怕就怕,别人不理解;怕就怕,算账没有了账本。嗨,为了百姓,为了救吉德,我不当这个镇长没有说话砝码呀?打人家巴什,只有当镇长。小日本软磨硬泡,就是想让我归顺满洲国,当它日本人的******。拿我当镇长,去换回吉德的命和‘清白’,是值还是不值?值的是吉德和大家伙儿,不值的是我自个儿背上一个黑锅。这又太委屈自个儿,太违心了。不这样,又咋和日本人讨价还价,就救不了吉德。救不了吉德,打鬼子的队伍就少财力的资助,哪多哪少,擀面杖和筷子,哪粗哪细,傻子都能分辨得清。这擀毡的事儿,咋整都是说不清道不明的,糊涂庙糊涂神吧!冤就冤了,‘冤’字本来就是兔子被困在洞穴里,我和兔子同病相怜喽!骑狼看唱本,走哪算哪!跟老虎藏猫猫,只能躐(lie)等。
崔武想的很多,并不想说出要以当镇长为妥协条件和日本人交换的话,救出吉德。他不想让殷明喜和吉德承受感恩戴德的情义,怕引起好脸的殷明喜的反感和推托。以我之辱,换取吉德含耻之冤,他们爷们是万万不能做的。我是出于义气,是义举,但大大戳伤了殷明喜和吉德的自尊心。为此他回避了这个话题,也是他到死也不能说的心里秘密。我何不将计就计,就当听其劝,顺水推舟,堂而皇之的当众说出我当镇长。一来是大伙儿的规劝,不是我崔武想当这‘汉奸镇长’,高风亮节;二来日本人也不能沾沾自喜自个儿攻心战术的成攻;三呢,也把我委曲求全的妥协救吉德的初衷掩埋得天衣无缝。所以崔武不惜吝啬之词,说出激昂奋进的心里话:
“各位前辈,我崔武虽是几朝江湖了,但那是做的中国人的官。这被倭人所掳的官,我是打心眼儿里压根不想做,也不愿做。可众望所归,实强人所难。为众生遮风挡雨计,我崔某不才不德,愿承受冤孽,忍辱负重,肝脑涂地,粉身碎骨,以御窳(yu)劣,还我河山。希众前辈,众乡亲,昂起头颅,挺直脊梁,携手并肩,鼎力相助。望马鬣(lie)张扬,粼粼碧波,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殷明喜等众掌柜和孙二娘等众乡邻听后,无不鼓掌叫好。马六子这个阴阳人也为之动容,为之感动,良知灵魂天平的秤砣瞬间偏向了正义。那帮混吃等死,醉生梦死的警察,也听得肠溜屁顺,有的净也情不自禁的鼓起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