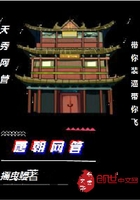关内军阀混战正酣,关外日本人蠢蠢欲动,各种势力人物粉墨登场,商战、暗斗,拉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角逐。
松花江浪花荡漾,每朵浪花都闪着个太阳。白亮银色的叼鱼狼,掠过涟漪起伏的江面,自由的翱翔。静静的一叶小舟顺流而下,上面坐着吉增和美娃夫妇,老远瞅上去悠哉游哉。
吉增双眼呆滞的眺望着细浪拍岸卷起千朵雪和远方淡淡的山影绿茵茵的两岸,好像心不在焉。
眼前掠过一处鄂伦春的撮罗子,红狐皮和黑貂皮搭在门口一盘马拉磨旁的架子上晾晒着;一处鱼亮子,靠江边儿长着一撮一撮柳蒿芽的空地上,人字架子上晾着鱼网和成串的鱼干,一条老黄狗懒散的趴在点缀着小白花的绿地毯上;亭亭玉立的篝火旁有两个人叼着大烟袋席地而坐,白烟袅袅的带着烤鱼香往上拔着高,委婉地渐渐飘散,融入蓝天。不远处,成群的羊群啃着青草,几头老黄牛“哞哞”叫着撒欢跑远的小牛犊儿。一大群灰花花的大雁,在江北岸草滩水泽中悠闲的嬉戏啄食,不时有大雁起飞翱翔于蓝天,不时有大雁从空中滑落。
对这一幅风和日丽的松花江两岸优美画卷,愁思满目的美娃,盯盯望着微波荡漾的江水,无心浏览松花江两岸风光。
自打小胖夭折后,吉增遭受了极大的打击,一直萎靡不振,整天价泡在烟馆里鬼混在瓦子里打发时日。美娃更是伤心欲绝,整天价以泪洗面,心里憔悴得衰颓苍老,看淡了人生的七情六欲,对吉增不抱任何幻想,两人也已是有夫妻之名无夫妻之实了。
夫妇两人己有好长时间没回黑龙镇了。这次从三姓赶回黑龙镇,是为大舅殷明喜五十大寿祝寿的。接到电报,错过了船期,又没赶上七天才一趟的班车,这才雇条拉脚的小船赶往黑龙镇。
吉增虽对美娃有愧于心,但就是不能自拔,陷入了颓废的神经状态。好在铺子有老丈人周大掌柜的帮衬,得已维持。
吉增除了陷入在小胖夭折的思念中外,心里还有个人叫他纳罕的琢磨不透。
一年多前在三姓,吉增结交了一位不速之客,后来成了交心换心的朋友了。可不成想末了那人有件事儿欺瞒了吉增,叫似朋友为哥们的吉增一直耿耿的不舒服。
这天,吉增醉生梦死的和几个哥们在一个小酒馆喝得醉醺醺,在隔桌走过来一个彬彬有礼绅士模样的人,微笑着说话,操着一口纯粹的京片子口音,和吉增搭讪拉话,“掌柜的,初次见面,请多关照。我是京城来的皮货商,叫邱厚来。”来人很随便的自我介绍,“掌柜的,不请我喝一盅吗?我非常了解咱这噶达的人豪爽好客,在中国是出了名的。好喝、能喝、愿喝、瞎喝、傻喝,黑瞎子掉酒缸——非一醉方休不可!是不?”说着个个儿搬个板凳,蹭巍在吉增身旁坐下,又抱拳又施礼。吉增醉眼眯瞪地歪歪头,大舌啷唧的拍着邱厚来的肩头说:“你老兄,耗子啃汽球——嗑(客)气啦!俺这些哥们,要论喝酒,能喝你个洋拉子(树虫)倒上树,尿出的尿,一头壳郎喝了,就会磕头。来吧!”吉增挪挪凳子,给邱厚来腾个地儿,又扯过一双筷子一个小碟儿一个酒盅,撸下袖子,对两哥们说:“哥们,这位老兄,跟咱们叫号,咱们也不能装**熊,拿出看家本事,跟老兄照量照量!”坐在邱厚来旁的胖子说:“朝火朝火就!”“呱”把酒盅倒满,“先走三个!”“欻欻”谁也没让,自己个儿先扔了三个,向邱厚来一抹眼,手一让,邱厚来也黄瓜蘸白糖——甘(干)脆!没闭嘴倒嗓子眼儿三个,“咕噜”下了肚。这三杯酒下肚,还有啥说的了,论年长幼,磕头拜把子,哥们了!
吉增醉眼朦胧的拍着胸脯,“邱大哥,这趟想办点儿啥货,包在老弟身上,一利不取!”邱厚来不急不忙,稳稳当当地说:“我的货不难办,看好啥货要啥货,不挑。现钱碓。一把一利索。”说着,自斟自饮,“啊哈,我就不客气了,兄弟们随便喝。我这个人也是竹筒倒豆子,有啥说啥!如今关内战事正紧,啥货都奇缺,尤其皮货生意更好做。”吉增问:“这生意呀,如今是应了那句歇后语了,“王八头敲鼓——越敲越缩缩!你说好做,咋个好做法?”邱厚来眨巴眨巴一双单眼皮儿说:“老弟,军阀混战,把关内整的是灰堆里放屁——乌烟瘴气!逃难的人多,少帅又鼓动移民东北,冬天晚儿谁都怕冻着,有个皮筒子穿着,走到哪都能避避风寒不是?所以呀,这皮货最抢手了。你老弟不是开皮货铺子的吗,这正是个赚钱的好机会,想大发一把,就和咱搭个手,保你只赚不赔?”吉增稀溜一声,“钱难挣,屎难吃,有这好事儿,你别诓俺?”邱厚来也一嗤溜,“你不信是不?准比你这儿的市价高两层。咋样儿,有赚头吧!”吉增向上翻翻眼说:“好是好,这不是发国难的不义之财吗?”邱厚来说:“你小子还挺那啥呢,这熙熙攘攘这人都干啥呢,忙活的不都是钱哪?你个买卖人,又不偷又不抢,凭脑袋瓜儿吃饭,有啥这个那个的?这叫赚钱有道,商机难觅呀!”一旁的胖子发话了,“那可不咋的。该赚就得赚,说不准咱们还是帮了他们的忙了呢?他们没皮子买,说不上得冻死多少人,是不邱大哥?”吉增看胖子也这么说,本来就虎胆,有酒垫底儿,虎劲儿上来了,“****娘的。”满口应承,“好!咱今儿个煮酒论英雄,正事儿明儿唠,喝酒!”老哥新朋,叮咣的,马尿又一顿灌。
跑堂的,看吉增都喝这样儿了,眼睛都绿了。吉增老来,小来小去的,跟吉增处的不赖,就捅咕捅咕吉增,贴吉增耳朵小声说:“吉掌柜,差不多了,整多了咋回家呀?”吉增喝得早已有些潮了,硬着打摽的舌头说:“你、你别管!鲁智深喝多了能倒拔垂杨柳,俺拔不了垂杨柳,俺拔木桩橛子行吧?俺、俺邱大哥,谁呀?俺哥们!你说,不喝透了,能、能他娘的回、回家吗?俺今儿高、高兴,再、再来二斤,俺、俺还、还能打、打死只老、老虎呢!”邱厚来这老小子酒量很大,咋没咋的,也欲擒故纵地劝说:“老弟,改明儿再喝吧!”吉增挺挺站起来,捞着邱厚来的手说:“你、你瞧不起俺?啥三碗不过冈啊,那是店家没酒了。这儿、这儿的酒缸能洗澡,有都、都是。邱大哥咱再来三盅。完了,完了,俺听大哥的。”又三盅下肚,吉增还要来,邱厚来说:“老弟,咱领你去个好玩地儿,一切开销大哥包了。”吉增抻长脸说:“你还有好地儿玩,你别王婆卖瓜自吹了?三姓这噶达俺哪没玩过,还吹啥呀吹?好!俺今儿是两把钥匙挂胸口——开心,开心,特开心!哥们,跟邱大哥走,看他有啥花样儿?”胖子淌着哈喇子也说:“邱大哥请客还有啥说的。妈的他财大气粗,咱们不蹭他蹭谁去呀?要讲玩儿,咱们都是菜园子里老母猪啃过的萝卜没缨,各个是头!”吉增由邱厚来搀扶着,含糊不清地对跑堂的乱儿乱儿,“先赊着。记账,一堆算!”跑堂的说:“吉掌柜,这位大哥已付过账了。”吉增说:“付过了,那扯啥呢?那不成了豁子嘴照镜子,当众出丑呢吗叫俺?”邱厚来咧咧着吉增说:“瞅老弟说哪去了?咱们哥们一条腿裙子,不劈叉!一家兄弟咋能说两家话呢,谁花不是花呢?”吉增说:“可也是。一个屁咋能掰两半呢,哥们嘛!”
吉增几个儿,晃晃悠悠,丑态百出,咋咋呼呼,招摇过市,惹来不少路人的卖呆儿。后来就剩吉增、胖子了,还和碰见的熟人啥的猫叫春,搂脖儿抱腰的瞎扯。吉增嘻嘻哈哈地和邱厚来乱扯。邱厚来也极力奉迎,天南地北的说笑逗乐。
吉增不知不觉地被邱厚来引进一个幽静又幽深的胡同,再往里走了一阵子,来到一个很考究的青砖大瓦房院落。邱厚来有节拍的扣了扣虎头饰铜门环,从里面走出一个穿长袍马褂的门房。邱厚来向门房使个眼色,门房点点头,“来客啦!找两个单间,这都是我的铁杆儿哥们,有仙桃嫩枣的尽管上来,把我兄弟陪好了,钱不算啥事?”门房呵呵地说:“我拿脚趾头都能猜度到,不是貉,谁往一个丘里钻呀?”门房老道的引着邱厚来、吉增、胖子进了院,进了屋,几个花枝招展的毛子娘们拥了上来,说着蹩脚的汉话。吉增晕晕乎乎地辨别说:“这也不像似花行柳巷啊,这倒是周正大当家的地盘,毛子烟馆!邱大哥,你挺能淘咕呀?这噶达的招待,除了毛子娘们,还有琉球娘们呢。你初来乍到刚跩脚,咋这么通络呀?你个大泡卵子,生意还没做,花花草草,倒先牛奶香肠面包的又此地苣荬菜的开剜了?这噶达,可没有蹩脚货,你瞅那胸挂的大葫芦,一个就够十个皮糙肉厚大老爷造半拉月的,你老兄艳福不浅哪!”邱厚来说:“镜花水月都,老弟,你满意,我高兴。”一个老毛子娘们笑成桃花似的,扶着吉增坐在烟榻上,礼貌的帮着吉增脱掉鞋,把两腿扭到榻桌前。邱厚来往榻上一仰,对毛子娘们说:“来,给我兄弟烧个烟泡。我不抽那玩意儿。老弟你掐着劲儿抽个够,好好过过瘾。嘿嘿……”吉增躺下前,还没抽,“邱大哥,你来一口呗,这玩意儿可解乏了。”邱厚来忙一摆手,“你来吧!我享受不了,一抽就恶心,要吐。”
吉增躺下后,毛子娘们也委上榻来,贴着吉增身边烧上大烟泡,笑眯眯地把烟枪递到吉增手里,吉增接过烟枪,抽了一口,把长长一赶儿烟儿喷向毛子娘们。毛子娘们张开红红小嘴儿接住,吸进,憋憋了一会儿,淡淡的烟束喷到吉增脸上,然后吟吟地笑着瞅着吉增,吉增呵哈一乐,“这老达姆挺调皮啊,会撩骚!”吉增又抽一口,喷毛子娘们一脸的烟雾,虚虚幻幻,醉眼里更加隐隐绰绰,云里雾里了。
“来,你抽一口。”毛子娘们笑着就吉增的手抽了一口,很贪婪的憋了好半天,才又把一束烟喷向吉增,吉增也学毛子娘们的样子张嘴接着,一下子呛住了,换来一串儿毛子娘们仰脖儿半遮脸小鸡儿下蛋似的咯咯。
吉增抽完一个烟泡,起身漱了漱口,一抬眼,邱厚来已不知了去向了,屋里只剩下他和毛子娘们俩人。
吉增栽咧咧地鼾声大起,酣睡过去。
“倒老实,真乖!”毛子娘们出溜下榻,正正布拉吉,怕抽拉着吉增,随手捞过一条大毛巾给吉增盖上,扭身出门还回头瞅瞅吉增。”
吉增也不知睡了多久,醒来时,屋里已点上了蜡烛,明明亮亮的。毛子娘们躺在吉增对过的烟灯旁,一个人想着啥呢。吉增打个哈嚏,抻个懒腰,坐了起来,迷登的瞅着毛子娘们,笑了。毛子娘们也一笑,起身烧个烟泡,把烟枪嘴插进吉增嘴里。
门嘎吱吱推开了,邱厚来进屋来,“老弟醒了,没打搅吧?”吉增放下烟枪,“你这大哥,够鬼祟的。俺是康熙铜钱,眼儿大!一睁眼你没了,又一睁眼你又回来了。你这不是耗子搬家,穷折腾吗?”邱厚来坐在榻边瞅着吉增笑说:“我喝多,才出去散散酒气。我看你叫烟儿拱的,小脸儿是阳春汩汩桃花,越红润了!花烛夜半深,良宵渡美女,窦燃情未了,倜傥又风流。瞅那毛子小娘们灿烂夺目的脸,就知你俩抽的唠的很开心,还跟我卖关子呢?”毛子娘们也是为了讨好吉增,一边溜缝,“这位爷呀,那是王八头上顶扇子——盖帽了!”说着,向吉增眼前晃着大拇指。
正说着,另个毛子娘们推门进来,装的一脸的不高兴,“菜花,你倒快活,烟份子没少挣?”说着,冲菜花一挤咕眼儿,指着邱厚来报怨,“这位爷可倒好,把我拽到借彼儿,只说话也不抽,清规戒律的,他不是个爷们!咱这些姑奶奶,是指烟份子挣钱的。”这个毛子娘们气的,说着就把邱厚来摁倒在榻沿上,骑上,邱厚来闭闭嘴的嘿嘿,就往下推那娘们,吉增一瞅,忙把那个毛子娘们捞下来,这才解了邱厚来的围。
闹哄一阵子,邱厚来喊来茶头,要了膳食白干,“咱们边喝边唠好吧!”菜花又叫来胖子和陪胖子的那个毛子娘们,几个人撤下榻上的烟具,放上炕桌儿,六个人围了一圈,咬了劲儿的喝了起来。
毛子不管男女,不怕喝,喝不怕,怕不喝,有一个算一个,好喝、善喝、能喝,喝不够,见酒比见老子还亲,玩命的喝。
一会儿,几个毛子娘们,煮熟鸡蛋剥皮的脸上浮出红晕,粉莲的诱人。菜花大着舌头,秃噜,“爷们几个,我们是俄罗斯贵族,十月冬宫枪炮一咕咚,就把我们这些小小天鹅轰到这噶达来了。我们养尊处优,不会干啥玩意儿,落迫的凤凰不如鸡,只有卖笑陪客人,糊弄几个钱儿花。唉,有国不能回,有家不能归,有姊妹不能聚,有父母不能见,苦啊!”吉增撇撇嘴说:“苦个屁!这有吃有喝的,哪苦啊,苦啥呀,还诉苦叫屈?阎王爷说老毛子话,你骗鬼呢你?喝你奶奶的酒吧!”毛子娘们叫吉增几句话,扒哧地嗤嗤傻笑,一杯一杯灌酒。
灌够了,菜花搂着吉增的脖子,“你这爷们嘴可够损的了啊?癞蛤蟆跳进美人蛇嘴里,送上门的肉,你掏上了?嗯,咱不就想多讨点儿赏钱儿呗!”邱厚来挑一眼菜花,逗嘘说:“亏待不了你几个,钱是啥玩意儿,花的呀!老弟,你说是不啊?”吉增说:“爷们挣钱谁来花,一个杆子砣来压,一个买来一个卖,两厢情愿都自在。嗯、嗯,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