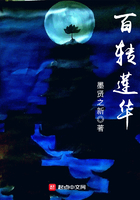皇姑屯大帅专列一声爆炸,张大帅一命呜乎,日本人下手了。张少帅执印东北,“易帜”,天下大“一统”。
“小鱼儿又甩籽子啦!”
“啊,这是第几窝了?”
“第四窝了!”
“又是个儿马驹!”
“哎呀我的娘哟,咋赶谷子了,那么密实呀?那小身板儿,没累趴稀了,赶上老母猪能生了,瞅这一窝儿一窝的。那柳月娥咋啦,吭哧瘪肚的,生个心儿就卡上壳儿,小母鸡不开裆啦?是不是德哥管踩格子不点种啊,把地给撂荒了?”
“你猫头鹰睁一眼闭一眼的,别猪八戒跳猴筋,弹毛蛋弦子了?就德哥那情种,是浇地浇的太勤了,把地给浇涝了,淹死了!”
“哈哈,是不是小鱼儿净偷油喝了,到了柳月娥那噶达,就剩些清汤寡水的刷锅泔水了?”
“你金鱼睁眼睡,扯呢?那春芽呢,回去又来,来了又回去,不也是老核桃不开口吗?”
“谁说不是呢。嘿嘿,那大丫儿不也不是,生个小德后,不也扎口了?”
“你说大丫儿呀,那可不能跟春芽和柳月娥比,那是供桌上的猪头,明摆着的。大丫儿就不同了,偷一口吃一口的,不是旱就涝,哪能就那么巧接骨上那几天闹心的日子啊?嗨,谁生养几个子女,这就是命。小鱼儿,面相好,人又柔韧顺滑,一瞅就是个多子多孙的命相。”
云凤、春花、巧姑,还有小樱桃几个小媳妇,从黑龙镇赶回娘家婆家帮家里忙活春种的,栖栖一块堆儿,坐在牛二家后院的果木园子里,叽叽喳喳,山燕子似的纳着鞋底子缝着衣服嚼着舌头。
一条黄盈盈大狗,水呱呱地趴在云凤脚下,一会儿挑起眼皮,一会儿抹上眼的憩息。
几个孩子,淘气包儿小子在一旁抠坑儿弹着玻璃溜溜,小丫头片子在树下蒙着眼睛摸瞎瞎找家家,“小丫蛋儿,梳两辫儿,扭达扭达,上江沿儿,打出溜滑,摔屁蛋儿;小子哈哈笑,丫头哇哇叫,哟哟呀哟哟,屁股摔两半儿……”
紧挨果木园子西,是拿柳条编的低矮的篱笆墙隔开的菜园子,种的各色应季小青菜,蘸大酱生吃的小白菜、小菠菜、小生菜、小香菜、小葱、小茴香、小水萝卜,青油青绿的铺满一畦一畦埂,散发着清新味。还有炒鸡蛋、包三鲜饺子馅儿从房墙根儿到北道杖子长长不太宽的两大垅叫马粪追得绿耨耨一捺多高的韭菜,挨韭菜地靠西边杖子两垅过冬的苶葱,高高蹚胯的耨耨绿长着梃儿,亭亭玉立,头顶着大大的被白绿纱巾包裹的桃心儿向上的葱骨朵,含苞待放,影影幻幻的映现孕育着的千万个襁褓中的蓓蕾黑宝宝。
“嘁嘁喳喳”,家雀在树上、房上,上窜下跳。
“喳喳唼唼”,几只油黑的小燕子,在屋檐下的燕窝旁蹿跳。
几株垮塌塌的向周围铺散着老朽不衰和茂盛新枝桠的老樱桃树,结出的一个个小小樱桃,露出树叶的,变脸儿似的,一面青绿,一面紫红,隐在树叶深处的,还青绿楞青的,看了都叫人嘴酸。
几株矮趴趴的李子树,绿绿葱葱,绽放油油的光,小指盖大小的李果,和叶子一样的颜色,不大捋会儿,很难发现果子的踪影,谁要发现,那就自找苦头,嘴里准涩的不行,舌头都虏不动,蠢蠢的发轴。
几棵高高的杏树,撑伞伞的,跟房脊比试的抢着阳光,青青的小杏儿,尖儿上顶着干瘪的花絮,密匝匝的长满了枝头,昭示金黄的一天。杏树一旁几棵沙果树,沙果已长有野山丁子大小了,一撮一拉的,奓奓的像花蕊点缀着树叶的空虚。
“嘎嘎”,掠过的一队大雁,在高空鸣叫。
宁静祥和的乡间房后果菜院里,风和日丽,菜蔬茵茵,果木翠绿,扎堆儿做针线活计闲扯的女人,淘气、调皮、戏闹、嘤嘤的小孩子,一派东北庄稼院的田园风情。
围坐在小板凳上的云凤,解开抿大襟花布衫子襻扣留着领口一枚,搂开怀,捞出鼓鼓胀胀的大布袋子,喂着怀里八、九个月的大小子。这是她的第三个孩子。云凤够起脚下的鞋底子,纳着,“你说吉老二家,够糟心的,啥事儿都叫他摊上了。美娃好不容易生个小胖,活蹦乱跳的,多好的孩子。前儿听牛二说,不知遭啥邪得了啥怪病,抽开了羊赶儿疯,不几天,说没就没了。美娃哭的呀,死过去又活过来的。几次寻死觅活,都到松花江边儿,叫人拉了回来又摸绳子,可咋整你说?二十几岁,出这丧子的恶事儿,搁谁吧,劝理儿劝不了情,心病难医呀?这折磨瘦的呀,多俊的人,皮包骨头,像髅髅瓜了,人都脱相了?嗨,老二呢,一天老打蔫儿。大烟不记了嘛,又捡起来了,整天泡在那瓦子里,铺子生意代理不理的。你说啊,美娃的命咋这么不济呢,要是能再生一个半个的也好啊?吉老三这个驸马爷呢,艳灵又作妞了,可不知是个啥,就怕甩面片子,又是个丫头。他那三小姨子好灵,殷大舅撮合,硬是嫁给了钱庄钱大掌柜在燕京大学堂念过书在咱镇上国高当先生的公子,好像小俩口也不太那个。那四小姨子,也不太省心,老是和那些爱闹腾不稳当的一些先生同学搅在一起,殷大舅也惯孩子,眼睛都不睁一下。就德哥这股旺兴,一个小鱼儿就救了驾了。”春花撂下打麻绳的拨拉锤儿,挺着大肚子站起来,晃当到樱桃树前,扒拉开叶子,挑着楞青楞青的樱桃往嘴里划拉,巧姑看了,“你不酸啊,吃的人家直倒牙冒酸水?等樱桃熟了,叫你这吃法,都成秃老鹰了?”春花回头对给她跟她长得一样的小丫头小凤拿篦子篦着头上虮子的巧姑说:“酸儿辣女,再酸的,我吃着可甜了?巧姑你不来点儿,也好给二娃生个淌大鼻涕的大小子!”巧姑一心专注地篦着小凤的头,说:“我妈和婆婆得意小丫头。二娃说,他家一窝穷小蛋子,生淘!丫头好,柔柔媚媚的,他想要一窝呢。”春花坐下后,拿小指盖剔下牙,扫下扒着小葱的小樱桃,撩逗地说:“小樱桃,你熟透透的樱桃了,咋生了个二牛就没动静了呢?你那死鬼是不是不稀罕你了,还是咋的叫野娘们偷油喝干了精?”小樱桃扫下低头纳鞋底子的云凤,剜着春花说:“你瞎耪耪啥呀?谁向你,猪似的。这眼瞅着,又一个双黄蛋儿又要露脸儿了。你那俩牲口玩意儿,轮着番的,啥盐碱地老那么追肥,也成了肥地,别说苞米带豆角了,啥庄稼不长啊?咱可不行了,一棵树勒小绳,咱那死鬼贼儿贼老瘦的,又天生的鳖货,鲶鱼将咕哒嘴,上哪不清碗儿去?”巧姑说:“小樱桃,这倒好了。瞅你都二十好几的小老娘们了,还像小姑娘似的,心眼儿就不会活泛活泛,找个拉帮套啥的,借鸡下蛋偷种生子呗!”小樱桃抓把地上的小葱抽打巧姑,“你个小骚蹄子,净不往好道上想?毛驴不甩鞋,我哪敢往那上想啊?你还别气我,不是咱吹牛皮不上税,咱要邪一邪,小腰儿扭一扭,胸脯嘚一嘚,屁股歪一歪,那熊玩意儿,一筐一篓的,那还用拿鞭子赶呀不多了去了啊?到了了,可有一样儿,孩子找哪个认爹去呀?咯咯……我小樱桃啊,这辈子,那死鬼也不学好,咱也指望不上,就靠守着我儿子二牛过了。哎,我不像你们老爷们都哥们,你们姐妹处的就跟妯娌,春芽嫂子,回老家又有年景了,也不知啥时再回来,我还怪想她的。”春花撩起大花绸布衫子,看看锃光瓦亮的肚皮,“小樱桃,你别哪瓜儿不甜摘哪个了?从哪旮论,搁哪处说,你才见春芽嫂子几面呀,就烧包了?我们跟春芽嫂子,就跟亲嫂子一样儿,啥时来没音儿,走了,都哭得眼睛跟兔子眼儿似的。关里那头,蜡花大姐费劲巴拉的才生了个亲生的小子,没两年赶上瘟疫,没了。蜡花大姐不愿再看那心酸地儿,连捡的妮妮一家子三口也来西街了。蜡花大姐夫不跟黄县县城哪个师父学了点儿武把操嘛,在平安大戏院子当把总,给人家看场子,老家就剩公婆老公母俩儿了。那老俩口也是嘎巴土的人,不还有那几垧地,不愿来咱这噶达享清福。说嫌乎冷,冻下巴子。这要搁我,冷啥冷,热炕头一坐,火盆一烤,一嗯达,猫冬呗!小鸡崽儿一大窝又都在这噶达刨食儿,老抱子在老窝里待啥劲儿?这就苦了春芽嫂子,提溜个没蒸饺儿大的小饺子脚儿,跩和跩的,鸭子似的,两头扯拉,这不孝顺哪!”云凤从孩子嘴里拽出焐着的大烟袋锅子****,把孩子放平在大腿上,搂上大衣襟,扣好襻扣,说:“人都有老那一天,这要摊上我们那条街刘大麻子几个狗崽子,谁都够戗,游手好闲的。刘大麻子的大老婆大倭瓜,头年不大病一场吗,几个儿子也不着家,连问都不问一声,要口水喝,那小老婆二妈都使脸子。多亏大倭瓜姑娘麻妞勤往娘家跑跶,算没饿死在炕上。拉了、撒了,都是麻妞,大冬天的,又洗又涮的。姑娘是妈的贴身小棉袄嘛,还是有个姑娘好。那刘大麻子也败家,爷几个合伙的败活。祖上留那老些地,今儿个押出去,明儿卖的,也快折腾得不差啥了。这也是养儿?根不正,苗儿能正道,长的都是大乌縻!”巧姑篦完小凤的头,叫玩去,帮小樱桃摘着小青菜说:“乌縻炸酱好吃啊,再来两碗大豆烀的大碴子,那才叫一个香呢!哎云凤嫂子,牛二哥可是个独苗儿,牛二叔婶子可老夸你呢,你还是多生几个小蛋子吧!牛角、牛蹄儿、牛尾、牛耳、牛鼻儿、牛眼的,把牛身上的零碎挂全生个遍。”春花嘿嘿地说:“巧姑,你还有两样关键的没说,牛……灯笼挂儿呀!”抱着睡着三牛的云凤进屋放孩子,顺道顺脚踢了巧姑一脚,“你撅达钩,想钓我的大嘴儿鲇鱼啊?”巧姑从板凳上翘翘屁股,“噗——”,一个屁,云凤嘿嘿乐地扭达开说:“没舌头,秃噜的挺响啊?像似本地口音,还带点儿黄县味!”巧姑扭侧脸儿,冲走进后门里的云凤喊叫,“你舌头长,一口哈喇子,含着牛二哥那大茄子还会说人话?”几个小媳妇一阵大笑。
二牛一头的汗,灰土抹巴个小花脸儿,手捏个玻璃溜溜,直奔小樱桃跑来,叫着,“妈!妈!大鼠、小鼠老向着大牛、小牛,欺负我!明明我弹进坑里的溜溜,是我赢了,大鼠硬说是大牛赢了,小鼠还帮狗吃食?妈,你管不管?你不管,等牛二干爹回来,我叫他揍大鼠。”小樱桃抹着二牛脸上的灰土,从屋里走出来赶上的云凤,摸着二牛的头说:“二牛,别勒大鼠小鼠那两活兽,八、九岁了,也不知哄弟弟们玩儿,就知个个儿傻?二牛,去跟小牛弟弟玩儿。要饿了,锅里有现成的白面豆包,个个儿拿,先垫巴垫巴。一会儿,大娘给你炖鱼烀肉吃。啊,去吧!”巧姑瞅着二牛蹦蹦跳跳地跑开了,“云凤嫂子,这二牛真听你的话。”又看着小樱桃说:“咋那么像。我咋瞅二牛咋像牛二哥。樱桃姐,二牛不会是牛二哥的吧?二娃说,你俩可好过!”小樱桃脸像熟透的樱桃,腾一下子红到脖子根儿,眨巴诱人的小双眼皮儿,窘迫的瞅着巧姑,尴尬的扫下云凤,憋憋小红唇,云凤满嘴生风地说:“巧姑,瞅你长得漂漂亮亮的,咋一肚子的泔水?你糊涂粥勾啥芡哪,二牛本来就是牛二的。二牛一直管牛二叫干爹!妹子,你还是嫩,啥不懂?小孩子跟谁亲,就长的像谁。哼,我还巴不得小樱桃跟了牛二呢,知根知底的,咋也比那不认识的****贱货强?现在这大老爷们,有点儿掏粪能耐的,哪个不是娶仨带俩的,不稀奇!我们牛二如今也是堂堂的德增盛大商号二掌柜的了,小樱桃跟了牛二也不屈得慌。小樱桃,你说是不?”云凤这刀一样的嘴,削豆腐的话,叫小樱桃漂亮的小脸蛋儿火燎燎的,浑身发高烧的滚烫,瞟了一眼云凤,“云凤嫂子,你不是发醋疯呢吧,正理歪说,我哪有那福份哪?再说,当初我俩好,也就一个圩子住长了,嘎巴的好。可老天爷不长眼,我爹眼睛又钻进钱眼儿里了,哪看到牛二哥的今天哪?我俩是有那情,没那份?人家牛二哥眼目前,威风凛凛,又有你贤惠的云凤嫂子,还咋能瞧上咱了?我已是拉拉蛄盗过的老娘们了,那漂亮还会拿情的黄花大姑娘有都是,上赶巴叽更多了去了?就云凤嫂子容得下我,我个个儿还容不下我个个儿呢?至于二牛像还是是牛二哥的,嘴长在人家的嘴上,叫人说去呗!只要云凤嫂子不嫌乎,搁得下,咱咋的都行,没说的。”春花从拨拉锤上往下缠着打好的麻绳,一撇嘴儿,“就是。我那会儿叫大鼠小鼠他俩爹那俩兽在苞米地给祸害了,还说啥,也就认了。肚子一天天的鼓溜儿,说三道四的风言风语,就像老北风,灌得我的耳根子生疼?这又一女嫁二郎,那可就是老北风夹冰溜子了,我咋的了,说去呗,我又没偷贼养汉子?小樱桃,别管它,谁愿说谁说去?”云凤纳着鞋底子说:“小樱桃,我这人说话,口对心,心对嘴,说的都是真话。我要有一句假话,我都是王八那么大个儿的。你今儿把你那死鬼蹬喽,我明儿就给你操办。咋样儿?我云凤说风就是雨,把话扔给你,绝对不吃后悔药!我告诉你小樱桃,你人越敞亮,越招人待敬。你越夹夹箍箍的,大老爷们心里就越烦。这一烦,好嘛,就偷鸡摸狗了开始。你说,春芽大嫂子为啥家里外头都得意,还不是想得开?咱女人做人这一条,就得拿得起放得下。家里的容不下,那爷们上外头跑骚你就容得下了?都说眼不见心不烦,那都是上坟烧窗户纸——糊弄鬼!咱德哥,你听说他逛过埋汰地场了吗?哪个爷们不骚,人家在个个儿家猪圈里打圈子,你谁还说啥?这又保了爷们的名声,咱女人也不丢分!像吉老二,美娃一是想儿子二是又恨个个儿爷们,弄得个个儿一身的病。就想不开。再叫吉老二说一房,不勾住了人,又生养了孩子?管谁生的呢,你是大房,还不叫声大妈啊?小樱桃,咱家这老二的位,我给你留着,别像我那小姑子似的,老踅摸丘的。”杏脸桃腮的小樱花没吭声。春花乐得捂着大肚皮,“云凤啊,天上掉大金饼,呱唧,砸人头上了。可你这踅摸丘的,可有点儿那个啥啊,左敲门,右敲框,点人眼?哎,我雇你开个醋铺子,给你个顶身股,准赚钱。拥乎你不吃醋啊?”云凤剜哧着春花,“还顶身股,美的你?我要开铺子,先把你家的土狗子和土拨鼠肚子灌饱醋,俩人打得头破血流的,瞅不把你撕个稀巴烂的?”春花把缠好的麻绳团递给云凤说:“嗯,我才不怕呢。我家那俩个玩意儿天生就不会吃醋,有谦有让的。时不星的有那么一两回,过屁功夫就好了,又好的咋是的。”云凤看了看麻绳,“打的不错,匀溜,比我强?”就把麻绳团扔在盛针线的柳条笸箩里,又从柳条笸箩里拎出一桄麻蓖子,站起来抖了抖,挂在头上的杏树杈上,“春芽,你这对双棒儿如今都当上了掌柜,不像先前穷,哥俩说一个老婆不砢碜?你要舍得,抓阄,一个守你,一个再娶。我帮着张罗,还不都上赶着呀?何苦呢,让两个老爷们爬哧来爬哧去,腻腻歪歪的,多膈应人哪?”春花把麻蓖儿一头拿嘴唇抿一下,纫至麻经头上,手高吊着拨拉锤,旋转一下,手指捻捻的,“可不是。咱说过多少遍,可那两个熊玩意儿,不听!苦厄呀,我也没啥法?”小樱桃投洗完小青菜,对云凤说:“我去整饭吧!一会儿,大爷、大娘就该回来了。”云凤说:“还得阵子。晌午在莲花庵那疙瘩蹭顿斋饭,咱们整喽咱们吃。唉,自打鱼鹰爷爷和那老蒯搭上伙,大丫儿就带着小德去莲花庵陪伴文静师太了。说是带发修行,不用剃度。这都是扯由子,还不是放不下德哥?这可苦了小德,七、八岁个丫头片子,整天搁庙里转悠,早晚还不是个小尼姑呀!你说也怪了,文静师太本来个出家人,四大皆空,可挺有人情味的,可稀罕小德了。八成德哥那年叫瞪眼完哥们闹腾那一把,兴许真有骨血那回事儿,那大丫儿可算尽孝了。嗨,人呐,真就各有个的活法。这不惦记姑娘,整得老公公老婆婆三天两头就赶个马车往庵里跑,拿咸鸭蛋、小鸡蛋、小青菜、米面啥的送去,拐带老爷子老太太也磕头阿弥陀佛的了。”巧姑说:“大丫儿也够觉牙的啦,嫁给德哥算了!这何苦的呢,啥时是个头啊,文静师太也不劝劝?”云凤说:“那可不是?文静师太苦口婆心的劝了多少日子,大丫儿就一根筋,认准一门了,套九头牛也拉不回来。这不,文静师太没辙了,就收留了。净管唠了。小樱桃、巧姑你俩先生火,把粳米饭焖上。多焖点儿,待会儿下地的劳金就回来了,他们可能造了。鱼鹰爷爷一大早在咱圩子下坎儿起网,送来两条十拉斤大鲤子,全炖了。粳米饭吃大鲤子最对路。对了,牛二昨晚拿回半扇前槽肉,咱再来个猪肉炖粉条子,也让孩子们拉拉馋?”春花扶着杏树站起来,一手拎着拨拉锤儿,一手按扶着后腰,嗯哒个个儿两小姑娘,“大狗、小狗你俩个小丫崽子,六、七岁了,好好和小凤玩儿?”又问蹲在后墙根儿从青薅草包里掏鱼的云凤,“听说你家水稻种的不老少,长的咋样儿啊?我公公和婆婆吵吵巴火的明年也要种呢。”说完,从浇地浇树的大水缸里舀两瓢水,倒在大泥瓦盆里,靠着门扇框边儿,瞅云凤手脚麻利的磕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