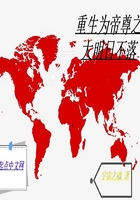吉德、大丫儿和牛二心知肚皮,找必须找,是咋找,上哪找?
二掌柜一看这帮小子要打架,忙问清咋回事儿,二掌柜听后,“别急,这事儿蹊跷?这谁扔的孩子也蹊跷?这孩子没的也蹊跷?如果这个孩子是扔的,这是扔孩子的人家后悔了,盯了很久,欻空把孩子抱回去了。这种可能,有!如果是绑票,这大白天的,有可能吗?那得多胆儿呀,胡子窝啊?可你再琢磨,小德有八、九个月了,认人了。这生人抱,要是没睡,肯定认生,得哭闹。要是睡了,生人抱走,村里都有路卡、巡哨,没那么大胆儿,敢在大白天明晃晃的,把一个孩子抱走?这得是知根知底儿的,对周围环境了解的,又熟悉孩子的人,抱走的。这就有另外个原因了,兴许、兴许……这孩子最拖累的人是谁,大丫儿!大丫儿,是长的俊,可不是妙龄了,已二十了,早过了出门子年龄了,捡个孩子带,又不是私生子非得带着,这对她往后的前程、名声,谁最不愿看到呢,这就不言而喻了吧?这,排除扔孩子人家抱走孩子的可能,谁最不希望大丫儿带这个孩子呢?”
彪九说:“我就不希望大丫儿带这孩子,可我没抱走这个孩子?”
大丫儿此时悲痛欲绝的已不能自持,不理智的说:“你不打自招了吧?你说你回来送菜,那是糊弄大头鬼呢?是有人名声大了,怕小德损害那人的名誉,才下此毒手?”牛二知道大丫儿指的是谁,扯下大丫儿,吼叫的制止,“你疯了?乱咬啥呀?”大丫儿拧把到嘴鼻涕,又抹两下脸,指着彪九发疯的喊叫,“你,你受人指使,趁我不在,抱走了小德!”说着,虎一样的就扑向彪九,“你还我孩子!你还我的小德!”彪九拿手抵挡的往后躲,“大丫儿!大丫儿!你不能这样儿想,我喜欢归……”大丫儿两手抓住彪九的头发撕打,“你猪头狗脑子的熊玩意儿,还我孩子?”彪九掐着大丫儿的手,“我冤枉啊!……”
吉德大吼的从后面扯开大丫儿,搂抱在怀里,恸哭地说:“大丫儿、大丫儿你错怪人了?你德哥最疼你,更疼小德,谁也別想伤害小德,俺这去找。找不到小德,俺就跳松花江,还你个……”大丫儿对着吉德,两眼瞪得溜圆,直勾勾的,哽噎着,“还我的小德!小德,小德……”
“大丫儿!大丫儿!”大丫儿昏厥在吉德怀里,吉德和众人撕心裂肺的大喊,“大丫儿!……”
“掐仁中!掐仁中!”
二掌柜喊着,撺上一个念头,没料到一个捡来的女孩子,对大丫儿会产生这么大的亲骨肉般的惨烈悲痛,这孩子来路太蹊跷了,叫二掌柜百思不得其解,难道另有隐情?
大丫儿在呼喊中苏醒过来,一手抓着吉德,一手抓着牛二,惊恐的瞪着迷惘的大眼睛,“小德!小德呢?小德……”
牛二不忍的刷刷落泪,把头扭到一旁,不敢面对大丫儿那失望而又可盼的眼神。吉德抱着大丫儿的头,哭着安慰着大丫儿,“小德会回来的,啊!”
“这么闹扯,小德是回不来的,咱得马上找。上哪找呢?”二掌柜叼上烟袋吧嗒一口,“依俺看,华山一条路,就到那最亲近的人,或者跟最亲近人有关的人,亲戚了,朋友了,去找!”
二掌柜的话,提醒了牛二,想起那天晚上,妈妈忧忧的眼神,霍然的扒开大丫儿紧攥的手,“骑马上车,回牛家圩子!”大伙儿不解的没有动,吉德明白的抱起大丫儿,“快!快呀!”
月皓云急,风魔兮兮,马蹄碎碎,芨芨草动,颗颗心火,狂驰希望。
“吁!吁!”
狂奔烈马刹住四蹄尘烟起,窗内灯光惶惶颤栗,牛二一跃马下,跌撞似爬的冲进屋里,牛二爹妈惶惑的瞪起四眼,盯着牛二肆无忌惮的乱翻乱蹿,东屋西屋,厦屋厢房,牛二爹妈张着大眼问涌进屋的大丫儿和众人,“这咋啦”
牛二手拿马鞭往炕沿儿一排(piā),“咚”的倚在墙上,两眼瞪着爹妈,“说吧,把小德藏到哪去了?”
“小德?”牛二妈疑惑的瞅着众人期盼的眼神说:“问大丫儿呀?”云凤也符合地说:“是啊,问大丫儿呀?”
“妈,小德不见了!”大丫儿扑在牛二妈身上,出溜的跪在地上,抱着牛二妈的大腿,痛哭的乞求,“您老开开恩,还给我!”
“这咋说的呀?”牛二爹扒瞪两只老眼,惊诧的起来跪站在炕上,两眼角和脑门子皱起的皱纹弥缝里,聚拢着蒙受诬赖的波光,烟袋锅从嘴中滑掉,“啪”掉在炕席上,燃焰的烟末崩得火星四溅,“咋来管咱老俩口要孩子呀?我俩从镇上吃完席,彪子送咱回来的。咱眯了一觉,喝点粥,干坐着,没上哪去呀?”
“小德不见了,不管你俩要管谁要?”牛二腾的站起来,拿鞭子敲着炕沿大声吼着,“你俩不想叫大丫儿带小德,怕大丫儿不好找婆家,这就是嫌疑?”
“二呀,话可不能这么说,你可冤枉爹妈了?”牛二妈一手抚摸着大丫儿头,一手抹着脸上流个不停的眼泪,“孩子抱回来了,爹妈没说一句不赞成的话,还欢天喜地的当亲外孙女一样稀罕。你爹还舍老脸,叫人嘁嘁嚓嚓的匀羊奶喂小德。爹妈知道大丫儿的心思,哪能干出那缺大德的事儿呀?”说着,一堆缩,抱过大丫儿的头恸哭数落,“我可怜的姑娘啊,你咋命这么苦呀,都二十了,捞扯个小德,咋还这么不顺,出这岔气的大事……”
“妈、妈!你老别哭了,小德咱不要了,俺听妈的,找个人嫁了。”大丫儿看妈妈确实没有嫌弃小德的意思,更没有为她的前程抱走小德藏起来,就心疼的可怜起妈妈,规劝的嚎哭,“小德呀,她压根不该来到这个世上,我不该带她,这是老天报应你姑娘啊!脚上的泡个个儿走的,妈你就放宽心,咱不想小德了……”
“你疯啦丫头啊?”牛二妈哭喊着。
春花拿没汤的奶子,叫小德咂咂着,“你俩这是作孽呀这是?大丫儿不知咋着急呢?这人家大丫儿捡孩子愿养着,关你俩啥屁事儿?牛二喝点儿酒,是对大丫儿捡孩子养不高兴,可没叫你俩偷走人家孩子呀?这可倒好,还偷家来了?你俩养着啊,还是咋的?再说了,一个圩子住着,哪有不透风的墙,这要叫大丫儿知道了,还不吃了你俩?我看哪好心做到底,趁大丫儿没觉景,趁天黑,找个人家,远远的,送了。可别搁在家里,这得惹多大祸呀?”
“不送不送!”大鼠吖语的倚在春花身旁摸着小德的小胖手,嗯嗯的喊叫。
“妈,妹妹好玩!”小鼠站在春花腿前,够够的摸着小德胖嘟嘟的小脸儿,稀罕的说。
“不送,拿你俩喂呀?”春花嗯怠大鼠和小鼠。
“大丫儿姑姑,喂小德咂咂吃!”
“瞎说?姑姑……喂咂咂……哎呀妈呀你俩死鬼,我就说嘛,大丫儿那两玩意儿咋像带孩子妈似的,鼓鼓挺挺的那大?哎呀这小德,八成是大丫儿生的。我就纳闷吗,这要喂的孩子,咋会裹咂咂这个上溜呢?你瞅瞅,还真哪像啊?”
蔫头耷拉脑的土狗子和土拨鼠,一下来了神,就春花手里端详着,“是咧!那鼻嘴,那小脸蛋儿,妈呀还真像!这小眼睛?像,像谁呢?”土拨鼠扒扒的瞅下,“像谁?像那野爷们呗!”
“对呀!大丫儿生孩子,哪来的种啊,不会是你俩扒洞的地老鼠吧?”春花纳闷的晃脑袋桄眼珠子嗤笑,“这大丫儿呀,一向眼眶高,谁谁也看不上,还有这一手呢,偷鸡摸狗的,真看不出来呀?”
土狗子一眼不眨的叮叮端详小德老半天,像明白啥了,“小德?”一巴掌“啪”拍在自个儿脸蛋子上,窜下地,“德哥,老大干的!”土拨鼠不敢相信个个儿耳朵的“呱呱”拍了两下,“吉德?小德!这名不明了?老大,就是小德那个野爹!”春花搂紧小德的在脸上贴贴,嘻嘻地叫喊:“合着你个臭丫头,是德哥的大千金呀!大丫儿呀,真有你的,好眼力!不亏,值!德哥,谁呀,大爷们!那多稀罕人,哪个有点儿女人味的谁不想啊?春花哪也不比你大丫儿差,论长相还是论俏皮,那要美美的搂在一个被窝里,啊,那一啥,嗲声嗲气的一嗯唧,多贼贼的逮歪呀?”春花忘情的忌妒大丫儿,尽情嬉闹地唱开了贵妃醉酒戏文,“醉在君王怀,魂归大唐梦啊……”举着小德在地上转了一大圈儿,又放在眼前,仔细瞅了又瞅,“这是德哥的丫头!德哥又有了一个丫头。”土狗子喝斥春花,“瞅你乐的损样儿,像似你亲生的?望穿秋水了,眼馋大丫儿了是不,是不想当大丫儿第二?这是个丫崽子,月娥给老大生了个大胖小子,你傻不傻?”春花愣眼说:“是吗,没听说?”
“别傻了,送回吧!”
“送?往哪送?”
“是啊,往哪送?”
“哪抱送哪去呗!”
“走吧!”
“我不去!”
“你不去,谁去?”
“你去!还两肋插刀呢,出的馊主意?这回这一脚,踢到装牛角的地场了吧?”
“不是我抱的。谁抱的,谁送!”
“就能背后捅尿窝窝,好汉做事好汉当,我送就我送!大丫儿要敢吊腰子翻脸,我就把她和老大她俩的砢碜事儿,抖落出去,看臊谁的屁股?不要脸!”
土狗子一想起在麝香沟上暗门子仙草的炕,叫牛二发现他偷拿了花市布,吉老大悄悄赎回布放回原处,没叫他丢面子,这个好,滴水之恩,他老搁在心里感恩。“这事儿,哪说哪了,咱只是听大鼠一说,谁见了?我告诉你大鼠他妈,这事儿别嘴快,搁在肚子,烂了,臭了,千万千万,别咧咧出去!你那老娘们嘴咧咧啥都行,咧咧出个孩子我也不管,就这事儿不行?”土拨鼠点点头地说:“哥说的对!咱是德哥的铁杆儿,松花江上拜过把子,起过生死的大誓,德哥这是个丢人的埋汰事儿,说出去,杠那些坏种的舌头,咱也跟着丢人现眼?我去送。大丫儿要咋收拾就咋收拾,我都认了。”春花也冷静,安慰地说:“去吧!大丫儿不急成啥样儿了?当妈的,说捡的,是拿酱缸帘子盖脸,那是幌子,心里不知咋着急呢?这说捡的,要不咋说,好听!其实,这里大丫儿有难说出口的苦痛,兴许这里还瞒着所有人呢,就她一个清楚。你哥俩都去,好有说词。咱确实是觉得大丫儿一个姑娘家带个捡来的孩子耽搁了,为她好,就想了这个损招,好心办个错事儿,愿打愿挨,就大丫儿一句话。”
“我也去见姑姑。”大鼠拽着春花的衣襟吵叫。
“大鼠这话倒提醒了我,不用去老鱼鹰家了,省得见着大丫儿难为情,直接去牛二家,编个理由,把小德交到牛二妈手,你们就撤梯儿。”
土拨鼠抱着孩子,和土狗子鬼鬼祟祟的去了二牛家。春花不放心,大鼠小鼠也闹着去,春花就尾后跟着。
吉德从地上拉起牛二妈和大丫儿,苦劝的安慰着。牛二妈拉着吉德的手,“德子啊,你就是妈的亲儿子,好好照顾好你这个妹子呀,别骟了妈的心啊!”吉德说:“俺的心,跟妈一样,会好好照顾妹子的。”
二掌柜这边脑子一直转个不停,他相信个个儿的判断,不会错。排除了牛二爹妈,那就在牛二这伙小哥们身上,“咱别等了,在圩子你们小哥们家找找,这兴许……”牛二脑子马上回想起在土狗子家喝完酒后,土狗子送他时说的话,‘我会叫你当不上这个舅,背那黑锅?’
“土狗子!”
牛二扒拉开挤在屋门的众人,朝外跑。众人也向悟到了啥,也呼呼啦啦跟着。牛二出门,一眼看着土狗子和土拨鼠抱个襁褓进院。
土狗子和土拨鼠走到牛二家门口前,看见好几匹坐骑和马车,就认出了是谁的了。他俩胆怯了一下,说了两句这祸惹大了,还是硬着头皮进了院子,碰巧就像约好了似的,看见牛二喊着“土狗子”气冲冲的冲出屋,和后面灯光焐下的众黑影。
土拨鼠腿一软,抱着小德跪下,双手托着襁褓。大丫儿跑过来,一愣的往后挓挲一下,好悬没跩倒,牛二扶了一下,大丫儿疯子一样,抱过孩子,呜呜的贴在脸上,猛然站起,照土拨鼠脸上“呱”重重打了一大巴掌,扭头跑回西屋。
大鼠、小鼠蹬上窗下倒扣的花筐,趴在他俩在窗户纸偷偷抠的两小窟窿,“小鼠看,咂咂!”小鼠舔着小嘴唇,把嘴贴在大鼠耳朵上小声的馇咕,“妈妈为啥不叫咱俩吃咂咂了呀?”大鼠蹭下了花筐,拉下小鼠,“走,找姑姑吃咂去!”
这寸节,老鱼鹰赶着毛驴车在门口下车,就冲院子里嚷嚷,“大丫儿呀,我想起了啥,我梦里恍恍惚惚梦见,是土拨鼠把小德抱走了!”老鱼鹰坚信不疑了,“是土拨鼠干的。”
土拨鼠跪在地上,牛二等一帮,木呆呆的站着,不说一句。
“这咋?”
二掌柜上前搀着老鱼鹰,喊着说:“老人家你费心了,土拨鼠把孩子送回来了!”老鱼鹰说:“我说吗恍惚的是他。”老鱼鹰似想有点儿啥的,个个儿磨叽,“不对呀,这大丫儿还不得恨我没看好小德呀?这要结了怨,再不上我那去了咋整?这都怨这鼠眉鼠眼的,欺我老了,多贪了两口,才偷走了孩子。”一想,生了大气,拿驴鞭子指着土拨鼠,“损兽!你拍花子啊?你算哪根葱哪瓣蒜哪,安的啥心,偷孩子想捣腾卖钱呀?”说完,举起驴鞭子,云凤没拉住,照土拨鼠就抽了下去,“我非抽死你这个无恩无义缺八辈大德的狗玩意儿?”土拨鼠抱头躲躲的就想挨这鞭子,为好心办错事儿付出皮肉之苦的代价了,以解脱好心给大丫儿造成的伤害和众人对他的误解,“啪”一驴鞭子是抽了,是抽在铤身而出春花身上,“鱼鹰爷爷,你老糊涂了,咋不识好人心呢?大丫儿一个没出门的大姑娘家,带个捡来的小孩子往后咋整?土拨鼠是为大丫儿好,才下四滥的抱走了孩子。谁知道大丫儿这么上心这孩子,要早知道这样儿,何苦呢?”
“哪有勺子不碰锅沿的,都是好心。”二掌柜安慰春花一句,“还疼吗?”
“啊,要这么说,我还真错怪了土拨鼠了?”老鱼鹰撂下驴鞭子,“这孩子是……”老鱼鹰瞅瞅吉德,把话又咽下去了,蔫巴了。牛二感激的扶起土拨鼠,拍拍土狗子,“是牛二哥的不对,叫你俩遭这不名大罪。”
吉德两眼里含着话,擎着的泪花像天上星星闪闪颤颤的,他歉疚疚的拍拍牛二,又一苦笑的碓土拨鼠一杵子,“大哥对不住你们了。”吉德又对春花笑笑,“抽疼了吧?你够一说。能为土拨鼠扛这一鞭子,足见土拨鼠在你心目中的份量。你又一语惊人的道出事情的原委,误会解除了,做得好啊!不是德哥说笑,要不这对双棒儿,咋会死皮赖脸的吊在一棵梨树上守着两大牙梨呢,还是春花有夺人之处啊?”春花受宠若惊的低下头,感动得掉下两滴眼泪,心说:咱明白了,大丫儿为啥一意孤行的跟着你德哥呢,就这一句话,说得你人心暖暖的体贴,红颜知己啊!这谁摊上了,谁也舍不得撒手啊这个?
彪九觉得心里酸酸的,自语说:“这变戏法的孩子失而复得,要找不到,我得遭一辈子窝囊,替人背一辈子黑锅!”
“姑娘,妈和爹就守在门口,有事儿招呼妈一声。唉,可怜哪!”牛二妈和牛二爹心疼姑娘,不想离开的守在大丫儿门口,大鼠和小鼠拉手扭扭的要进屋,牛二妈哄着的不叫进,“小妹妹睡了,明儿个再玩。”大鼠张扬个小鼠眼的对牛二妈说:“牛奶奶骗人,小妹妹吃咂呢!”牛二妈想捂住大鼠嘴,已不赶趟了,叫牛二爹听得真真切切,“嗨,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啊,这丫头?”牛二妈嗳叹声,推推牛二爹,“谁这一辈子不留点儿遗憾事儿呀,哪有那十全十美的。咱这丫头就这命,任性,挣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