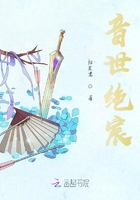“这定单从时间上看可不小啊二掌柜,行啊!”殷明喜赞成的从桌案后站起来,走到二掌柜跟前,手搭在二掌柜肩上,乐呵呵哈腰低头问:“二掌柜,这又盖房子,铺子又要开张,还要迎娶小鱼儿,那钱呢?”二掌柜抬起眼皮,抹脸地说:“问俺?俺还问你呢?”殷明喜一甩二掌柜,走到吉德面前,“想法归想法,巧女难做无米之炊呀?一万多块啊!”吉盛一旁说:“大哥空壳了,大舅就掏掏腰包呗!”殷明喜挪到吉盛前,一脸的无奈,“俺是想掏啊,多好个赚钱机会呀?一是你大哥独立,从不沾大舅钱的边儿;二呢,大舅也难啊,这冬天快到了,咱做皮货生意的,一冬赛一秋啊,眼瞅着要收皮子了,那也是一大笔钱哪?咱把上皮子的钱,拿给你大哥,那叫不务正业,舍了西瓜捡芝麻,不可为呀?”吉盛失望了,“大哥,馒头扔锅里,泡汤了!”二掌柜说俺说个馊主意,“找找钱大掌柜,把房子押上?”吉德笑笑,“二叔,那得拿利息,就增加了成本。粮食这玩意儿,一斤无利,十斤够本,百斤利薄,大宗才有赚头,必须得精打细算,一粒儿一颗的抠。大舅,俺没有弯弯肚子,也不敢拿镰刀来吃。这钱,俺倒有一笔,四、五千块,都是叮叮响的现大洋,放在钱大掌柜的钱庄里。两三年了,俺都没动。”吉德这话一出口,叫殷明喜和二掌柜连吉盛都傻愣愣的,半晌没喘一口气。
“大哥,你使劲掐下个个儿,疼就是真的,不疼就是想钱想疯了,异想天开,吹牛!”吉盛从座上一步倒一步的凑到吉德前,够够的,“哎,大哥,掐呀?”吉德瞟一眼吉盛,“你傻呀,俺掐?猪咋死的,笨死的!”吉德喝一口铁观音,清清嗓子,噗嗤笑了,“大舅,这事儿吧,挺蹊跷的。一直瞒着你,没敢说。你记得大前年冬,俺跟你说俺捣腾的麝香吧?俺没跟你说,这当中,大车店喂马的跑腿儿,受一个卖人肉的娘们唆使,晚黑在窗户外吹了熏香,把麝香从土拨鼠胯裆里偷了。偷了后,连夜和那娘们坐马爬犁跑了。半道上,那娘们早和人串通好了的,把喂马的绑了,捆在外头大树上冻干了,那人独吞了麝香。那个人当时就把麝香,一手钱,一手货,卖给了等在那的一个洋人了。那年麝香不火吗,卖的价很高,交易完了,两伙人,一个拿钱,一个拿货,猱了。那个娘们哄骗喂马的,说偷了麝香后就和他远走高飞过日子。其实啊,那娘们另有打算,也叫那人哄骗了。那人是哈尔滨良大掌柜大药房的外柜,老去麝香沟收麝香,跟那娘们有一腿,是老相好。俺抢了他的生意,他俩就合谋偷了俺的麝香。可叫那娘们没想到的是,那外柜涮了她,丢下不管了。等土狗子醒来和大熊俺狐狸沟认识的哥们发现了,就臭狗,顺爬犁雪印撵上去了。这之前,不知哪冒出两个神秘人来,从土狗子他们身边儿擦过,不大一会儿,那两神秘人,在半道上,把麝香又都给抢了回来,连麝香和那交易的大洋往地上一扔,‘货,完璧归赵!大洋,拿去做买卖吧!’说完,扬长而去,人就不见了。你说,来无影,去无踪,奇不奇?”
“赶说书的了,离奇!”吉盛捏拳头的听完,拍大腿的叫好,“觱(bì)篥(lì)管乐,悠不悠扬的,惊心动魄啊!大哥,那喂马的和那骚娘们你咋整了,揍死他俩?”
“整啥整,那娘们疯了。那喂马的冻的半死,捡了一条命。”吉德说:“俺给那娘们和喂马的扔下些吉钱儿,就去东省哈埠了。”
“哎大德子,俺听你说过,那四个神秘人,你怀疑是曲老三的人?”殷明喜问。
“大舅,俺是怀疑过。打俺被刘三虎绑票,俺就不是怀疑了。曲老三为救俺,不绑了刘三虎的两个小儿子了吗?俺和大丫儿逃出来,在北江沿儿等截船回来,不碰上了曲老三帆船了吗,那四个神秘人在船上露了露头,等俺上了船,那四个神秘人又不见了。这回俺不是怀疑了,那四个神秘人,就是曲老三的人。”吉德说。
“神人也!没那曲老三神秘人护驾,你不可能买卖做的这么顺利?”殷明喜背着双手,踱来踱去,“这曲老三啊,琢磨不透啊?这当初,你哥仨救美,是出于义愤,意在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显出你们做人的正直、正义。你们的莽撞,一时叫曲老三扫了面子,下不了台,他叫鲁大虎抓你们,震怒之余,没有丧失理智,他却很冷静,没有把你们沉江,或咋咋的,却叫鲁大虎把你们交给他干爹老鱼鹰看管。这说明他高傲自恃,没把你们仨傻小子放在眼里,砢碜、寒碜不当一回事儿。在一个当胡子人的眼里这不算啥,尤其你们是外来的愣小子。但这里面却有一点,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在他心里,对你们另有打算。这点,从老鱼鹰偷偷放了你们后,曲老三震怒于老鱼鹰中,看得出来他的某种打算。这种打算,一个是曲老三有鸿鹄之志,网络人才,叫你们入伙;另外一个就是,你们的黄县口音,叫他感兴趣。他这个人当胡子,是叫刘三虎逼上梁山的。他一直有个心结,洗白!后来,事情急转直下。从他想整治老鱼鹰中不难看出,他多么看重你们啊?曲老三这人孝顺,当他知道老鱼鹰认了你们的干亲了,他只有按老鱼鹰的意思了。再后来,他又知道你们是俺的外甥,他不想跟俺在疖子上再结疮,还想对你们好眼看待向俺示好。至于他最终打算,还不得而知。从你和老鱼鹰联手贩鱼,叫他对你另眼相看,并暗中帮你,不惜任何代价,叫你成功。这里头,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那就是江上绺子不同于其他绺子,全民是胡子,又全民是渔民,霸占一方,只求自保。他的绺子,不抢不夺,不吃大户,不取不义之财,所以渔民都很贫苦,捧着金饭碗要饭,也是吃一顿没一顿的。这里的原因是,渔民不会经商,打上鱼,等门上客,卖多少是多少。这时你赊鱼要贩卖,叫曲老三看到希望,你帮了他一个大忙了你?他不好出面说,那太掉他大当家的架,还怕你又记恨又胆怯他,不贩鱼了。另外,他从你的救美人品上看出,你敢闯敢拼;又从你敢赊鱼敢进山贩鱼,看出你有头脑;渔民敢把鱼赊给你,除老鱼鹰的面子外,这里必有曲老三的想法。反之,你不会那么顺利。至于赔挣,那就是看你重信义这点上了。他知道江湖险恶,他不出手,光靠你的热情,恐怕会失手,那也砸了他的锅。这从他给你那支匣子,就看出他当时的心境,保护你,支持你。俺过去由于邓猴子从中挑唆,跟曲老三结过梁子。这疙瘩在牛二的婚礼酒席上都说开了,冰释前嫌,言归于好了。俺历来是反对和胡子来往,但你就在这烂泥塘里,咋能不沾泥?胡子就像贴树皮、赖皮缠。咱做买卖的,你想甩又甩不掉,惹不起,又得罪不起,更躲不起。那咋整,轱辘呗!咋轱辘,得分三六九等,分出好赖,不招惹、不亲近、不依仗、不讨好。咱们这旮子三伙大绺子,鱼龙混杂,刘三虎可恨,王福可恶,曲老三可信。俺说这些干啥,就是大德子这笔钱该不该用?”
“依俺看,该用!”二掌柜拿砣地拍着椅子扶手,“这笔钱,账,当初就记在胡子身上了。另外这笔钱,神秘人就是给了大少爷。再就是,你用不用,曲老三他都不管,心意到了。”
“问问曲老三?”吉盛说。
“问曲老三,他不会成认有这回事儿的。因为,曲老三是暗中相助,不想叫你说他好?你心有就有,没有就拉倒。至于神秘人他会一口否认,不知道?他成认了,那神秘人就不神秘了?曲老三他就是想叫这事儿,神兮兮的。助你一臂,不图报!”二掌柜说。
“不会是下底钩吧?”吉盛问。
“下啥底钩啊?这笔钱,曲老三事先又不知道,是神秘人作的主,又不是曲老三指使的。别乱猜度,拿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曲老三不是那样的人?”吉德反驳说。
“曲老三他说过,他倒有成为一个正儿八经商人的想法。他陷入江湖不能自拔后,他看大德子行,只有支持大德子实现他的报复了。这倒有,这里不能说没有他的影子?”殷明喜说。
“你绕来绕去,这笔钱该用了吧?”二掌柜急咧的问。
“大舅的话,俺听明白了。二叔又赞同。俺想好了,先用。用完了,如数再归回。这笔钱,就作为应急之需,不能算做德增盛商号的股本。那买办先付一半的货款,剩下的运一船结一船,运完结清。缺口这块,钱大掌柜答应帮忙,咱有房产,他一点儿不担心。”吉德说:“俺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拿小麦毛利的五厘,换回老毛子一万根的木头,也可拿一部分小麦顶木材。来回载,船不跑空,运费又省了一笔。一个钱当两钱花,两头赚。这俺也是给杉木下一个眼罩,抢抢他的生意。”
“杉木拿掇你,不卖你房梁,你一趟富锦,倒叫你看到了商机。”二掌柜哈哈地说:“杉木啊,都说东洋人鬼,天机算尽,反害了个个儿,叫大少爷发了财。”
“老毛子的木头,八公尺六公尺长的,大人一抱粗,才一块大洋一根,这里还有赚头。杉木早眼红了。从老毛子那出海,运到东洋多近啊?”吉德说:“可东洋人为了北满,窥视西伯利亚,出兵帮俄罗斯白匪打苏俄红军,老毛子再好的木头,杉木只有眼瞅的份了,叫他望洋兴叹吧!”
“师弟!师弟,月娥生了!” 彪九手拿马鞭,急忙火燎的跑来,“大胖小子,足足八斤多。啊,大舅妈也在。”
“这到日子了吗?”吉德惊喜的站起来问。
“到没到日子我哪知道啊,那得问你个个儿呀?”彪九嘻哈地说着,拽起吉德就走,“你这师哥啊,想占俺的便宜?”吉德高兴的跟彪九说着,连向抬腿就跑,“哎哎大德子,你忘了你大舅了你?”殷明喜合不拢嘴的叫着,腿可比谁跑的都快,“哎哎大哥俺还要采生呢!”吉盛拽上二掌柜,“二叔你也别落后,还抻悠啥呀?”二掌柜咧咧的嚷嚷,“拽啥拽呀,俺的鞋……”
几匹快马,飞驰到了吉德租的小院门前下了马,吉德让着殷明喜,一头跨进堂屋,“儿子!儿子呢?”殷张氏眉开眼笑的从东屋迎出来,挡在屋门口,“瞅你高兴的,唱蹦子啊?大德子你別急,瞅一身的凉风,大人小孩平安!”吉德手上扯着殷明喜够够的就要进,殷张氏挡着说:“一帮大老爷们的咋好闯产房啊,等着。”吉盛擦过殷张氏背后说着,“你们都大老爷们的就别……俺是小叔采生呢还要?”一嗤溜,就钻进了屋。殷张氏扭头说:“这孩子,你采生,那小孩儿还不得跟你一样怕黑胆小呀?”殷明喜指指的说:“是啊,你横扒竖挡的,咋叫盛子进屋了呢,这孩子非得胆小不可?”殷张氏喳喳的,“胆小就胆小,说这干啥,说也来不及了?”吉德问屋里谁在笑,“咋像小鱼儿?”殷张氏说:“小鱼儿一听信儿,就跟俺跑来了。还有艳灵、好灵、蔼灵和爱灵,一大帮呢。”
“哈哈,还谁采生呢,一帮姑姑丫头?”二掌柜靠在外屋门边站着,“这小子,可是长子,将来也是个小情种,一帮丫头采生,那是啊?”
“一帮丫头采生咋啦,那也总比你当叔公公的采生强?”殷张氏抿嘴的说着,“那百灵不是你采的生,还大伯子呢?”
“嗯,你生养也不找个时候,嘎嘎的,三弟又没在家,俺当大伯子的咋整,稳婆子那个叫俺,俺哪管那些了?”二掌柜嗤嗤的辨白,“百灵咋样儿,俺采的生,不是上了高学堂了,还说呢?”
“小宝宝来喽!”艳灵推门撩起门帘,小鱼儿笑得一团花的,抱着露着红红脸庞的孩子出来,“只许看,不许摸,宝宝脸皮儿嫩,别拉着。”
“对对,只许看,不许摸啊!”吉盛探头的附和叮嘱,“包前儿,俺看到了宝宝的******了,还一撅一撅的呢,老好使了?”
“不许瞎说,臊不臊你?”艳灵嗔怪的对吉盛抹着眼,“说啥呢,当一帮丫头面?”
“咳咳,你没瞅啊?”吉盛白下艳灵,不服地说:“一个小孩儿的,有啥啊?”
“小宝宝,睁睁眼,叫爹、舅爷、爷爷瞅瞅吧!”小鱼儿笑着瞅着小孩儿说:“看多俊个大小子呀!”
“来小鱼儿,叫俺这当爹的抱抱。”吉德伸手地说。
“你是爹也不行?你说,宝宝太小,闪着呢?”小鱼儿拿笑眼儿瞟下吉德,喜爱的又瞅着小孩儿,“宝宝,叫爹爹!”
“也不是你生的,就叫俺大哥抱抱呗!”吉盛替吉德争口袋,“那要你生的,还不得纸包纸裹的啊?”
“俺生的,就不叫三叔看。”小鱼儿笑着剜下吉盛,又瞅下艳灵,“你不用急,等你有了,你再抱吧?”
“小嫂,你别急,大舅说,等铺子开了张,就给你张罗。”吉盛逗着小鱼儿,“你想给俺大哥生几个呀?”
“生几个哪能行啊,咱给你哥生一窝!”小鱼儿敞亮的回敬吉盛,“七狼八虎,像杨家将似的。你呢,三弟?”
“媳妇还没有呢,俺哪说了算呀?”吉盛说着,瞟瞟艳灵,“俺有了媳妇,也叫她生个七狼八虎,撵过你?”
“人家月娥生孩子,瞅你俩眼馋的,呛呛啥?”殷张氏笑着,谝哧小鱼儿和吉盛,“百灵他爹,你看这孩子,这眉眼,多像月娥呀?俊!”殷张氏看着殷明喜说:“女儿像爹,小子像娘,也有又像爹又像娘的。咱百灵几个丫头,就又像你又像俺。”
“这小子起名了吗?”殷明喜眨着眯成一条缝儿小眼睛,眼神炯炯的问殷张氏,“俺想好了一个小乳名,大号俺可起不好,那是你们老爷们的事儿。小名吗,就叫心儿。咋样儿啊?这头一个小子,多可心呀!”说后,两手捂着嘴凑近殷明喜耳朵,嘻笑的嘀咕几句,扬眉舒眼的盯殷明喜瞅着,殷明喜点着头,“好!”又小声嘀咕一句,“是得有心!”二掌柜在侧,心里听明白殷明喜嘀咕这句话啥意思。“等满月了,抱心儿到莲花庵,叫文静师太给算算,祈福呗!”殷明喜看着殷张氏说:“那行。文静师太多能哏,算算,多念点儿保佑经。”殷张氏同意的点头。
“哇哇……”
“心儿饿了吧大舅妈?”小鱼儿紧张的得瑟着心儿,心疼的哄着,对殷张氏说,“来舅奶奶抱心儿。”殷张氏接过心儿轻轻悠悠,脸贴在心儿脸上,“哟心儿,饿了也不能吃奶啊,你娘还没下来奶呢。大梅,冲点儿俺拿来的红糖水,别搁太多,太咸,看齁着。”大梅哎声,进屋冲糖水。殷张氏抱心儿进屋,回头说:“这屋窄巴,栖栖的,这儿有俺呢,你们都回吧!孩子要睡了,月娥也该歇着了。回!嗯?”屋门关上了。
“俺去给俺爹娘发电报去!”吉盛跑出屋说的话,叫吉德吓了一大跳,忙拽住吉盛,“你唬啊?爹娘和你春芽嫂子,还不知道你月娥嫂子的事儿呢,捅马蜂窝啊你呀?”吉盛一长长眼,嘴上说:“你还瞒啊大哥,这孩子都生出来了?俺不管,俺得叫爹娘高兴,他二老有大孙子了。”吉德拽着把吉盛搂到院子墙旮旯,压着嗓子,“俺不是不想告诉爹娘,只是不是时候,等俺这段忙活完了,俺回老家一趟,把爹娘和你嫂子接来,那时再说也不迟?你这冒失暄天的,一个电报能说清吗?这生米已煮成熟饭的事儿,早一会儿,晚一会儿,可就大不一样了呀?这爹娘听了,非扔下家不管,来找俺算账!你嫂子呢,听了会咋样儿,那还不作翻天啊?你要想消停,听大哥的,先别叫老家那头知道,俺会摆平的,好吗?”吉盛不屈不饶的耍开了磨磨丢,“你这是欺人太甚?”吉德近乎哄小孩儿的诺言,“俺就求你这一回,往后大哥啥事儿都听你的。啊好三弟,哥求你啦!”小鱼儿看吉盛任性,就走过来拉开吉德,扯着吉盛走开说:“听小嫂的,咱去电报所,拍电报!”吉盛一听,甩开小鱼儿拽的手,往后褪,“拍电报,俺不去?”吉德听见了,也煞白脸的跑上来,“小鱼儿,你想干啥,怕事情闹的不大呀?”小鱼儿笑着瞭一下吉德,拽紧吉盛地说:“走啊?给你二哥拍电报,你不去呀?”吉盛这回高兴的拉着小鱼儿就跑,“蛤蟆大喘气,小嫂你咋不早一堆儿说了呢?”吉德如释重负的拍着胸口,“俺的娘哟,聪明的死丫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