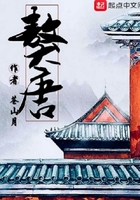云凤干净麻利的拾掇完碗筷,端起炕上的火盆到外头倒掉炭灰,从锅灶里铲出红红的木火炭放进火盆里,满满一下子,用炭烙铁压实,端到炕上放好,不高兴地说:“你们撑五饱六得的了,还想啥呀,烤火吧!关东、关东,有啥好,死冷的天不说,人也驴性霸道的。你们这才搭个炕沿边儿,炕洞子深着呢。油烟子炕洞灰,熏黑死你!有多少老少爷们闯关东的,在码头下了火轮,就叫人弄到江北兴山煤矿上,当煤黑子去了,过着有黑没白的日子。死了,连个白茬薄木棺材都没有,炕席卷儿一卷巴,就跟大煎饼卷大葱似的,扔到山窝子大野甸子喂狼了。所以,这里的狼吃惯了人肉,见人就咬,可凶了。啥肉比人肉香啊,细发白嫩的。这片桦树林子里,藏着一百多条狼呢,饿得白天就敢进圩子里吃小孩,一秋就没了七个。这儿的小孩一哭闹,大人拿狼吓唬小孩子说,张三来了,小孩就地儿憋回去不哭了。”云凤说着,上炕盘腿坐下,瞅着吉德仨兄弟,接着说:“不说这些了,你们也不愿意听,说些打你们牙的事儿。我猜你们现在最往心里去的事儿是啥,逃跑!对吗?”吉德摇着头说:“你猜哪去了?猜的太离谱了?差的比孙悟空折的跟头还远?不跑!这有吃有喝的,啥活不用干,还有你这么漂亮姑娘相伴唠嗑解闷,这好事儿上哪找去呀,云凤你说呢?”云凤一听吉德说的话酸溜溜的,没好气地说:“你是不是酸菜吃多了,我听着咋带酸菜水味呢?我漂亮不漂亮,就是个水裆裤,你不用拿猪胰子当胭脂给我搽,心不对嘴的说那些斜影的话干啥玩意儿呀?说的不舒服,听的也別扭。我好心的问问,你可倒好,当驴肝肺了,不识抬举的东西?”云凤堵气回敬了吉德一句,下地趿拉个鞋就跑到门口,推开门一看,“我说窗户纸刷刷的,啥时下的雪呢?机会来啦!”跑回坐在炕沿上,系着棉鞋带子说:“哎,三个空心柳,鱼鹰爷爷昨晚黑儿,就去地窨子找三爷了,到现在还没回来,不知拥护啥事儿给拖住腿了?八成三爷泡黄豆,鱼鹰爷爷磨上小豆腐,爷俩拿地窨子当烧锅了。你们好好睡一觉,下晌儿吃顿饱饭,天也杀黑了,到那时嗯……再说。”吉德哥仨一听云凤说这话,话里有话,马上眼珠子醮油角,又滑又腻,眵(chī)迷眼了,互相瞅瞅,都没敢吭声问。就云凤那直筒子破烂的体性,咋好伸猪巴子嘴直接问呐?怕一问,吹起的胰子泡没咋的呢,一巴掌就搧破了?搁心里高兴的鼓鼻涕泡吧!
‘噢噢,看来老爷子不是脚底抹油,新媳妇放屁竟任儿躲人,也不是笑面虎背后藏刀,是真心想搭救他们啊!从云凤浮沉不定的样子来看,老爷子筹划的还石滚子没落地,不一定有十分把握。不管咋说,总算从云凤的话里看见了胎儿眉毛,还愁不长眼睛了?’
吉德不死心的,尽量想从云凤的脸上看出点儿啥破绽。可云凤此时却双手捧腮沉默,呆呆地看着窗户发呆,眼神凝重。
老鱼鹰在曲老三地窨子里煎活鱼似的睡了一夜,未见曲志老三回来,就在地窨子里找到冰穿、操罗子啥的,出了地窨子,来到江边儿上,踅摸着那冰茬冻得厚实地场,透着厚玻璃如绿宝石似的冰层,选好凿冰眼的地场,凿开冰,打冒眼儿,弄了半袋子鲫鱼,湿拉拉地扛回地窨子。一瞅,还不见曲老三的人影,见炕灶里啰喽刚攮完的袼囊,一汪汪的炭火,就从袋子里掏出几条鲫瓜子(鲫鱼很像嗑的葵花瓜子,俗称)扔进灶坑,扒拉些炭火埋上,焐烤着。他吧嗒完一袋烟,在炕旮旯捞过一坛老山炮,蹲在灶坑前,拿棍儿扒拉出烧烤得糊巴的鲫瓜子,敲打几下,拿手里烫得两手倒着连拍打鲫瓜子上面的灰土,又拿到嘴边儿吹吹灰,看差不多了,像啃烤苞米棒儿似的,外皮儿脆,肉里嫩,几口下去,一条六、七两沉的鲫瓜子,就剩下一个完整的骨架和内脏,最后咬下鱼头,嚼得脆生响,抹搭几下,咬掉瓶塞,连酎几口酒,哈哈的仰脸吐一口酒气,“妈的,逮杆儿屁啦!”也就一泼屎的工夫,等他再站起来的时候,灶坑前剩下一个空酒瓶子倒在地上,鱼骨架和内脏当柴火在灶里吱吱地撺火的呻吟着。他拍拍羊皮大氅沾的鱼渣儿和灰末,看看死寂闷静的四周,也不等了,背起装鱼的袋子,踏着刚刚下起的雪花,回到了家里。
原先的盘算,老鱼鹰是想靠他的老脸,向曲老三求个情,放了吉德哥仨。现在看来指不上了,曲老三不知啥时能回来,就回来也不一定说了管用。思前想后,下这场雪,这回算老天开眼了,有雪他就好办多了,可施展他的谋划了。他想,夜长梦多,只有当机立断,当一回老大,趁着雪迷迷的看不清人,躲过眼线,放了这仨好孩子。过后老三知道了,发通火也就结了,他敢把老子咋的?这么作不合乎规矩呀,绺子上都这么干,那不是瞎骡子打里儿,乱了套了吗?我不能拆老三的台呀?不拆这台,这仨孩子可咋整,就不救了啊?不能啊,我就充回老大,不,老大的爹!
“咣当”门一响,云凤随声高兴地嚷嚷,“爷爷回来了!爷爷回来了!”忙拿起炕上的糜子笤帚,拍打沾在老鱼鹰羊皮大氅身上的雪屑,“你这上哪旮旯去了,还弄的一身的酒气呀?”老鱼鹰脱掉大氅,捋捋长白胡子上冻的冰茬茬说:“能上哪,在你三叔那旮子嗯待一宿。那地窨子的地火龙,叫小崽子们烧的咕咕热,弄得我一身的汗。”云凤问:“你见着我三叔了,他咋说?”老鱼鹰接过吉德递过来的长烟袋,冲吉德一嘻嘻,逗吉德的狗壳子,“大小子啊,我在地窨子里嗯待一宿,也想着你们看到的好事儿了。可没人喊‘救命’,娘腿的白大白,烙了一宿的大饼子,连个老屁星子都没见着,哪还有那‘救命’的好事儿了?”云凤着急地插嘴,“爷爷你嘻皮笑脸地倒有闲心,说的啥梦话?啥‘救命’不‘救命’的。这不救命,这也是火上房的大事儿?你老冲着啥了咋的,这个没正事儿似的?”老鱼鹰屁嘎地乐着,‘你个臭丫崽子,你哪知道我说的啥乐子的啥呀?’眼光叼着心领神会苦笑着的吉德,“你三叔一杆子支马虎力去了,我连毛都没摸着?踅摸的,就打冒眼打半袋子鲫瓜子,在外面门口呢。八成还没冻实膛,好拾叨,快弄屋来。这冻实了,就不好弄了,还得缓唔的。”云凤一拧达,“这不还是没正事儿吗?你还有心弄鱼去,我可没那心做呀?你不说下雪就有辙了吗,这雪可是越下越大了,你不压出个辙印子,别想吃鱼?”老鱼鹰吧哒个烟袋,一脸的嘻闹,“吓唬谁呀你个臭丫崽子,没那鸡子儿还不做槽子糕了?咱这仨孙子,都属猫的,生吃!”吉增听了,说声俺去拿,人出去拎个袋子返身回来了,“云凤,倒哪旮子?”云凤撇下嘴说:“腿倒快的。猫闻着腥味了,显大包?那你这大孙子显勤儿,就倒到泥瓦盆里拾叨了吧!鱼嘎碎,你可得抠净喽。冰块儿,放那泥瓦盆里,化了好炖鱼。”吉增晃下头说:“哪都有冤死鬼,咋整你都歪楞歪愣的。我是吃过江水炖江鱼,还有用冰块化水炖鱼的?”云凤一歪愣眼睛,“你还知道啥,放屁啥味,狗嚼屎?”老鱼鹰吧嗒口烟说:“这丫头老这样,嘴不饶人。老二,她是心疼你,怕你拔手。”云凤剜下老鱼鹰说:“爷爷瞅你说的。我心疼一个两路世人干啥玩意儿嘛!我是烦他们,没事儿找事儿,惹得爷爷为两方世人着急上火的。那没见着三叔,还得等啊?爷爷,我可伺候他们够够的了,趁早打发了。要留,你给他们弄吃的。不留,往绺子上‘秧子房’掌柜那一交,等三叔回来愿咋处置就咋处置,多省事儿?你说那招,可下雪了,再烙饼还是蒸饽饽,错过机会,面就走碱了?”老鱼鹰说:“看你倒急了,皇帝不急,你个宫女急的哪流子水呀?这要你三叔六亲不认,翻了脸,我的老脸不得钻裤裆啊?这事儿你就当不知,快做饭去,吃饱喝得再说?”云凤朝吉德一挤眼,乐颠的生火做饭。老鱼鹰眨巴下老眼皮,对吉德说:“老大呀,一会儿云凤把鱼炖好了,咱爷几个再好好喝一顿,好聚好散嘛!”这句话一出老鱼鹰的口,说得吉德哥仨是牛犊子叫街,蒙了门!
老鱼鹰抽完烟,倚在被卷眯瞪上了,鼾声“呼噜呼噜”震得破窗户纸唼唼的响。云凤见了,拿大氅盖在老鱼鹰身上。
从打老鱼鹰说出那句云里雾里的话,云凤冷个脸,闷头干活,一声不吭了。吉德蹲在地上跟吉增和吉盛拾叨着鱼,小声地说:“哎,邪性了,云凤咋不喳喳了呢?老鱼鹰那句话是啥意思,好聚好散?”吉盛说:“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不是棉裤薄,就是皮裤没有毛。”吉德训斥地说:“老三,都啥对时候了,你还扯这咸淡话?”吉盛睄睄吉德的脸,蔫蔫地倒了蒜茄子了。
拾叨完鱼,吉德闲下来没事儿,走到窗前,眼瞅隔断视线的窗户纸,仔细打量,琢磨开“窗户纸糊在外”这一显示人类聪明才智的大怪现象。
这奥秘,据当地人讲,这窗户纸不是一般的纸张,是用芦苇、蒲棒、花麻和破绳子“剁绳头子”后,用立起的碾子压,用生石灰块清洗,再挤压清洗干净,拿柳条筐把淌到池子里的料桨捞出,控尽水,碎麻成为筐样的坨,放在大锅上蒸,蒸完碾压,然后放进池子里搅成豆腐脑样儿,拿叫“沙拉子”的二尺半长磨茬小棍“打线”,沉淀后捞纸,码垛,用“压马”压净水份,风干晾晒。又粗又厚的老纸上面,再用胶油勒上细麻条,刷上桐油,无论是草苫的房檐下,还是檩瓦的房檐下,都不怕雨水和潮气。人们管这种老纸叫麻纸,也有叫麻布纸的。你别看这纸不起眼,还是贡品呢。紫禁城皇宫里,也用这老纸来糊窗户。冬天,窗里窗外温差极大,如果把窗户纸像南蛮子地界糊在里面,窗外结的冰霜遇热就融化,水就会流到窗纸和窗棂结合处,如此不仅容易使窗纸脱落漏风,还会造成窗棂啥的腐烂,使用寿命受影响。再者,也是防风。你再大的风咋刮,背后有窗棂顶着。如果糊在窗棂里,兜风,风一刮,就会呼达掉了。因此,满人就摸索发明出这东北一大怪,窗户纸糊在外。
吉德看老鱼鹰的窗户纸,经多年风雨已老化了,桐油出现了爆皮的斑驳。有的地方,斑驳得己花花搭搭的脱落,只剩下麻丝,明显透着光亮。从光亮中,吉德想起阻断他们不能与近在咫尺大舅相见的一堵墙,就像这薄薄一层窗户纸不可逾越。老鱼鹰高深莫测的一句话,勾起吉德蒙冤的伤心和莫测的前景。他想起了老家的爹娘,想起刚结婚的新媳妇春芽,心血来潮,思绪滔滔。心中默默地念叨:‘爹!娘!儿不孝啊!俺违背了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为了己利,抛下二老。原本想成了家,就该立业,闯关东,站稳脚跟儿,混出个人样儿,才带两个弟弟迈出这坚定的一步,好一点儿了,再把二老接来共享天伦之乐。可哪成想……爹、娘,儿要这么冤死了,儿的冤魂你们都不知上哪找去?儿要真叫胡子强逼入伙,儿做买卖的念想就付之东流,全泡了汤。俺一时逞能,莽撞行事,还连累了两个不太懂事儿的弟弟遭此大难,愧对爹娘的养育之恩,儿不孝呀!如果俺累及两个弟弟性命不保,俺就难在世上为人了,连根刷,俺吉家不断了子孙了吗?’
触到伤心处,好男儿也有落泪时,吉德哭出了声,吉增吉和盛也凑过来,抱着吉德嚎啕大哭。哭得冷屋霜墙直打寒噤,掉下霜渣儿;哭得云凤泪水掉进煎鱼的热锅里,炸得热锅吱啦啦乍响;哭得老鱼鹰梦中惊醒,蒙蒙的叫苦不迭,触景生情,老泪也纵横不止。
这一哭,惊天动地!这一哭,哭出逢凶化吉!这一哭,哭出老绝户头子最后的智慧和勇气!这一哭,哭出云凤弱女子充当巾帼英雄不惜冒死!
老鱼鹰从炕上滑下地,忙走到吉德哥仨面前,红肿的眼里润着泪花,还没等老鱼鹰说话,云凤跑过来,抽哒鼻子说:“你们仨别哭了,哭得人心绞魔乱的。救你们的法子爷爷早想好了,就是下不了这个笊亮,担心捞夹生饭,吃不下,丢不了,虎皮拔噔的。救不了你们,还得兜着,搭上爷爷一张老脸,叫三叔骟。”老鱼鹰补充说:“事情还不周全,没敢挑明灯跟你们说,怕你们心里长草,弄出点儿啥响动来。啥事儿不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吗?我这法子也不是啥好法子,走的是春天晚儿顺了水的冰茬子,冒险!冒这个险逃,冒得成冒不成,值不值,还在针尖悬眼窝子上呢。帮你们猱了,老三还不知咋整治我呢?认了,说不过去。不认,那还不得找个脸,找个垫脚的。要不这帮人咋带,怕不服呀?最坏想,老三真拿你们喂家雀儿,我这老家贼就难逃一劫喽!”吉德哥仨听老鱼鹰的准确话,“噗噔噗嗵”双膝跪下,磕着响头,“爷爷、爷爷!有你老这句话,你就是俺们的救命恩人,你是俺们的亲爷爷。你老就认了俺们吧!还有云凤,你就是俺们亲姐、亲妹子。”老鱼鹰泪花盈盈,忙扶起吉德,“我认!好孙子。”云凤说不出来是高兴还是不舍,抹掉眼泪,在一旁溜缝,“我们就是一家人了,还外道啥,烫酒上菜。皇帝不差饿兵,吃完了,我跟爷爷送你们闯围坎。”
江水炖的鲫瓜子,滚烫热乎的老山炮,新焖的粳米饭,烙屁股的火炕,嘎亲的情意,凛然的正气,逃出魔爪的希望,满屋飘香的冒着热气,洋溢热气人气的融合,烈烈的感情绽放在祖孙老少红润的脸膛上。无难不见情,有难见真情,这一糅合朴实无华,蘸满人世间普普通通老百姓朴朴素素的百分人情味。
天寒冻死虫,酒浓情更浓,吃过最后的晚餐,爷孙们走出屋,出了院,上了胡同。黑透透的天,没有一丝风,雪下得密实,对面不见人。
前面雪中老鱼鹰黑影,蹒跚踩下东西斜不规则的一緉(liǎng双)靰鞡脚印,眨眼间又叫雪片覆盖。一溜儿黑影,像一个牵一个扯拉拉尾儿的尾随紧跟。窗户纸透出昏昏黄黄的灯光,伴着“嘎吱嘎吱”碾碎雪的声音,惹来好事儿狗的警觉,招来例行公事的犬吠。可一声声“汪汪”的狗叫,却噤若寒蝉的撕裂一溜黑影的心脏,滴滴颤抖的血液多想糊住讨厌狗的嘴。“汪汪”声越演越烈,此起彼伏,跟恐惧的人影开着性命攸关的大玩笑,考验人胆皮儿的薄厚。
狗尽着天职,是无辜的被无辜逃亡的人冤枉了。世上总有这不公平,总有被误解的冤诬,总有蒙冤无辜的死去。狗在为主人的安危尽着天职,却妨碍了正想享受安危它人的安危,它人就会咬直牙根儿骂它,“该死的狗!”
吉盛眼珠子贼溜溜地扫着眼前飘飘洒洒的雪花,就是这样在心里骂的。这一骂,狗还真嗅到有人骂它。胡同口,抹黑的高墙拐角,发出虽是懒骨头哆嗦的一嗓子,啥叫惊弓之鸟破胆的驹儿,也真够吓死人的。
“大雪泡天的,谁呀‘嘎吱嘎吱’的一帮,打瞎黑呀?”
“妈拉巴子的,谁这么横着走道呀?”
“老鱼鹰!干啥玩意儿去呀?”
“******腿去,没长屁眼儿呀,不会瞅啊?”
“瞅啥瞅啊,咋瞅啊雪迷眼的?”
“不瞅拉他妈倒,我带这几个‘空子’转转。天也不冷,遛遛食儿。一天都憋屈坏了,他们也没见过下这大的雪,挺新鲜。云凤,把那瓶酒给二子他们几个,怪冷的天,不易,抿两口,暧暧身子。”
“我才不想给他呢?整天价提溜个邪性的眼珠子,净挑人家姑娘家难处,邪门歪道的挲摸,不是好东西?”
“瞅瞅咋啦,谁不攀高枝儿,抱粗大腿呀?你要看上咱了,我还叫大当家的一句三叔呢。”
“美死你个大头鬼?给你灌!灌死了,少个扫巴星!”
“这丫头,就这张嘴厌恶,好话到你嘴里都馊巴了。”
“那我可转了二子?”
“我叫两兄弟跟着?”
“信不过我老鱼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