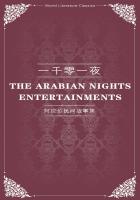我不会演奏任何一种乐器。哪怕是最简单的口琴,或者拿把吉他装模作样地那样拨弄两下,对我来说都是一件难事。乐器到了我手里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哑巴。钢琴可以随手按两下,按出来的声音虽说不算太难听,可那种没着没落的空洞的声音让我的心一下子跟着提起来,整个人成了一棵没有根的植物,悬浮在半空中。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一串十分连贯悦耳的声音,那是一个会琴懂琴的人正在演奏,他不需要有人聆听,他是弹给自己听的。
我一直很羡慕那些会弹一两样乐器的人,他们苦闷的时候可以用一两样乐器替他们发出声音,诉说他们的内心的苦。每当听到那些幽幽怨怨拖得很长的琴声,我都会想到一个人在午夜里独语的情形。他喃喃自语,把他的故事说了一遍又一遍。他也许并不希望有人听到,他不过是需要一个倾诉的渠道,把想说的话说了,把想表达的情绪表达出来。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听懂另一个人内心的声音,哪怕是最好的朋友,爱人,亲人都不能够将另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完全读出,所以我们时常觉得孤苦,即使在人堆里却还是觉得苦、觉得孤单。
乐器对某些人来说也许跟个伙伴差不多,每个人的生活中大约都有这样一两个伙伴:一本书、一支笔、一台用得顺手的电脑。这些静默无声的东西随着岁月的磨洗都会变旧变老变得仿佛是你身上的一部分。但有些东西一生都伴随在你左右,有些东西却永远都不属于你,即使你在形式上拥有了它,也并不见得真正占有它。
有一天下午,我到平安里附近去看望一位久未见面的女友。那时平安大街正在翻修,路边堆满了新翻上来的黄土,出租车司机把车停在丁字路口就死活不肯再往前走了,我只好跳下车徒步拐过路口的那个大弯。下午三点多钟的光景,偏西的太阳出现了一种炫目的金黄。街边店铺的门和窗都像抹了蜜一般泛着黄灿灿的光亮,玻璃宛若金属一般反射着巨大的灼人的光亮,让人看不清玻璃后面隐藏着怎样一个精妙奇异的世界。但不知为什么,那家店竟磁石般地将我吸引进去。走进店堂,刚才太阳刺目的光亮变成的灰绿颜色还停留在我眼皮上,我睁眼看到的是绿一块、红一块的光斑,却看不见真切的物体。我只好闭了一会儿眼睛,再睁眼时看到的景象令我惊异,我正站在街拐角最美丽的一家乐器店里——我这个音盲站在众多乐器中间真有些无地自容的感觉。
乐器店里最耀眼的明星是那排擦拭得锃亮瓦亮的吉他。它们挂在很高的地方,如人一般有姿有态地直立着。抬头看它们的时候会听到一种声音,是丁丁淙淙比流水更清亮的声音。它们一波一波地从我头顶上流过去,流过去了就不再回来,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我忽然决定买一把琴回家,疯了似的按都按不住,在口袋里书包里四处抓挠着寻找钱包。我知道我不会弹这东西买回家绝对没用,但当时却被吉他身体上那一道优美的弧线所诱惑,毫不犹豫地掏钱买了一把来。那东西后来一直挂在我墙上,一次也没打开过。我怕在那种深棕色光芒的照耀下自惭形秽到极点。我躲在电脑旁边写作,不时用余光打量那个陌生的客人。它不言不语静静地呼吸着我这屋里的空气,它闭着眼不看我,似乎和我没有任何关系。有时我指尖通电,一串串流出来的是叮咚作响的文字而不是有表情的音符。这时我忽然明白有些东西命中注定是属于我的而有些东西永远与我无关。
那把琴在我家墙上挂了很久,后来被谁拿走我已经不记得了。留下的是墙上的一道微黑的弧线和在我梦中反复出现的一家迷人的乐器商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