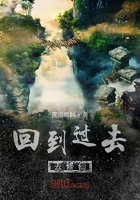就在欧阳非陪着黑子的岳父连夜坐火车赶赴绵阳保他妹妹的同时,欧老爹正在跟环卫局长谈话。那个晚上,对欧阳非的妹妹和欧老爹都非常重要。欧老爹那时正在经历他人生中最大的身份转变,当了几十年垃圾处理站站长的他,准备接手垃圾处理场场长的工作。那段时间,环卫局进行改制试点工作,决定让垃圾处理场公司化,不知为什么,环卫局长看中了欧老爹,亲自找欧老爹夜谈,让他挑起这个担子,全面负责垃圾处理公司的工作。
欧老爹其实是个头脑简单的人,一辈子勤恳工作,满心希望自己能有个出口鸟气的机会。他经常对欧阳非说的话就是,那些当领导的人,不要以为他们真有多大本事,也就是那个位置牛逼。谁坐到那个位置上,都能那样有能耐,有出息。欧阳非也夸他老爸说,您这话还真有些“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彼可取而代之”的意思啊,放在秦汉时候,您怎么着也能当个农民起义领袖。欧老爹鼻子里“哼哼”两声说,你小子别取笑我了,我好歹是养你大的,没亏待过你,你以为我这辈子没人捧过啊?
说到这里,得顺便描绘一下垃圾村的模样。欧阳非小时候,垃圾村并不大,一条南北贯通的小路,两边歪七劣八搭着好些不规整的屋子,屋顶上有些覆盖着石棉瓦,有些用油毡铺盖,许多房屋都破破烂烂,刮风下雨天经常有些屋子漏水。村子旁边有一个大坑,便是倾倒垃圾的地方。另一边有一条小河沟,原先里面的水还算干净,孩子们经常去那里玩水、洗澡,后来水沟里的水越来越肮脏,垃圾也越来越多,最后整个水沟都枯干了,要是有人提醒,就隐约还能看出那条沟的形状。欧阳非穿开裆裤那会儿,垃圾村里住了几十户人家,基本上大家见面都熟。近来这些年,城市在一点点扩大,垃圾山也越堆越高,垃圾村的人口也一年一年增多,估计有四五百户了吧,地儿也占到两千来平方米。这捡垃圾的工作,看着不怎么体面,寒酸、邋遢、招人嫌,大多数以为捡垃圾的都是穷得响叮当的人,可了解内情的人知道,那些捡垃圾的人中,也有好些挺有钱的主。欧阳非也是后来才听说,垃圾村里百万富翁什么的就有那么几个,只是他们习惯了不装13,外表仍是一副城市贫民模样,家里也不会装修得像宾馆,外出也不会开奔驰宝马充门面。
去绵阳之前,欧阳非买了些腊鱼腊肉等地方特产。坐在火车上,他满脑子漂浮的都是当初与妹妹在垃圾村生活的情景。有一年,妹妹看完电视上演出的舞蹈《卡门》,就吵闹着要老妈买一条卡门穿的那种红裙子给她过生日。那时候,垃圾村附近根本找不到地方买那种小孩穿的红裙子,再说,老妈从来也没有买衣服的习惯。欧阳非打小就没有穿过新买的衣服,身上的裤子、外衣、衬衣,不是从垃圾堆里捡来清洗清洗穿上的,就是老妈捡来一些布条布片缝在一起给我穿的,有时候还把捡来的衣服由长袖剪成短袖,汗衫剪成背心,长裤剪成短裤。
眼看妹妹为了一条红裙子又哭又闹,老妈好言好语劝说大半天也不起作用,欧阳非就决定想办法去为妹妹弄条裙子。恰好那是个暑假,欧阳非几乎每天都蹬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到附近的服装市场、街道、小区里四处寻摸、转悠,想看看有没有人卖红裙子,或者在阳台上、屋檐下晾晒红裙子。可找来找去,就是看不到那种鲜艳欲滴的红裙子,他简直都快郁闷死了。
末了有一天,偶尔碰到的一件小事让他眼前灵光一现,顿时有了主意。那天,欧阳非碰上几个小孩正在街边打闹,有个小孩拿了一支毛笔,甩着四处乱溅的墨汁,追逐着一个身穿白衬衫、比他个高的大孩子。那大孩子边躲边喊,你把毛笔扔掉,你把毛笔扔掉,弄脏我的衣服你赔。那小孩边笑边说,就不,就不,我涂你一身漆黑,看你还欺不欺负我!
欧阳非一拍后脑勺,马上想到,红裙子不好找,白裙子、粉裙子可到处都有,要是捡那么一条,再弄点颜色一染,那红裙子不就有了?就这样,他在某片小区随手顺了一条白裙子,然后弄了点染料,找了口破锅,跑到河沟边垒了个土灶,舀了些清水,将染料放进锅里,折了一根木棍挑着那条裙子,放在锅里泡着。然后,他又捡了些干柴,塞到锅底下点着烧了起来。等到水开了以后,欧阳非把裙子挑起又放下,挑起又放下,尽量让染料把裙子的摺边染匀了。最后,他把柴火撤出来熄灭了,把裙子放在锅里浸泡了一顿饭的功夫,自己累得躺在一旁的草地上睡着了,睡梦中看到妹妹穿上了自己给她染好的红裙子,美得她直在地上转圈圈,将红裙子的裙角旋转起来。
等醒过来后,欧阳非把湿淋淋的裙子捞出来,挂在树枝上晾干。那红裙子的颜色染得还算匀称,迎风飘拂着,远远看去就像一面耀眼的红旗。傍晚,他回到家中,悄悄告诉妹妹给她一件礼物。当他拿出那件红裙子后,老妈和妹妹都惊呆了,妹妹的眼神闪亮闪亮,兴奋得小脸都红了起来。她当即换上裙子,真的车转身轻轻旋转起来。那时,欧阳非想,天使也不过如此。
只有欧老爸不言不语,回头他把欧阳非拽到屋外,低声追问说:你老实告诉我,这裙子怎么来的?你偷的?抢的?欧阳非有些恐惧地看着老爸,战战兢兢地说:不是,不是,我哪有胆子去偷去抢,这,这,这是我一个同学的姐姐送的,她人好,嫌裙子小了,就送给了我。
欧阳非一边躲避着老爸严厉的眼神,一边胡乱编着理由,生怕老爸继续追问下去。幸好欧老爸只是叹了一口气,拍拍他的头说:好吧,你到时候看看家里有什么像样的东西,送点给你同学的姐姐,感谢感谢她,人家送了你东西,你也要学会回报人家,什么东西也不能白拿啊!
胡乱想着这些往事,火车不知不觉抵达了绵阳。在绵阳车站下车后,欧阳非与黑子的岳父告了个别,便直奔市公安局,找到老薄的老丈人的老战友李副局长。送礼品时,欧阳非特意说这是老薄的老丈人让我带来的,李副局长客气了几句,跟他寒喧了一会儿,就通过电话把他介绍给了关押妹妹的那个看守所的马所长。
李副局长的面子果然挺大,胖胖的马所长挺着肚子跟欧阳非说,这事要不是李副局长托付,实在没那么好办。这些日子上面抓“扫黄打非”抓得很紧,我们可不敢有什么闪失。欧阳非追问他说:那我妹妹到底犯了什么事,会被你们抓进来?
马所长两眼一眯说:老弟,你妹妹可不是我们抓的,我们只管看守。她具体犯什么事,我还真不太清楚,待会儿我给你查查,有记录。“扫黄打非”,你说还能犯别的什么事?马所长说罢,还“嘿嘿”笑了两声。
从看守所的记录中欧阳非了解到,他妹妹是因为在乡下表演脱衣舞有伤风化而被拘留的。看在李副局长的面子上,看守所只要了他两千块钱,就把妹妹保了出来。当欧阳非看到妹妹时,心里忍不住有些发酸,她明显比以前瘦了、黑了,头发有些凌乱,水汪汪的眼睛显得有些空洞、茫然。
在离开众人的视线后,妹妹一把抱住欧阳非,“哇哇”痛哭起来,欧阳非能感觉她的泪水流进他的脖子,身体在颤抖。说实在的,欧阳非已经多年没有跟妹妹这样亲近过,这样抱过她大概还是在十年以前,那一刻说不出为什么,他觉得自己的身体有些发热,神经有些发麻。他能清晰地感受到妹妹温热的呼吸,还有从她身上传递过来的体温,甚至她紧贴过来的柔柔软软的胸都让欧阳非一时有些失控。
欧阳非知道,贴在他胸前痛哭的妹妹,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个小女孩了,她已经长成了大女孩,能够激发人想像和激情的大姑娘。他觉得自己不能再胡思乱想了,便轻轻安慰妹妹说:别哭了,妹妹,我不会怪你,老爹老妈也不会怪你的。
妹妹抽泣着说:你可千万别告诉老爹老妈,这半年外出,估计他们就够操心的,你要告诉他们我出了这事,他们哪受得了啊。欧阳非拿出纸巾给妹妹擦擦眼泪说:你放心吧,这事我哪能让他们操心。不过你回去后一定得看看他们,他们可想你呢!妹妹点了点头,又理了理自己的头发说:你看我现在这样子,怪难看的吧,都是这看守所,搞得我神头鬼脸的!
欧阳非伸手摸摸妹妹的头发笑了笑说:到城里后先收拾收拾,弄精神了,再抽空回家看看老爹老妈。在热乎乎的空气中,欧阳非跟妹妹挤上了回家的火车,那车上几乎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他们就在车厢的连接处站着。实在累得不行了,欧阳非才找着车内的乘警,让他允许他俩到餐车歇一会儿。看在欧阳非是公安的面子上,乘警答应了他的要求。
美美自述11
那晚上撇下那个小官员回来睡觉后,老崔叔并没有责怪我。同屋的姐姐后来偷偷跟我说:你好大胆,可真够运气的!
不过,好运气不是总会有,没想到“崔家班”终于栽了一把。可能老崔叔没有好好打点地方上的公安,也可能正好撞在枪口上了。
其实,说起来好像也不算过分,就是表演的最后有一两场脱衣舞,也就是脱到穿裤衩为止,跟时装秀里的清凉装一样,三点式吧,不算黄吧。可是,还是赶上“扫黄打非”了。老崔叔说,“黄”这种东西跟艺术也一样,好像也没有什么太特别的界限,你说黄就黄了,你说艺术了就艺术了。
现在的人也真是什么都想得开,放得开,我头一次看女孩们在台上脱衣服,还是觉得有些脸发烧、心发跳。虽然在幕后经常看到她们裸着身体换戏装,没感觉多难为情,可毕竟面对大家公开表演,她们还是需要勇气啊!当然,老崔叔总是会强调表演这样的节目要有底线,这底线就是不能彻底脱光了,要留底裤,不然那就叫不上艺术了!
刚刚关进看守所的那几天,我真是一肚子委屈,别人动不动就把我们都当“鸡”看,那些人的素质简直就没法说了。老崔叔早就顾不上我们了,据说他一看到有公安来抓人,也没通知我们就自顾自地跑得没了影。我们算什么啊,为谁啊?为老崔叔赚钱,为逗大伙一乐,公安才不管我们是不是搞艺术,也不管我们有没有底线,说你当众脱了衣服就叫涉黄。那农民干活还经常露大腿、光膀子呢,农村大嫂还经常当着大家面露出乳房给孩子喂奶呢?那也叫黄吗?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些轻信,我的出走是不是有点盲目,反正我听说好多人这么一抓,这辈子前途就给毁了。我的人生刚刚开始,就这样一塌糊涂,稀里糊涂进了看守所,我这是怎么了?我不甘心生活在满是垃圾的地方,可好笑的是,现在进来的地方好像更垃圾。难道这就是命吗?
现在我只能找我哥了,他是惟一能帮我的人。我在老崔叔这里结识的这些伙伴,现在都是自顾不暇,他们从看守所出来后会去哪里,谁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