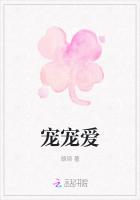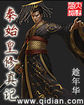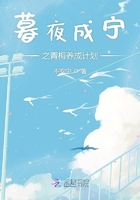陵宫四壁各有一个三角形的拱门,状如壁龛,均装有透雕的大理石石屏。陵宫呈八角形,中间覆盖着一个圆形的巨大穹顶,四周的墙壁以黑色大理石的图案画的半部《古兰经》文字和花草装饰,各色宝石镶嵌在娟秀的纹路中。寝宫的门窗都用白色的大理石镂雕成菱形花边小格,格中也镶嵌翡翠、水晶、玛瑙组成的色彩艳丽的藤蔓花朵,那枝干都用黄金制成。寝宫内有一扇由中国巧匠雕刻得极为精美的门扉窗棂。寝宫共分五间宫室,宫墙上有构思奇巧、用珠宝镶成的繁花佳卉,使宫室更显得光彩照人。在寝宫的正中间摆放着泰姬的石棺,那侧旁稍小的石棺是沙贾汗的。这是供人凭吊的空棺,他们的遗体被安放在寝宫底层的八角形的墓穴中。
走出寝宫正门,站在那宽阔的石阶上,面对着的是一条长形的清澈水池,倒映着塔身的倩影。池水两侧是红砂石铺成的甬道,甬道外就是绿草茵茵和鲜花盛开的公园了。有高矮错落的柏树、榕树和凤凰树点缀其间。如从寝宫的后门走出,你便可以看到朱木拿河正在泰姬陵身后静静地流淌,唱着不尽的挽歌。
泰姬陵最让人惊艳的是那一身通体的白晶,如冰清玉洁般的纯洁,像圣女般的高贵,正像泰姬——一位柔美、坚贞、善良、赤情的王妃的化身。她的淡雅纯朴,她的天生丽质,她的气质非凡,都物化在一个永恒之中。这正是泰姬陵的魅力之所在,这是高贵女人的魅力,这是纯真爱情的魅力,这是寄情于物的建筑的魅力。白居易在《长恨歌》中赞美杨贵妃“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如果有谁赞扬泰姬陵“投眼一望百媚生,天下风光无颜色”,也许并不过分。
如果从建筑美学来观察,泰姬陵最美的是它的和谐和对称。建筑和园林是和谐的,主体建筑和附属建筑是和谐的,宏观和微观是和谐的,结构是和谐的,色彩是和谐的。和谐是因为对称,整个建筑都是对称的,以塔顶的尖端和寝宫中泰姬的石棺为中心,通过水池的中枢线,整个建筑可对应起来,东西是对称的,上面的圆塔和下面塔楼是对称的,东边和西边的窗棂是对称的,墙壁上的雕花是对称的,连每一朵花、每一枝叶都是对称的。然而还有一个最大的对称没有实现,那就是沙贾汗要在朱木拿河的北岸再建一座和泰姬陵完全对称的大小一样的黑色陵墓,以此来安葬自己,两个建筑中间由大理石桥相连。这正是《长恨歌》中的“在地要做连理枝,在天要做比翼鸟”吧!他们的灵魂会通过这座玉桥去相会。
可惜,这个痴狂的情圣、疯狂的建筑师、腐败透顶的国王,为了老婆的一个浪漫的遗愿,横征暴敛,劳民伤财,祸国殃民。在泰姬陵长达22年的工期中,他以皇帝的名义动员数万民工,花费重金从印度全国和中亚及欧洲聘请一流的设计师和建筑家,虽建成这一空前绝后的陵墓,却造成人民的灾难和国家的衰败。在泰姬陵建成四年之后,沙贾汗还在规划着建设自己的陵墓之时,他和泰姬的第三个儿子奥朗哲布“大义灭亲”,率部杀死两个兄长,推翻了自己的父皇沙贾汗,结束了一个昏庸腐败的王朝。祖父阿克巴和父亲贾汗吉尔两代经营的繁荣盛世,全被沙贾汗在大兴土木中耗尽,农民的税赋高达收入的一半!在民怨沸腾之下,奥朗哲布政变成功。他把父亲关进阿克拉城堡,专为他修了一个八角形的小亭,通过一扇小窗可以遥望朱木拿河南岸那朦胧中的泰姬陵。在八年后的一个风轻月明的夜晚,沙贾汗让服侍他的女儿把他从病床上扶起来,走到小窗前,对着泰姬陵的方向喃喃自语:“泰姬·玛哈尔!泰姬·玛哈尔!”当晚溘然去世。他那当皇帝的儿子,把他装进一个比母亲稍小的棺木安放在泰姬的身旁,也算满足了他的一个心愿吧!后来到此访问的中国大使孙玉玺留诗一首:
暮色苍茫看陵丘,
几度辉煌几度愁?
漫天浮云遮泪眼,
扫地秋风吹白头。
人生百年空遗憾,
史记千古训常留。
可怜天下痴父母,
不孝儿孙恩报仇。
在阳光明媚时分,我们告别这一处装满爱情神话的“金字塔”。据说,随着日落和日出,特别是在月光初上的夜晚,泰姬陵会变幻着奇异的光彩。可惜,我们只看到它一时的光彩了,但已很满足了。因为对泰姬陵的怀念和思考会很长久的。
金三角
离开泰姬陵,我们还是一步一回头。对于泰姬陵的过分迷恋,耽误了我们参观阿克拉城堡的时间。其实这个城堡也是上了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名录的。阿克拉城堡的兴建者是沙贾汗皇帝的祖父阿克巴大帝。1565年出于国家安全的目的,阿克巴就地取材,用红砂石建成了这座固若金汤的城堡。从外形上看,它敦实坚固如军事要塞,圆堡突出,由城墙相连,城墙上有便于防卫的垛口,圆堡的窗口很小,那是战时的枪眼。到了沙贾汗当皇帝时,这位狂热的建筑师,又在城堡内大兴土木,把这个军事要塞建成了辉煌的皇宫,这为他1632年建设泰姬陵,1639年建设老德里的红堡都积累了经验。现在人们还记得这位皇帝的名字,就是因为他还为印度留下了这些建筑艺术的瑰宝。
我们匆匆地登上阿克拉城堡,还是想再领略一下沙贾汗的建筑才华。在这方圆只有一英里半的城堡里,建有许多巍峨的宫殿和肃穆的清真寺。宫殿中有议事厅、觐见厅、枢密院、镜宫等,清真寺为珍珠清真寺。整个建筑呈现伊斯兰风格,圆形的尖塔,大理石的廊柱,以白色和蓝色为主调的装饰,细部的花蔓由多彩的宝石镶嵌,多彩玻璃镜面饰墙,给人以华贵晶莹之感。浪漫好玩的沙贾汗还在皇家花园的小广场上镶上了棋盘式的方格,这是他和王妃及宫女们下棋取乐的地方。他还独出新裁地建了个宫女市场,购物逛街是女人的天性,既然不能出宫,就在宫里逛吧!沙贾汗对女人的依从,可谓天下第一。
随着络绎不绝的人流,我们也走到了城堡左边的那个八角形的石塔小楼,抚栏远望,可见在那绿色的草滩上静静流淌的朱木拿河,还有河对岸朦胧中的泰姬陵,那白色的宫阙海市蜃楼般的时隐时现。这里就是篡权的三儿子奥朗哲布为沙贾汗安排的幽禁之处。在八年的时间里,沙贾汗经常抚栏远望,以泪洗面,感怀爱妃,诅咒自己的不孝子孙!
离开阿克拉城堡,我们便东行了,奔斋浦尔方向而去。从德里南行到阿克拉,再从阿克拉东行到斋浦尔,再从斋浦尔北上回新德里,这三个城市中间的距离大约都是200公里,正好形成了一个等边三角形。这就是有名的印度“金三角”。过去我们知道缅甸的掸邦高原有个“金三角”,那是以盛产毒品而出名。而印度的这个“金三角”以旅游胜地而闻名。我们已走马观花地看了横贯古今的名城新老德里,又看了誉满中外的古都阿克拉,现在又前往曾辉煌一时的古都斋浦尔。这三个城市地处恒河平原,这里正是印度古文化的发祥之地,许多古邦国都诞生在这片土地上。这里也是富庶之地,许多民族部落在这里繁衍生息。如果你想了解印度的古老历史,“金三角”中那数不清的宫殿、古堡、神庙、陵墓里写满了故事,其中不乏金戈铁马,也有花前月下。那列入世界历史文化遗产的莫卧儿王朝的第二皇帝胡马雍的陵墓、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泰姬陵、著名的古皇宫阿克拉城堡、法塔赫布尔西格里古城遗址、盖奥拉德奥国家湿地公园都在这个“金三角”之内。凡是游览印度的,“金三角”肯定是首选之地。
应该说印度是个旅游的资源大国,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在亚洲最多的国家是中国和印度,据统计到2003年列入遗产名录的中国有29项,印度有24项。但印度却是旅游经济的小国,据中国使馆提供的资料,2000年全年到印度观光的外国游客只有260万人次,其收入30亿美元,仅占全世界旅游收入的0.38%。近年来,印度政府采取改善基础设施、保护环境、提高服务质量等办法,但旅游业仍不见大的起色。究其原因,大使馆分析,一是地区形势不稳。印度和巴基斯坦关系紧张,军事冲突时发;国内教派冲突不断;这里又是国外恐怖分子袭击的重点地区。这一切都让旅游者望而却步。二是交通十分落后。我们已领教了公路最好的德里到阿克拉的200公里的5个多小时的路程。我们也看到了新德里国际机场的现状。这样的交通条件使来者怨声载道,耳闻者只好放弃险途。三是大城市的旅馆少而贵,乡村的旅馆少而脏,让人住不起,不敢住。四是票价不平等。到泰姬陵参观当地人20卢比,外国人750卢比。有的参观点还要另买拍照票。这常使我们这些老外愤愤不平。其实这些问题20年前的中国就有了,现在中国真的好多了,印度朋友应该到中国来看看!可惜,印度人到中国的很少,连阿伦这样的“中国”通和阿菲这样的中国“准姑爷”都没到中国来过!他们俩还说到,印度旅游业发展不快还有一个原因是印度人对旅游业不热心,他们说本来人就多,又来些外国人,不是更乱了。他们不理解,陵墓里都是些真死人,寺庙里是些假死人,有什么可看的!不过,这两位导游都对旅游业的发展很有信心,因为中国人来的越来越多了。
从阿克拉通往斋浦尔的公路就更差了,有了德里到阿克拉的颠簸经历,这一段行程就算我们回到中国70年代到农村的一次采访吧!路上还是那么车水马龙,多种车辆抢行,大象、骆驼、老牛都来凑热闹。这次的突出感受是汽车的喇叭都特别地响,声调不同,节奏各异,组成了一部公路交响乐。阿菲说了,在印度开车,必备一个特别好的喇叭,否则你就寸步难行。在印度行车没有车速的限制,就更没有对笛声的限制了。印度人喜欢嘈杂的生活?
很难得,我们看到有人在扩修公路,工人不多,在扩宽的路面上铺石子,一台老式的压道机慢悠悠地行进,有顶着水罐的妇女来送水。看不到中国式的热火朝天的修路场面。阿菲说,在印度修路很难,先要政府研究,然后报议会讨论,议员代表各个阶层的利益,很难达成共识,一件事久议不决,没有紧迫感。议会同意了还不行,土地是私有的,要修的路经过谁家的地,还要和这一家谈判,一家家的谈,十分艰难。就是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工程进展也特别慢,印度人干什么都效率不高。说到中国基础设施的高速发展,有的印度官员感叹,只有专制的中国才能办到,民主的印度是办不到的!在经济建设上是中国的“专制”好,还是印度的“民主”好,还是让历史来证明吧!不过印度式的“慢”也有好处,很难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
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有权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一位旅美的印度华人学者说:印度有“安贫乐道”的传统,民性倾向于平和、纯朴、顺其自然、循规蹈矩。印度独立之后,尼赫鲁以一个“r”字母的区别来比较中国和印度的发展规律。他说中国提倡“revolution”(革命),印度提倡“evolution”(进化)。半个世纪印度的发展道路也不平坦,但不像中国那样大起大落。中国的跃进式的进步是印度所赶不上的,但印度前进道路上也不会有中国那么大的风险与提心吊胆。
一路上,我们看印度想中国,思考着亚洲这两个最大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如果我们能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一定能在国际舞台上“龙象共舞”,那是一部好戏、大戏。
满城尽是粉红色
印度人是喜欢色彩的,一方面表现在印度妇女那一身色彩鲜艳的纱丽,无论是在繁华的都市还是在偏远的山乡,她们都是流动的风景线;另一方面表现在许多城市以某种色彩为标志,经久不变,昭然天下,以此吸引游人。如老德里古城的红色、乌代布尔的白色、焦特布尔的蓝色、斋浦尔的粉红色,都让这些城市名享遐迩。
走进斋浦尔,才对城市颜色的魅力有了真实的感受。这个位于德里西南约265公里的城市,是拉贾斯坦邦的首府,满城尽披粉红色的外衣,这就是我们最鲜明的印象。那粉红色涂在古老的宫墙上,也刷在临街的所有外墙上,虽然有些陈旧,但仍然鲜明。每一个游人走进这个城市时,都对被这种颜色笼罩的城市有着有趣的印象,有人说初到斋浦尔,看到满眼的粉红色,以为这个城市曾经被大火烧过,那色泽也好像一只被开水煮过的大螃蟹。也有人浪漫地说,走进斋浦尔如走进春天的桃园深处。
面对斋浦尔,我以为她像一个过气的美女,无论怎样涂脂抹粉也无法掩盖曾经的风尘,她的衣裙太沉旧了,她的面容太苍老了。显然斋浦尔没有我们的家乡哈尔滨年轻美丽,不仅因为它年长了一百多年,还因为哈尔滨几乎每年都要粉刷一次,让城市换上米黄色或乳白色的新衣。但斋浦尔不行,房产都是私有的,政府没有力量让整个城市经常穿新装,你就是想换,房主不同意,你也无计可施。
其实任何城市的颜色都是有政治色彩的。北京的金色,那是古都的遗存,哈尔滨的米黄和乳白来自欧洲文化的影响。斋浦尔的兴盛得益于辛格土邦王朝的发展。1727年,萨瓦尔·杰伊·辛格二世建设了新都斋浦尔,他是杰出的政治家,还是梵文、波斯文作家和伟大的天文学家和建筑家。这个土邦王朝发迹于附近的安贝尔城堡,辛格的前辈臣服于强悍的卧莫儿王朝,使自己的王朝的繁荣从11世纪持续到20世纪,而卧莫儿王朝19世纪就消亡了。当英国殖民统治者进入印度后,辛格王朝又向英国人示好。1876年为迎接来访的英国威尔士王子,辛格二世下令把斋浦尔全城的建筑都涂成粉红色,因为他听说,王子喜欢这种颜色。辛格的热情让王子大悦,英王也大悦,背靠大树的辛格王朝在斋浦尔的统治一直持续到印度的民族独立。那时,辛格王朝的宫殿成了国家的博物馆,但还保留部分给王室成员居住,一直到现在。一个王朝结束了,但它的颜色被保留了下来,这也是对历史的一种尊重吧。现在辛格二世仍然受到印度人的敬仰,尼赫鲁说过:“无论在任何地方和任何年龄的人中,他都是最伟大的。”一个城市必然打上他的建设者的印迹,多才多艺的辛格让自己的城市充满了浪漫的艺术气息和科学精神。而那些粗鲁的农民起义者,经常烧毁华丽的都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