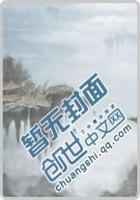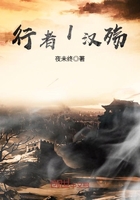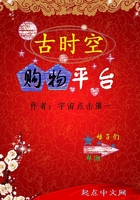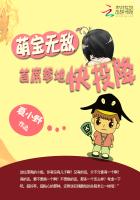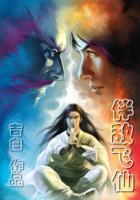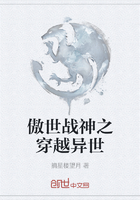丝绸之路的开通,并不是一人一时之力的结果,而是各民族长久以来不断交往的必然。作为中西文明交通的大动脉,丝绸之路在当时及此后的千余年间,一直发挥着无以替代的重要作用,是中西友好交往的历史象征。
■命名由来
19世纪后期,德国地理学家李西霍芬第一次提出“丝绸之路”的概念。“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通向西方的贸易通道,从今天的西安出发,经新疆分南北两路,越过葱岭,到达中亚、西亚各国,再由这些国家转道至欧洲。其实,中国通过丝绸之路向外输出的物品远不止丝绸一宗,但以丝绸最为有名。从公元前2世纪起以后的千余年间,中国的丝绸通过大宛,源源不断地经由这条商路远销地中海世界,成为国际市场上闻名遐迩的畅销商品,此路故而得名。早在张骞通西域前,西域绿洲诸国为了自身的存在与发展,必须谋求各个绿洲之间的合作,互通有无,无形中沟通了绿洲之间的交通路线,形成相对稳定的商道,奠定了丝绸之路的雏形。张骞通西域,使绿洲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东西方之间的联系又借汉朝的政治力量进一步加强,使丝绸之路得到实质性开发。东西方彼此间物质、技术、文化的互相需要,是丝绸之路得以开通的根本性原因。各国商旅的贸易往来,使节的频繁交通,都对丝绸之路的实质性进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繁盛的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沟通了东西方的贸易往来。中国的丝绸、漆器、铁器及其他手工艺品输入西方;中亚和西亚的一些植物品种,如葡萄、苜蓿、石榴、胡桃等,盛产于康居等国的皮毛,月氏、安息、大秦的毛织品及各种珍奇异兽,如琉璃、琥珀等也输入中国。精通天文、农业、水利、冶金的各种技术人才移居西域地区,对于推动当地生产技术和科学进步,都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西域地区的具有波斯、印度风格的乐舞、美术、生活用品,如胡坐(靠椅)、胡床(折叠椅)等,一时间也引得都城皇室、贵胄、官僚的竞相效仿,风行一时。西域南北两道城郭诸国在丝路贸易中是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丝绸之路的开通,也使得中国与西方文明频繁接触,交流持续不断,而西域则成为各个文明交汇融合之地。汉代,不仅有陆路丝绸之路的开放,几乎同时也有海上丝绸之路的拓展。东南沿海擅长航海的百越民族,沿着大陆边缘的海岸,经过长途航行,到达东西方海上交通的汇聚地南印度洋海岸,进行各种物品主要是奢侈品的交易。随着历史的发展,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和作用日渐突出。
■佛教东传
两汉之际,产生于印度的佛教辗转传入中国。相传东汉永平年间,明帝梦见一位神人,身上发出金色霞光,在朝殿中现身,而后又向西飞去。明帝询问群臣,一位官员解释说:“天竺国有得道高僧‘佛’,可在天空飞行,身有神光。皇上所见的,可能就是‘佛’。”明帝于是派遣中郎蔡、羽林郎秦景等12人前往西域求佛法,在大月氏抄写佛经。或说永平十年(67),蔡等人于大月氏遇见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两人,并得到佛像经卷,因而用白马驮回洛阳。为了接待天竺客人,明帝令人仿照天竺祗园精舍,特为他们建立住所,是为白马寺。据说,他们在寺中翻译佛经《四十二章经》—中国最早的汉译佛经。江苏连云港东汉佛教摩崖造像的发现,则证明佛教也可能是从海路传入。佛教传入内地后,最早的信奉者多是王公贵族,如楚王刘英等。佛教东传,佛经的翻译成为当务之急。只有把梵文、西域文佛经译成汉文,实现天竺智慧形式的汉化转换,才能推动佛教的传播。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安息僧人安世高到达洛阳。在此后的20多年间,他翻译佛经30余部。佛经的翻译,极大地推动了佛教的传播,到了桓帝、灵帝时期,“佛学在我国成为道法一大家”。献帝初平四年(193),丹阳人笮融建造佛祠,铸造佛像,广招信徒,这是史籍中关于佛教造像立寺的最早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