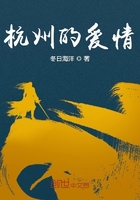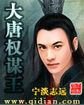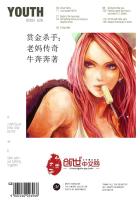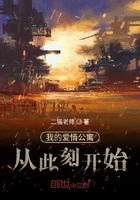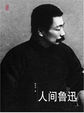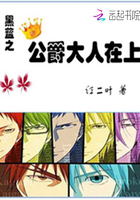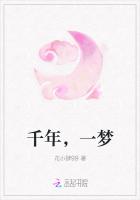以铺陈夸张为特色的大赋,成熟并兴盛于汉代,为统治者所钟爱。而主要来自民间的乐府诗,则往往能较为真切地反映社会生活,也是在两汉兴起的一种重要的诗歌体裁。
■汉赋
赋是介于散文和韵文之间的文体,出现于战国后期,成熟并兴盛于汉代。西汉初年,摹仿楚辞的骚体赋流行于文坛,代表作有贾谊《吊屈原赋》等。枚乘的《七发》,虽不以“赋”名篇,却开创汉代大赋创作的先河。武帝对赋的喜爱及提倡,推动了创作者的不断涌现;国家的兴盛及统一,也为赋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赋自此空前兴盛。当时最著名的赋家是司马相如,代表作是《子虚赋》、《上林赋》。赋篇“润色鸿业”,极力歌颂朝廷强盛和天子尊严,盛赞大一统国家的气势与声威,末尾归于“讽谏”。在形式上,结构宏伟,韵文、散文相间,辞采靡丽堂皇,场景雄伟壮观,震撼人心。继司马相如之后,著名的赋家、赋作,有扬雄的《蜀都赋》,班固的《两都赋》及张衡的《西京赋》、《东京赋》。大赋过于追求形式,过于铺张扬厉,以至于“虚而无征”;表达方式上,多是采用主客答问和层层排比,以至于呆板少变,几近僵化;文辞堆砌,又多用奇词僻句,给人味同嚼蜡之感。至于“讽谏”,更多的被后人讥为“劝百讽一”,形同虚设。当大赋盛行时,抒情小赋也依然行世。东汉中期以后,抒情小赋逐渐成为创作的主流,代表作有班彪的《北征赋》、张衡的《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及蔡邕的《述行赋》等。这些小赋,突破大赋的颂扬传统和呆滞体式,多采用骚体,或抒情言志,或借物寓言,风格清新明快,往往有较多的批判现实的内容。
■乐府民歌
乐府诗,是两汉兴起的一种重要的诗歌体裁,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园地里的一支奇葩。乐府最初可能设立于秦朝,本是政府的音乐机构。汉武帝时,出于制作礼乐的需要,改革并扩大乐府机构,令其谱制新声、教习歌舞,以备祭祀之需;又派人大规模地采集各地“观采风谣”,并为之配乐。这些制作和搜集配乐歌唱的曲辞,当时称为“歌诗”,后被称为乐府诗或乐府民歌。乐府诗主要来自民间,往往能较为真切地反映社会生活,表达民众感情。乐府诗内容丰富,或表现百姓生活困难、无法生存,或反映战争和徭役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或揭露讽刺统治者的荒淫与腐败,或表现爱情、婚姻与家庭。它的形式自由灵活,突破《诗经》以四言为主的格局,创造乐以五言为基干,包括四言、七言、杂言的新的诗歌体裁,以包含更多的内容,更为自由地抒情叙事。它的语言质朴自然,生动活泼,不饰雕琢,富于生活气息;
叙事真切,情景逼真,闻其声,可想见其状。汉代乐府诗歌中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与北朝民歌《木兰辞》声誉最为显赫,被世人称之为“乐府双璧”。
■《古诗十九首》
五言诗在汉代以后成为中国诗歌的最主要的体裁之一。文人五言诗在西汉已经开始出现,到东汉初年以后,文人五言诗已经趋于成熟,并且出现创作腾涌的局面。代表汉代文人五言诗最高艺术成就的是《古诗十九首》。它并非一时一人之作,大部分诗篇是东汉中前期的作品。主要内容,或是哀叹人生短促,该当及时行乐,如“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或是抒发相思情,伤别之苦,若“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或是感慨个人遭际,向往功名利禄,像“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轲长苦辛”。它既不同于一般民俗歌谣,也不同于“诗骚传统”影响下的文篇,而是以抒写文人士子的世俗情怀、表现生命意识为主的创作。感情真挚而质朴,语言自然而文雅,故被刘勰誉为“五言之冠冕”,后人更评价为“情真、景真、事真、意真,澄至清,发至情”。
■建安文学
建安是东汉献帝的一个年号。献帝时代战乱频繁,民生凋敝,然在文学上却颇有成就。这一时的诗歌,扬弃了有汉以来的铺采摘文、义归讽谏的注重功利的诗骚传统,异化了东汉前中期文人追逐个人价值、沉湎于自我意识的非功利诗潮,输注了乐府诗用现实主义手法反映现实社会的诗歌创造精神,熔铸了忧患人生、忧患社会的双重忧患意识,塑造了汉末诗歌神采飞扬,慷慨悲凉的时代风格。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是“建安七子”和曹氏父子。建安七子,仅仅是建安文士中声名最高者,他们是孔融、王粲、陈琳、徐、阮、应、刘桢。他们于当时的文体,无论是散文、辞赋,还是诗歌,各有所长,各有特色。
曹氏父子是建安时期的文学领袖。曹操的诗篇,质朴而豪迈,苍凉慷慨,气势雄阔,有乐府诗的粗犷风格,反映了身处乱世的悲愤情怀,但又不失积极的奋斗精神。《步出夏门行》中说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用来抒发人生短暂,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曹丕之诗,多取材思妇游子的离怨别愁,婉约缠绵,柔情妩媚。曹植(字子建)的诗篇,尤其是后期诗作,成就更高。他缘情赋诗,以情纬文,抒情动人。前期诗作风格豪迈明快,后期沉郁悲怨。其诗阴阳协和,刚柔相济。刚则近于曹操的雄浑老劲,却具有青春气息;柔则类于曹丕的清丽婉约,但更重抒写性情。神采斐然,音韵铿锵,文质相称,流传广泛。据说,南朝谢灵运曾言:“天下才分十斗,子建独得八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