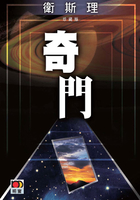“当然。据我所知,喜欢的人还很多。”我想起那两位日本女客的事,“景焕,现在中国搞插花艺术的还不多,我想你很有这方面的天资,一定会搞出名堂的。我有很多热心的同学和朋友,他们都会帮你的……”
她的眼睛里又闪出了那两团迷人的星光,良久,她轻轻地说:“真是……太谢谢你了……”
暮色渐渐深浓了。远方灰暗的云朵聚集成大块,像泼墨画里的牡丹似的。落日把最后一缕苍白的光线投到灌木林的尖顶,寒风又把这光线撕碎,抛洒在湖面的厚厚冰层上,发出凄厉的声响。
“冷了吧?再滑一会儿?”
她仰起头,信任地把手放在我的手心里,嘴角上挂着一缕娇媚的微笑。
我拉着她滑了一会儿,渐渐把手松开了。
她一个人在冰面上滑行!暮色中,我看见她的眼睛好像始终是半睁半闭的,她沿着我们滑过的那个圈子滑着,风把她那顶小帽吹掉了,一头柔丝在冰面上飞舞起来。
我想起了那首叫做《弧光》的钢琴曲。
夜深了。这是一个无星无月的夜。我们俩静静地坐着,仿佛互相听得见对方的心音。她冰凉的小手正在我的掌心里悄悄地融化。有一种说不出的含着苦涩的甜蜜感哽塞着我的喉头。我怕这一刻我会说出蠢话,但沉默又迫使我不得不说些什么。
“今天……你玩得高兴吗?”
“当然。……很高兴。好长时间没这么高兴了。……”她的微笑里带着几分忧伤,“我发现,我的情况还不像想象的那么坏……”
“你的才华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
“一个人总有些他喜欢、热爱的东西,假如这就叫做才华的话……”
“是啊,我也常想,假如一个人永远可以干他喜欢干的事就好了。可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除了喜欢、热爱的概念之外,还有需要。社会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也就是说,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还缺乏条件……实际上,对工作的兴趣是可以培养的……很多人干的不也是自己不喜欢的工作吗?可是时间长了,照样干得蛮好……”
“这是……你的心里话吗?”
“我想……我是这么认为的。”
她不说话了,呆呆地望着广漠的天空。
“你不觉得,我们现在的生活很可怜吗?”良久,她突然低声问我。
“可怜?”
“是的。我们像只工蚁,而不是像个人那样地活着。”
“……?!”
“我同意爸爸的观点,人类社会是以学习为基础的。人,这种生命有机体,具有创造力上无限的多样性和可能性。只有蚂蚁社会才以遗传模式为基础,假如对人施以限制,让他永远像工蚁那样去重复固定的职能,那么他作为人的优越性永远发挥不出来,也就是说,他永远成为不了一个完善的人……”
这番话使我目瞪口呆。我万万想不到,在她的心灵深处还藏着这许多东西,这太不符合我们日常所受的教育和常规理论了。因此听起来是那么别扭……
“怪不得谢霓说你是个梦想家。可我们现在生活着的是一个讲求实际的社会。”
“其实,梦想与现实只有一步之遥。这个地方……不就是我首先在梦中常常见到的吗?……这只是巧合吗?……”
“这……偶然性太大了。”我勉强说。
“偶然?爸爸说得对,我们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偶然性的世界。没有幻想,没有梦,没有那些被你们认为是荒诞不经的想法,就没有今天的科学,今天的人类。”她忽然变成了一个喜欢夸夸其谈的女理论家,这使我深感不快,“就说‘飞翔’吧,这是人类的最古老的梦想。从中国最古老的神话、瑜伽托钵僧的梦想,到关于克里特英雄伊卡洛斯的传说……后来,不再是传说了。人类发现了撒哈拉阿杰尔高原的岩石画……那些岩石画上画着一些类似翅膀的东西……这究竟是人类的想象,还是那时外星球来的某种飞行器呢?为什么我们不能设想一位星外来客曾在这个岩洞里生活过呢?从古代的神话,伊卡洛斯的飞翔,经过高原岩石画,中世纪巫师的扫帚和达·芬奇设计的翅膀,一直到菲利斯、佛格的世界……科学和富有诗意的梦想难道有一时一刻是分离开的吗?……”
我像看一个陌生人那样看着她。我自以为了解她,可至今才看到她的本来面目。或者说,是她的另一面。应该承认,她讲的话里确实有许多我不知道,也从来没去想的东西,这使我这个大学生深感惭愧。
“把梦想变为现实的过程中,热爱是一把最好的解决困难的钥匙。我喜欢花,喜欢那些美的东西,于是我就想方设法使它更美,改变它的颜色、香气和花期,我可以让夜晚的花在白天开放,夏季的花在冬天存活,难道这些在古代人类的梦想中,不是只有女神才可以做到的事吗?……你做到了,你就是女神;你认识到了这个,你就懂了你活着的意义。于是你又去开拓一片新的你热爱的领地,你作为一个人的潜能就这么一点一点地被挖掘着,直到你度完了一生,你看到了你耕耘的果子,你看到了人类在品尝这果子,于是你明白,你的人生价值实现了……”
尽管我可以提出一千条理由来反驳她,但此时此刻我却说不出来。我的内心深处被某种东西震撼了。
应该承认,我那一千条理由都是别人的。我至今还没有形成自己固定的想法。风,变得更寒冷了。我在内心嘲笑着自己:搞心理学的,却完全不善于了解别人。几个月来我心目中的那个温顺的、惹人怜爱的姑娘不存在了。我庆幸自己刚才没有讲出什么蠢话。
谢霓说得对,我们都是凡夫俗子,而她,却是玛雅金字塔:神秘,孤傲,可望不可即。是收场的时候了。
“景焕,我……我想跟你说一件事……”我努力把话说得温柔、平缓些。我不愿再增添这个姑娘内心的创伤,但我必须要说出来,迟迟不决只会对她更加不利。
“不,你不要说……”她显得又紧张,又激动,像是已经期待了很久似的,在幽暗的光线里,她的眼睛像黑夜中的两点美丽的萤火。
“不,我要说,这事一定得跟你说……”我明明知道,她在期待着什么。我明明知道,我只要说出了那永恒的三个字,这双眼睛里的萤火就会喷射出来,这颗心就会像蜂蜡一般融化……可是,我却只能受另一种更强大的力量的驱使,说出另一番话来,“你知道,谢霓是我的女朋友,我们已经相处三四年了,可就在前几天,我们发生了冲突。是为你。她有些误会。……你……你能帮帮我吗?我知道,你是个很好的姑娘,又聪明又善良,我也很喜欢你……可是……”我说不下去了,自己也认为太虚伪,我希望她痛痛快快地骂我一顿,然而,她却连一句责备的话都没有。
“我懂了。”她急急地说,抑制不住嘴唇的颤抖,我鼓起勇气看了她一眼,她那种神情真是令人心碎,那两点美丽的萤火在黑暗中熄灭了。
“我会去……会去替你解释的。”
我半晌抬不起头来。心上,有一种沉重的东西在压迫着我,我就用这种姿势坐了好久好久,直到手脚都麻木了。
我心里的另一种东西像刀子似的拉着我。不,不!这未免太卑劣,太不近人情了!我抬起头来,想把这几个月来内心感情的变化、矛盾和痛苦统统向她和盘托出。
她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走了。
“她来过了,替你说了不少好话。”谢霓抱着饼干筒边吃边说,“看得出,她真心真意地爱过你,也许现在还在爱着……”
“后来呢?她上哪儿去了?”
“不知道。也许是上那个养花老头那儿去了?”
“她没有给我留下什么话,或者什么东西吗?”我像个偏执狂似的追问着。
“没有。也许,这件事是我办得不对……可无论如何,这几个月的院外治疗还是对她产生了效果的……”
“别说了!”我突然愤怒地咆哮起来。
谢霓吃惊地望着我,把饼干筒扔在一边。
“她留下的,只有这些小玩艺儿和两幅画,小玩艺儿,你不会感兴趣,那幅‘弧光’在妈妈手里,这幅是阁下的肖像,你拿去吧。”她从抽屉里把景焕给我画的那幅肖像拿出来,递给我,“你抽空把最后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快点给我。我在这个小医院终非长久之计,今年的病理专业研究生我还是要考的。景焕的材料,对我来讲是太重要了。郑大夫已经向我透露了点儿消息……”她越说越兴奋了,“现在国内已经有人搞移情疗法,我得争取抢先发表论文,这对研究生考试有利。……”
她还说了些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我的全部意识都集中在这幅肖像上。我吃惊地发现,这幅本来被认为是丑化了的形象竟如此像我,我还从没有见过一幅画像能这样活生生地画出一个人的灵魂。或许,她真是个女巫吧?我默默地想,打开了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