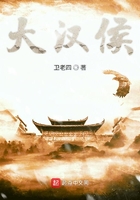我的曾祖见到我二祖父的时候,看着泪流满面,无助的父亲,二祖父没有流露出惊讶,他平静替父亲擦去眼泪,一样无奈的说,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我跟你一样改变不了。这一天呵,早晚都会发生。
曾祖说,惟有你是老大的救星呵。
他轻轻的摇头,缄默半天又说,你以为你儿子是谁呵?我不想救他嘛?这是政治斗争,跟抗战没关系。
你认识那个白志沂嘛?
二祖父点头。
那你跟我回去一趟呵,在他跟前,给老大求一人情。
眼跟前就打仗了,我回不去。请假,那长官也不准呵。二叔的眼泪,突然掉落下来,呜咽道我救不了我哥。
曾祖只带了一封信,那是一封写给白志沂的信。满怀希望的祖父,把那封信毕恭毕敬的呈递白志沂,这位高干撂在公案上,笑得祖父毛骨悚然。
民国三十二年的蒲县,共产党建立的组织,已经荡然无存了。经过晋西事变,和两次肃伪运动,共产党人幸存者极少,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对被捕的同志,无力组织有效的营救。尤为重要的是,中共西北局未派人,重新组建蒲县县委,领导蒲县的抗日和革命。而蒲县这一时期的反共肃伪,成为了第二战区的模范县。蒲县基层党组织主要负责人,都是在这一时期,被捕牺牲的。
惟一被保释的席俊,在三联中学校长刘春浦,和全体师生的竭力担保,其父席道正利用其影响,多方奔走呼吁,席俊最终获释出狱。翌年,在领导那场向临汾军事指挥部,请愿的学生运动中再次被捕。民国三十七年,临汾解放前夕,被秘密杀害。
祖母前后探过三次监,还带我的父亲去过一次。那时候祖母对祖父,不再抱生还的希望了,每一次都哭得悲痛欲绝。祖父也预感到了去日不远,不管那最后的生命,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都注定了生命的寂灭。那庸常的流光,因了短暂异样的珍贵了。他很想留下一些文字,却没有纸笔。在疙瘩山蝎子沟,那个临秋的八月,充满了血腥和悲壮。在枪声响起的刹那,他思想着什么,是否看到了那梦想的风景。
祖父牺牲后的几天,或两天或三天,或是更的时间。祖母才得到枪毙的消息,便带了人步行六十余里来到县城,在蝎子沟的一处草洼里,扒出了被掩埋的祖父。之前,祖母找到看守所的一个伙夫,请他转告这一消息。那伙计也是北塬人,叫郭福奎。他答应了祖母,并且冒险做到了。
找到掩埋尸体的地方,已经有了刨挖的痕迹。是狼或野狗的咬吃,大腿上的股肉,遭到了破坏。当那具残缺的尸体,抬回仁义村,曾祖抚摸痛苦,一村人都哭了。祖父表现的很坚强,他那宁死不屈的精神,成为北塬永远的辉光。
闾长成福挺说,那天他跑掉了,不会死的。
一村人问,他为甚不跑呵?
几十年后,我听到他们的讲述,在祖父的故事里,一样有这样的疑问,他为什么不跑掉呢?因为那是生与死的选择。
目睹祖父最后离开村庄的人们,说祖父月色下的背影异样的从容,和他们熟悉的步履一样,充满了自信。
或许祖父没有想到,再也回不到北塬。或许祖父那从容的步履,是与他热爱的故土,完成最后的作别。
我无法准确的设定,祖父真实的心境。但为了他奋斗的梦想,那短暂的二十九岁的生命过程,充满了理性的传奇。我不知道他生命中的遗憾,是否在寂灭后释然,但在那个世界里,他肯定拥抱了梦想。
民国三十五年,也就是日军投降的第二年,祖母在祖父守望了三年多的北塬,在那棵枝繁叶茂的黑槐树下,终于等来了一个陌生人。那是一个差不多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穿一件北塬常见的紫布马褂,背着行李和雨伞。他小声问祖母,有一个叫成怀珠的人,住在哪儿?祖母说他死了。
他怎会死了呢?年轻人愕然了。
政卫营枪毙的,说他是共产党。
他家里还有什么人?那年轻人又问。
我是他的妻子。
春天来了。
突然听到那萦绕梦境的话儿,祖母愣住了。没有听到回答的年轻人,转身缓慢的离去了。只迈两步,蓦地听到了应答。
冰雪融化了。
他惊喜的回头,看到了祖母萦满眼眶的泪花。
年轻人是来蒲县,与地方党组织接头的同志。中共晋绥分局第九地方工作委员会,宣传部长孙先余。祖母带了他,走进了成得子的窑洞。而后由成得子负责联络,把蒲县幸存下来的党员组织起来,恢复了党组织的建设。
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中共蒲县委员会成立,地委宣传部长孙先余,兼任县委书记,恢复蒲县的革命事业。
假如祖父没有在第二次肃伪运动中,被捕牺牲,假如亲自应答了那句,冰雪融化了的接头暗号,假如祖父参预了中共蒲县委员会的再度组建,他会有什么样的表现,那一腔热血和忠诚,那献身的革命事业,永远有多远。
但这假设的一切,都与他的梦想紧密联系。
曾祖对我们这个尘埃落定的家史,有过追根溯源的设定,假如我的祖辈们,在河南那个陌生的故土,有一个温饱的生存环境,也就没有了那一次,改变生存环境的迁徙。那李姓到成姓,一个简单的改变过程,蕴藏去了一个家族,辛酸的奋斗,或自强不息,或悲壮或凄凉。从对土地渴望的梦想,到认知世界,爱国报国的情结,那样的波澜壮阔。曾祖说他在历史的选择中,是有错误的。我了解那个遥远的选择过程,却不知道曾祖所谓的对与错,假若让他重新作一次选择,他会怎样纠错呢?
曾祖说他的一生,是失败的一生。
父亲说他的祖父和父亲,是那个黑暗时期,北塬的骄傲。因了那些奋斗精神,一个革命者必然的悲壮,为家族带来了永远的辉光。
抗战胜利后,二祖父退役回到了北塬。他对当局充满了失望,也带了对祖父的内疚,离开他曾经金戈铁马的军界。他跪倒在祖父的坟前长歌当哭,在一九四三年的那个秋天,他是祖父生还的唯一希望。但他却救不了胞兄,甚至没有胆量踏上北塬一步。其实,他那悲痛欲绝的忏悔,对于老去的曾祖,那样的无所谓了。他了解二祖父的心境,有着少校军衔的儿子,是另一个儿子,生与死之间的一根救命稻草。在即将失去亲人的惶恐中,伸向那根稻草的手,并且纂牢它,是自然中的必然。也是祖父身陷囹圄后,惟一的营救计划。但又是一次注定失败的营救。
曾祖带着宽容的心境,对待那些尘埃落定的历史,对待他的亲人们。当二祖父告诉他,退役的消息。曾祖的表情和庸常一样的平和,说你个自选择吧。你也用不着忏悔,我明白你救不了他,那是一个自欺欺人的希望……
二祖父做了一个教书匠,他酷爱法书,楷书很有造诣,为北塬人喜爱。寡言少语,永远是一副生病的模样。
他病死那年三十多岁,曾祖最后守望他的时候,怀疑那泪水模糊去的目光,是否出现了幻觉。停止呼吸的二祖父骨瘦如柴,怎样也无法与,保定军校毕业的一个英俊的少校,联系在一起。一如白发人送黑发人,一样充满了悲哀。
那时候的二祖父,是曾祖心目中的脊梁,他生命中最后的过程,最后的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
但那脊梁,猝然垮掉了。
没有了寄托的曾祖,似是突然走进黑暗中去。
若干年后,坐在窑前晒日头的曾祖,直面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静静的回忆中,对二祖父的早逝,多了一层复杂的联想,那些被打倒的牛鬼蛇神,与一个国军少校相比,是小巫见大巫。活到今天的少校,肯定被一脚踏倒在地,戴着纸糊的高帽子,跟那些牛鬼蛇神一道,游遍北塬的村庄了。
一个儿子是烈士,一个儿子是国民党少校,曾祖不知道,那因了抗日救国,分化出去的历史,为这个世代贫农的家庭,带来了复杂的矛盾。假如二祖父还活着,他们会为这个家庭,划定一个什么样的成分。
因了那场不期而至的文化大革命,二祖父的早逝是幸运的,至少回避了一个家族的尴尬,维护了这个家族的荣誉。曾祖说不管甚运动,也不管我的儿子是共产党或是国民党,他们都为抗日作出过贡献。历史那是否定不了的。
红色和白色,在一个家族同时存在,在那个复杂的历史环境中,并不少见。但他们选择的初衷并不是这样,而是带了一腔热血,和抗日救国的牺牲精神,投身那个波澜壮阔的战争中去。他们不知道那个两党合作,最后的结果,那不同的信仰和主张,体制和分化,令他们的生命,异样的脆弱。
在曾祖的记忆和印象中,那尘埃落定的历史,惟余一声叹息。对与错,苦难与悲伤,那样的无所谓了。
祖父就义那一年,父亲十岁。
其实在祖父被捕前后,家境彻底败落了。祖父差不多把能够捐献的东西,全捐出抗日了。曾祖日夜在塬上耕作,祖父不但很少参加劳动,还经常往外带粮食,往家里带人。在营救祖父的过程,欠下了很多外债。为了支持儿子,曾祖陆续卖掉了一些田地。那些曾经给过他无数梦想的土地,在离开他的时候,是怎样的无奈和伤心。三百亩土地,最后剩下不足十亩土地。曾祖在最后一块土地上,坚守着他对土地的梦想。我想那一定包括,重新拥有那些土地,和土地里的梦想。
祖父的那口棺材,是赊来的,折合六百三十三斤玉米。十岁的父亲,做了三年的小长工,还清了那口棺材账。十三岁的父亲,坚守着传统的诚信,对祖父死的意义,却是模糊的概念。因为那坚守的诚信,意味着坚守孝道。他没有父辈的幸运,在那个战乱的年代,和败落的家境,接受教育只能是他,一个无法企及的梦想。
一九四六年的初春,退役的二祖父,这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是否送父亲接受教育,态度是冷淡的。他说知识在这个年代,没有用处。借用知识看清楚了这个世界后,会感觉人生毫无意义。
不主张父亲接受教育的二祖父,和侄子一样,对刽子手有着刻骨铭心的仇恨。新中国解放后的一九五一年,蒲县人民政府,召开第二次镇反大会,伪县长郑继文,参预杀害祖父的反动组织头领张新田,等六人接受人民的审判。
那一年父亲二十岁。
父亲从一个懵懂少年,成长为一个是非分明的青年。
消息传到了北塬。
父亲去学校找到了二祖父,他希望二祖父跟他一块去,参加那场镇反大会。二祖父正在上课,透过窑洞的窗户,看到了情绪波动的侄子。或许在父亲获得消息之前,二祖父已经得到了消息。他一字一句的朗诵课文,那样的从容,似是那镇反枪毙的反革命分子,跟他没什么瓜葛。
父亲等的很着急,当那下课的铃声敲响,他看到抱着教科书的二祖父,一步迈出了窑洞,在喧噪声里问,有事嘛?
县城召开镇反大会。父亲说。
这是好事。二祖父说。
不光有伪县长郑继文,还有那个刽子手李新田。父亲又说。
知道。罪有应得。二祖父说。
二叔,我们一块去。父亲说。
你一个人去吧。二祖父说。
我身上藏一把镰刀,砍死那狗日的。父亲说。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你有这个胆量和勇气,你父亲也该眠目了。二祖父说,县城远了,我走不到地方了。二叔支持你。有仇的报仇,有冤的伸冤,这也是政府的口号。你报仇,没有错。去吧。
父亲一个人去了县城,困惑了一路,他不理解二祖父为什么不参预。其实,那时候二祖父的身体,还允许去一趟县城,内心也有着和父亲一样的仇恨。他渴望目睹,那些刽子手最后的下场,但他少校军官的历史,和那不光彩的出现,让他放弃了这最后的快意恩仇。经历了快意恩仇的父亲,还不尽然理解二祖父。又是一个若干年后,老去的父亲回忆那一刻的快意恩仇,突然理解了二祖父的心境。那血浓于水的亲情,在那无奈的拒绝里,充满怎样矛盾复杂的伤感。
镇反大会期间,上台控诉的人很多。没有人注意一个复仇的年轻人,包括负责镇反的解放军战士。父亲突然跳上审判台,抄出镰刀砍去。猝不及防的战士,还是慢了一步,那挥去的镰刀,划伤了张新田的腿部。
父亲不肯罢手。
县长赵正萍问,年轻人,叫什么名字?
成怀德。
你的父亲是成怀珠嘛?赵正萍又问。
是的。
听到回答的赵正萍吁出一声叹息。说我认识你的父亲。他死的很英勇,也很伟大。成怀珠同志,是蒲县人民的骄傲。
我是从祖父那些,差不多同龄人的回忆文章里,或多或少了解祖父的。但更多的是曾祖和父亲的讲述。在彭华纪念文集里,这位曾在抗战时期,担任过蒲县县委书记,解放前后一直担任四川绵阳地区,主要领导人的回忆录中,讲述开辟蒲县党的建设工作,和晋西事变与奔赴延安等章节中,多次提到我的祖父。在祖父的帮助下,安全达到延安的很多前辈,都曾在回忆中,讲述与祖父并肩战争的友谊。
我不知道这样的讲述,是否可以划上一个句号。
或许那些远去的历史,因了这篇回忆的文章,在人们的生活中渐渐清晰起来。在那些陌生的记忆和印象中,或深思或掩卷一声叹息。认知我们的今天和未来,与那远去的历史,其实那样的紧密联系。
我怀念我的祖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