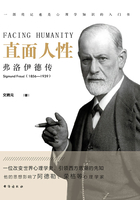在北塬的风景里,遗存着我父辈的生命过程,或辉煌或平凡,都在流光里成为了永远的记忆和印象,令人在漫长的历史中嘴嚼涵咏。但那熟悉的风景里迷失的,是远祖不变的故土。因了沧桑变幻,那模糊的追思,只作了美好的向往。我热爱蒲县北塬,澎湃的血统,又令我不敢忘记陌生的另一个故土——河南省的林县。这两省的两个故土,都或多或少成为我生命中,最最重要的一部分。
依照北塬的方言,我们这个家族个自的历史,充满了悲壮和灰。祖父那追求民族解放,献身民族的牺牲精神,和两个故土一样,是从曾祖支离破碎的讲述中,有了一个了解的过程。一个在蒲县庸常的家族,有着无尽的辛酸和漫长的成长,那在当地革命史志中熠熠生辉,慷慨赴难的国之就义,其实并非所谓的灰,而是一个家族,一个遍燃抗日烽火,三晋大地的骄傲和辉光。在万千为革命牺牲的三晋英烈中,至少我的祖父不应被遗忘。那把革命进行到底的生命过程,蕴藏了一个共产党员,谋求民族解放的坚定信仰。
祖父成怀珠凛然就义是在一九四三年,人生二十九岁。那一年灾难深重的民族,已经看到了抗战胜利的曙光。坚持在三晋抗战的八路军、牺盟会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淳朴勤劳善良的北塬,依然置留在长长的黑暗中……读初小时候,差不多每天都能看到曾祖,伫立在那个叫蝎子沟的塬上,向南眺望的形容。他那在黄土浮扬的思绪,和微翘的胡须,迷惘的目光,不知丢落在哪儿。沟底蒸腾的炊烟,夕照的霞辉,把他回映的背影,融入不变的古色古香中去,回到遥远的记忆和印象中去。他看不到梦中的故土,等不回牺牲的儿子。但那习惯的等待中,充满了太多的寄托和梦想。
离开河南故土的曾祖,在北塬度过一生,再也没有回到魂牵梦萦的故土。我对那个不是故土的故土,没有丝毫的慨念。一如在私塾中成长的曾祖,与读初小的曾孙,两个一样陌生的世界,根本找不到沟通的平台。我无法理解曾祖,或许他理解我。总以为他在等待我,但不知道那只是等待的一部分。假如没有日复一日,漫长的等待过程,在祖父最后的生命过程里,还会有什么期待。
曾祖昏花老去的目光,丢落在我身上的那一刻,异样的幸福。他用一双枯瘦的手,疼爱的牵住我的小手。结束了等待,也结束一个泛黄的幻象。一面回走一面问学习了什么新课。入学前曾祖教过我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我不喜欢那枯燥的千字文。
下沟的道儿深,曾祖的手纂的很牢,过半后我总是摆脱曾祖的手,啷啷呛呛奔下沟底,窑里搬出床床。曾祖笑着坐到床床上,冲炉子里,母亲呱嗒着风箱,窑浮上头窜着浓烟。沟里四处生满了野稞子,窑前菠箕大的平地,放个一张四的小柴桌。曾祖望着日头,闻着毛山药的香味儿,讲着他不厌的话题。
上学捏阁不得,那是个自哄个自,背来背去呵,书包空了,个自也空了。想吃角儿呵,要下功夫。
嗯。我应着,一面埋头写作业。
听清了。也不指望大出息,个自不愁吃穿,是福了。
嗯。
从前呵,我送你爷爷读书,打算城里熬相公。他不干,跟着毛主席。听了话,不会被人家杀了。新社会不兴熬相公了,那你就做一个公家人,端铁饭碗儿。旧社会的相公呵,铺子里柜跟前,那也是好营生。
啥叫相公?
就是合作社的营业员。解放前古县都没有,蒲县城才有。也就东西一条街,土路,短的一眼尽头了,没几家铺子。
日头照不进沟里了,野雀子飞走了。静谧的一遛儿蝎子沟,惟余几声蝉噪了。曾祖下炕点亮了油灯,一丝不苟的铺展草纸。那时候我的父亲参加了工作,因了苦大仇深,在县政府的一个科室服务。塬上不容易买到的煤油,父亲每次都带回一瓶,还带回了一盏美孚灯。薄薄的玻璃罩里跳着灯芯,很明亮。
曾祖醮了毛笔,一笔一画很仔细的写字,只写一页纸,十天后再写另一页。内容是我学习的语文课本,之后我比葫芦画瓢临帖。初小开毛笔字课程,曾祖发一本薄薄的字帖,说字是门面,要练好毛笔字。我问有铅笔钢笔,毛笔还有用呵?他说大用处。毛笔是丢不了的,古时候凭了一手好字,做官的人很多。我又问人为什么要当官呢?他笑说你不懂。长大就明白了。读书呵,顶重要的就是功名。
其实,曾祖的很多话我都不懂。
曾祖突然浸淫往事中去,在灯辉里迷惘,轻轻絮语:你的二祖父,写了一手又粗又黑的毛笔字,不光在塬上,古县一方都有名气。他还读过保定军校,弃笔从戎抗日报国,又报国无门,走错了路呵……
对我那位二祖父成怀德,和祖父成怀珠一样没有印象。但他却是北塬很有名望的人物,在晋绥军当过少校军官,坐过卧车的,解放后做中学教员,又写了一手很好的书法。对谁都是有求必应,为人忠厚,又是一个热心肠。离开晋绥军后,曾经一身襟抱和梦想的热血青年,失望后成了一个醉壶子,只做了几年教员,病榻沉疴抱憾逝去。
在曾祖的认识世界,对子女的教育是失败的,惟一正确的认识,是强制接受教育,和对知识世界的迷惘。中学时期他谆谆告诫我说,不管结果如何,知识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东西,至少可以帮助你,认知这个世界。我牢记了曾祖这句话,才有了今天读硕士、博士的阅历。我感谢曾祖的教诲,我怀念我的曾祖。他的善良勤俭,广博的知识,和对我的鞭策和期望,是我前行的力量。
我弄不清楚,对曾祖讲什么,用什么样的努力,让他在九泉下欣慰。但我知道他一直在关注着我,一个叫成文革的曾孙。我想对知识的渴望,直到今天,漫长的求学之旅,是对他最好的回报方式了。
曾祖是一个纯粹的农民,因了知识和对事物的理解,又不是一个纯粹的农民。严格的讲有两种身份,第一个是北塬的农民,其次是北塬古县镇上,商品贸易的经营者。用他区别于农民的知识,成为北塬成功的典范。三百多亩地的置业,一个读太原一中的儿子,一个读保定军校的儿子,足以说明一切。但他又摆脱不掉小农经营的思想模式,甚至或多或少继承了传统的保守和诡诈。假如曾祖尽去这些传承的思想,或许就会改变我们家族的历史。这是我的祖辈父辈们,无法认知的东西。
祖父太原一中的缀学,和二祖父完成保定军校的学业,跟曾祖的选择有很大关系。曾祖从不讲其中原因,但我相信他的内心充满了悔悟。当日本人逼近山西,首府太原乱成了一锅粥,祖父从被迫停课的太原一中,带了惆怅和襟抱,回到了塬上。最初曾祖打算送他去北平读书,之后又否定了计划,让父亲在北塬很快成家立业,倾资支持二祖父在保定的学业。二祖父进入军界的未来,给了祖父太多的期待。
曾祖做出决定前,只对祖父讲了一句话,有一个在外当军官的人,足可以撑起一片天了。世道越来越乱了,最有权势的是军队。乱世出英雄呵!没个把儿我们家也能出一英雄。祖父不响。因为保定北平,只能选择一个。曾祖缺乏供给两个儿子同时读书的资费。因为战争必然死人,直面一个无法预测的世界,企望一个留在身边,传承一个家族的血统和未来的存在。
我无法猜测祖父,是否明白曾祖复杂的选择,但曾祖一样被这一矛盾困惑。一直到他老去,依然带着最初选择的阵痛。假如祖父去了北平,那些尘埃落定的历史,也许将被改写?
然则在曾祖踏上陌生的北塬之前,在越来越远去的故土,我的宗祖们,是那片极度水资源匮乏的山坳,最纯粹的农民。当我看过那部红遍大江南北的名叫《红旗渠》的电视剧,为有那样不畏艰难的老乡骄傲,却无法体味宗祖的苦难。他们远离故土,翻过巍峨的太行山,西行的目的,是为了寻找一片更适合生存的土地,至少那儿有充足的水源,和肥沃的土地。在陌生的北塬,他们停下了脚步,虽然这儿有水源,也有肥沃的土地,但等待他们的是和故土,一样饥寒交迫,并不是他们梦中的桃花源。
在漫长的迁徙过程,这个渴望温饱的家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看到五鹿山之前,曾祖的母亲,疬饿中客死异乡。最初出发的目的,是富饶的关外。走出山海关,在那片人烟稀少的黑土地安居乐业。选择北塬的原因,不是美丽的五鹿山,而是没有力量走出北塬。
曾祖没有眺望过山海关,因为在他的世界,山海关外那片富饶的黑土地,无法与他未来的生命过程,联系在一起。在他的内心,对家族的这次迁徙,充满了怨望。只到他最后的生命过程,依旧不理解父亲的抛弃。那天在塬上的离别,是父子生死之别,从此曾祖再也没有见到父亲。
在曾祖的记忆和印象中,父亲的形容是模糊的,在塬上风沙里那个渐行渐远的背影,却深深烙在他的心底。他极少触及,走进一个陌生家庭的辛酸往事,总会引得他流泪不止。他从来没有试图,寻找那些音信两茫茫的亲人,也无从寻找他们。但在他最后的生命过程里,亲人的形容,异样的清晰了。他笑着告诉我的父亲,他看到了他的父亲,他们在遥远的桃花源,等着他呢。
这个迁徙的家族,在古县镇喘息了数天,他们第一次看到了陌生的蒲剧。戏名叫《杀狗》。曾祖的父亲听不懂蒲剧,也不是来戏楼听戏的。他牵着曾祖的手,在冷冽的北风里,跟着古县的一个杀猪掌柜,站到一个揣棉袄袖子的中年夫妇跟前。他们仔细半天,点头了。那掌柜伸手又替曾祖擦擦鼻子,指点上还染着猪血猪油,和一身的骚气。那对夫妇又瞟一眼,说明孩儿脸洗干净了,送欧家村来。
翌日,屠户带了他们来了欧家村。中年夫妇不让他们进村,不许见窑洞。风很大,他们在塬上等。只来了中年男人,往屠户手里撂下两块龙洋,屠户又很牢的扣在曾祖父亲的手里,交易结束了。
中年男人拉了曾祖的手,看着他们一步步远去。曾祖没有哭,只瞪圆一双迷茫的眼睛,似是明白不管怎么哭闹,一切都无法改变。
那一年曾祖八岁。
故土的山体,是石质结构,没有依沟依山的窑洞。北塬的贫瘠,曾祖是熟悉的,窑洞却是陌生的。下沟的曾祖很惶恐,在沟底最终哇一声,哭嚎出来。中年男人问,你哭啥?窑里有圪窝吃。
曾祖继续哭,不愿走进窑洞。他愿意跟着,没有圪窝吃的老子。
李立志改名成立志,这个名字成为曾祖,最终的名字。这家姓成的人家,是北塬殷实的农户,兄弟四人,惟有老二没有儿子。于是便收养了我曾祖,延续香火养老送终。我们这个家族,才有了扎根北塬的契机。
曾祖说那是宣统三年的春天。
吃圪窝的日子并不长,曾祖便成了多余的人。收养曾祖后,成家突然喜得贵子,他们想赶曾祖出门,又怕塬上的人讲闲话。曾祖饥一顿饱一顿,差不多做了他们家的小长工。曾祖跑到古县镇,找过他的父亲。那个挑一副担子,只做了古县镇过客的河南侉子,在北塬的沟壑,没有留下丝毫痕迹。
曾祖又回到塬上放羊。因为没有人帮助他,改变羊倌的命运。
之后,他又试图原路返回河南,但又找不到回家的路。走不出北塬的羊倌,又回到那个不愿回的屋檐下。他的种种表观,惹恼了成家二爷,拿一束荆条很揍了一顿,似是那两块龙洋,找补了回来,扫地出门了。
曾祖在沟里睡了几天,可怜他的邻居,施舍他几个山蔓荆。伤势虽是一点不减轻,几个马铃薯保了命。成家老大是一个极善良的人,顶不住沟里的风言风语七嘴八舌,又可怜一个外乡的孩子,领了一个弃儿回了家。
这个村子有一个很好的名字,叫仁义村。
成家老大的仁义,让曾祖继续留在了北塬。又因了接近温饱,令他忘记了亲人,和五鹿山东面,那遥远的故土。
曾祖是个感恩的人,伤痛尚未痊愈,便牧羊塬上了。那时候北塬有很多羊倌,畜牧业差不多是农作物外的第二产业。在偏僻的北塬,不知道三十五公里外的县城,北去遥远的太原,远在天边的北京,发生了什么事儿,正在发生什么事儿。
据说成家大爷读过私塾,但算不了一个纯粹的读书人。不戴石头花镜,窑里却藏了几本书,《千字文》、《诗经》,包括《三国演义》、《水浒传》、《施公案》、《二十四孝图》。讲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最为传神。他没啥学问,却向往读书,和五鹿山外的仕途。在仁义村他是惟一,以书香人家自居的人。窑壁上挂着蒲县名家曹肇绪的墨宝,四条屏山水画,摆放着陶器官窑粉彩画瓶。
距离老窑数丈外,又雇人修了一座窑洞,壁上照白,地上墁砖,课桌凳子大炕,样样儿收拾停当了,请来了一位私塾先生。那先生是从柏山上的东岳庙来,戴一副石头花镜,成家大爷说他姓席,是曹肇绪的学友,大学问家。花白的山羊胡子,跟羊倌的头羊差不多。腋下夹一紫花布包裹,慢腾腾的走道儿。包裹里那几本,早已过时废弃的教课书,足够一窑孩子,啃上十年二十年。
曾祖从塬上,赶一群羊下沟。嘈杂的叫声里,扬起很多尘土。他甩着羊鞭子,鞭花儿很响亮。
成家大爷喊,立志,往圈里赶。别赃了先生的腰腰。
席先生拍着坎肩,看着塬上的曾祖问:哪一个?
皮儿。成家大爷说:先生,您窑里请。您来了,哦这心里就不沉了,光宗耀祖呵,一准有指望。
席先生说掌柜的,你先宽展了,过三年五载,再给您一句话。学问不是人人都能装进肚子,讲缘分,重悟性。
成家大爷笑说,先生,哦懂。犬子拜托您了,打骂都由您,只要您调教出来了,您就是成家的大恩人。
席先生笑着不响。
成家大爷又喊,福堂,给先生磕头来。
成福堂是成家大爷的独生子,很娇惯,跟曾祖父去塬上放羊,多半是好玩。他们关系处的很好,跟亲兄弟一样。
磕罢头爬起来,成福堂问,明早立志读书嘛?
成家大爷说,他读书了,那群羊谁放去?
席先生一声叹息说,那孩子到是一个读书的材料。
成家大爷迷惑地看着远处的羊倌,絮语道我们家福堂,不比他差呵?
圈了羊,曾祖拎了鞭子,赤脚站在席先生跟前,趴在地上磕一头,大声叫先生。席先生拉了他手问,识字嘛?
曾祖摇头。
席先生又问,想读书嘛?
曾祖点头。
席先生说,羊饱了肚子,你来天课。
曾祖仰脸看成家大爷。
听先生话。成家大爷说,席先生不在乎多一个学生,一只是放,一群羊也赶。你们哥儿俩,较劲儿读书。
曾祖说我听话。
成家大爷接了席先生的包裹,陪了这位老秀才,一步步挪进窑里去。
他们用不着跟进去,但他们很想看一眼,先生带来的孔夫子的画像。蹑手蹑脚靠近窗户,隔着窗格子往里瞅。过年贴的新窗纸,经了春风一拂褪了颜色,也脆了。破去的地方张扬着纸片儿,夕照的光辉里,窑内很清晰。成家大爷为先生斟茶,炕头上下端坐,呷一口香茗聊开去,那些过耳的话儿,尽是一些塬上的风情,蒲县文人的趣事儿。半天,谈笑风生的席先生,没有动包裹的迹象。搁在小八仙桌上的包裹里,藏着圣人的画像。明天开课之前,首先向先师磕头。
他们很失望,怏怏离开了窗台。
他们牵了手西去,往沟里深处走。枝头的雪娃子,唱出这一天最后的歌儿,草丛的黑驴子,还没有叫喊。憋足嗓门儿的知了,钻耳孔的发毛。照进沟里的光辉,似染了一层雾气。
爬到半坡儿,成福堂说瞧他那眉眼儿,像是有学问。他来北塬做甚?咋不去山外的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