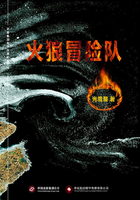冯乐礁睡的是驾驶舱里的上铺,上铺比较干爽与舒适,不像下铺有些潮湿和闷热。不管怎么说,冯乐礁是客,范老桅说啥也不肯让老亲家睡到下铺来。按理说,浪是这么节奏分明,船的颠簸也是舒缓有致,又比岸上凉爽得不知多少倍,对于长年跑船的范老桅来说,本应该更容易入睡,可他却大睁着眼睛望着舱外海天不分的茫茫夜空,静听着海浪一下接一下地拍打着渔船,久久不能入睡。
范老桅一生无数次地与风浪拼搏,三四米高的大浪他都能轻松地对付,只有对自己的孽子范二毛,他实在是毫无办法,冯水花对范二毛不好,他能原谅,他不能原谅的是冯水花污辱范家。不能在一块过日子不怕,那就分开,各走各的路,干嘛给范家戴绿帽子?你冯乐礁太死心眼了,亲家做不成了,兄弟还做不成吗?反正二毛已经下大牢了,他要和老亲家挑明,不做亲家做兄弟。
躺在舒适上铺的冯乐礁此时也无法入睡,他的思绪和摇动的渔船一样,在时间与空间之中杂乱无章地飞翔。这些年来,只要和范老桅在一起,他就摆脱不掉那种负疚感。随着他们儿女之间感情的日益寡淡,冯乐礁的负疚感就越加深重,他憎恨自己的闺女,咋就不给范老桅生个一儿半女,有了孩子拴上身,冯水花的心再漂浮,也会被孩子压瓷实了。想想当年,若不是范老桅拼了命保下他家那艘120马的大渔船,他们一家三口早就葬身鱼腹了,哪还有今日冯家连县长都羡慕的辉煌,更不会把冯水花娇惯成如此随心所欲,瞎美臭浪,成天粉面桃花地在渔村神气十足地走来走去,拿自己的丈夫不当人。
冯乐礁隐隐约约感觉到,下铺的老亲家也没有睡着,翻来覆去地烙烧饼。他不忍心老亲家一个人孤独地折腾,便说,还没睡呢?
范老桅停了好一会儿,才应了声。
冯乐礁说,要不,坐起来唠唠?
范老桅知道老亲家嗜睡,睡不醒就难受,便说,睡吧,有啥话,明天说。
冯乐礁长长地叹了口气,说,我对不住你呀,亲家,你心在想啥我知道。
既然窗户纸捅破了,范老桅也就没必要回避了,反正他也要说呢,这一次他要让两个孩子彻底解脱。范老桅也长叹了一口气,说,我就弄不明白,这老辈人和小辈人咋就尿不到一个壶呢?咱老哥俩,从小到大,谁不把爹的话当圣旨。
冯乐礁似乎好受了些,老亲家终于说话了,他就想趁势多说几句,让他的心再顺一顺。冯乐礁翻了个身说,谁说不是呢,这老一辈小一辈,中间就好像隔着道大海沟,我是一心一意让咱两家成为亲戚加兄弟,可孩子们就是不顺咱们的意呀。
范老桅说,孩们的心思,咱们猜不透啊,我看,是越管越坏菜,眼下,二毛还在牢里,还得蹲上十年啊,十年,你闺女也该老了,我不能眼看着她守活寡,他们的事儿,让他们俩商量着办吧,也该分手了。
冯乐礁激动了起来,他说,只要我活着,冯水花他休想离开范家。
范老桅说,捆绑不是夫妻呀。
冯乐礁说,没有亲家你,哪有冯家的今天啊,还是打的少,打怕了,她就老老实实地呆在你们家了。
范老桅啧了下嘴,老亲家本是开通的人,咋就在这件事儿上一根轴呢,他不想唠下去了,便一针见血地说,老哥呀,十年啊,冯水花怎能守得住?那顶绿帽子压在范家头顶这么多年了,压得我都喘不过气来了,你还捂着,不让摘下来,非要留下个亲家的名头,不是亲家,就当不成兄弟了?
冯乐礁不说话了,留下一个接一个的叹息。
一夜未眠。
驾驶舱的上铺正对着驾驶台四通八达的瞭望口,第一缕光亮扯开混沌的夜色,淡淡地表现在冯乐礁的身上。冯乐礁睁开眼睛,天边已有鱼肚白,鱼肚白的光亮虽然还很微弱,却把海天分得格外清楚了。
大海早已不似昨晚那般安静,浪拍船舷的声音,响得十分透彻。此时的天与海虽然都是暗灰的颜色,可天是无动于衷的灰暗,海却到处波动着不安分的灰暗。渔船在灰暗的大海中,渐渐明朗。
范老桅已经醒来,海和天在不知不觉中,分得清朗了。他走到船舷,冲着大海里起伏着的波浪,响亮地放出一泡尿水,然后抻足懒腰,运出单田之气,和每次出潮一样,底气十足地吼了一嗓子:
起网了——
起网是范老桅出潮时最为舒服的时刻,出潮打鱼就是为了收获,只有起了网,才能知道收获的价值。范老桅记不清,活了六十多岁出了多少次潮,甚至出了多少年潮,也需要屈指算算。惟有这一次出潮,范老桅对起网的兴奋不再是因为收获,收获不是这次出潮的目的,他把这次出潮当成了一种纪念,一种告别海上生涯的仪式,否则,他不可能象征性地带出为数不多的几片浮网,而且是那种根本不想把鱼子鱼孙打上来的大网眼渔具。
于是,范老桅发自心底的喊声,带有了几分表演的意味,那意思似乎是在说,他范老桅根本没有老到不能捕鱼的程度,就退出了海上生涯。他无法阻止别的渔船对鱼子鱼孙毫不留情的围剿,起码他是不想再为锐减的辽东湾鱼类做计划生育工作了。或许,他的余生就完全交给冯大岸的种苗繁育基地,亲手把鱼卵抚育成小鱼秧子。
面对着辽阔的大海,范老桅又一次吼着:
起网了——
网浮在大海里,既蜿蜓曲折,又轻飘飘的,卷扬机卷起的网,还同撒网时一样,保留网的原样。显然,极会看流下网的范老桅,根本没拿海流当回事,只求回去的时候别饿着就行了。
被卷扬机绞上来的网,也不是一无所获,偶尔也有嘴巴尖尖身子长长的青条子随网入船。伏天的时候,母青条子大多已经甩籽,一个个都是干瘪的肚子,偶尔有肚子鼓鼓的母青条子活蹦乱跳地被网扯进船来,范老桅就立马把鱼择下网去,弃入大海。那鱼便像蛇一样扭曲着身子钻进了大海的深处,寻找生儿育女的窝巢去了。每逢网上挂到蓝点马鲛时,范老桅便有些惋惜了,这种鱼是辽东湾里最凶猛也是最有志气的鱼,追起小鱼来,根本就不瞅前面有没有网,一旦撞了网,哪怕网仅挂它的嘴丫子,也不会回头脱身,活活地把自己气死了。
别说是辽西走廊里最有名气的海鲜饭店里看不到活着的蓝点马鲛,就是能把它捞上来的渔民,也没人见过活着的,除非你亲眼看到它撞网,又手疾眼快把它抓上来,你才能在手中感受到它生命最后一刻那一下子震颤。这种鱼,刚刚捕上个把时辰,身子还硬挺挺的,放入锅里清炖,出锅时再撒上一把香菜沫,又鲜又香又滑又嫩。可是,待到返回码头,鱼就会弯得比面团还要软,肚子也破了,眼睛也灰了,再入锅去炖,肉味酸溜溜的,不鲜也不香了,只能用盐淹了,晾成咸鱼干。
吊在网上的鱼少得十分可怜,好多片网除了挂上几缕绿得鲜艳的海白菜和紫褐的海草,几乎是空空如也。十几年前的海哪像如今这么寒酸,随便在海边钉几个橛子支起一个架子网,赶上两个落流子,就够两个极富推销经验的鱼贩子走街串巷卖上一整天了。那时用这种笨法打鱼的人,不是穷得置不起网具,就是不敢冒险只能挣小钱的人,真正的渔民把眼光紧紧地盯在了大的鱼群和肥硕的对虾上,成千上万地挣大钱。不像如今的人们,已经把粗糙的架子网进化成了八卦阵似的须龙网,任精明得无数次漏网的大小鱼类插翅难飞。
范老桅至今也弄不明白,二十年前的海,肥厚得流金淌银,别说是味道鲜美的鲆鱼镜鱼,也别说个头不凡的鲈鱼、梭鱼,更别说海鲜之冠的对虾,就是刚刚被日本人看中的海蜇,也是多得被海浪一层层地往岸上推。那时候,稍有点儿心数的人,只要能买得起盐和矾,加上手脚勤快些,用手推车把又腥又臭的海蜇运回家去,淹在几口大缸里,准能白捡个万元户。
冥冥之中,范老桅总是感到,那场海难是大海对渔民们无度滥捕的严正警告,或是残酷的报复,否则,海里的鱼怎会在第二年的鱼汛期骤然减少到难以置信的程度呢。
那场万劫不复的海难呀,仿佛把大海撕碎了,把一个貌似从前却又完全陌生的大海摆在人们的生活中。那个到处漂浮尸体的日子,想起来至今还会让村里的人心碎欲裂。范老桅能很容易地忘掉劫后余生的人们,他却终生不能忘记那场持续了将近一夜的暴风骤雨和滔天大浪对渔村的摧残。
海难,不堪回首的海难已经被时间蒙上了灰尘,大海不会再有从前的那种激动人心的收获了,也不会再有那种撕心裂肺的海难了,大海成了平静的大海,大海也成了无所作为的平凡大海。
52
海与天越来越清楚地显现出来,几颗最后的星辰黯然失色地隐去了身形,除了东方的那带天际淡得发白,整个天色纯静得湛蓝湛蓝。一抹淡淡的红色不易察觉地抹在了东北方的海平线上,渐渐地把那一方的天与海染成了一小团绯红颜色。马上就能看到海上日出了,范老桅和冯乐礁虽然无数次地闯海跑船,却极少碰到这么好的天色。很多时候,海上日出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辉煌,晨雾与薄云总是阻挡着太阳与人们开门见山的友好相处。
那一方天与海之间浅淡的绯红渐渐地扩大了,并且越来越红艳起来,红得鲜艳欲滴。接下来,那方天空就拱出了一个赤黄的弧形,仿佛是在给将要诞生的天之骄子铺设了一个十分舒坦的产床。红得流血的太阳从海平面上拱出头颅的时候,并没有显出诞生时的阵痛与艰难,而是直截了当地拱出个月牙似的殷红脑壳,随后不是一点一点地往上升,而是一节一节地往上窜跃着,直至最后才恋恋不舍地与大海粘连了几个回合,一跃而起高高地跳离了海平面。
虽然海上日出是在毫无声息中结束的,可范老桅还是听到了太阳出生时刻那种呐喊、撕杀、愤怒和呻吟的声音。可这种声音在太阳独立地跃上了天空,并且剥除掉软弱的红色外壳,变得黄白炽热的时候,一切糟杂之声便全部消失了。只剩下太阳威严的光芒,默默地从遥远的天际给范老桅的渔船铺设了一条波动着的金字塔似的金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