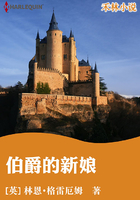20
又是伏天,又是休渔的季节。
冯大岸记不准这是第几次休渔了,他只记得第一次休渔时,老桅叔丢下他80马的渔船,趟着落潮时的细浪,迈进了村旁亘古不变的万年老滩。那天,老桅叔宽阔的肩上,坐着光着屁股,浑身晒得黢黑,欢快的小孙子。小孙子范天齐,露着两排芝麻乳牙,指着海滩上密密麻麻滚滚爬爬的海物,没完没了地问,老桅叔一一告诉,啥是鬼头蟹、啥是大爪蟹、啥是扣蛛蟹、啥是扁毛蟹。当然,这些都是没法吃的小破蟹,只有蹩脚的鸭子才会喜欢,渔人踩上它们都觉得硌脚。老桅叔不愿意理睬这些小破蟹了,撒开他坚硬的赤足,紧跑几步,追上从他脚下溜走的潮水。他用能张开的脚趾,去捉在水中横跑的红夹蟹、花盖蟹,甚至还有梭子蟹,这些蟹子的大螯,足可以夹断范天齐的小嫩手,范老桅腾出一只手,把蟹子从脚上接到手中,用牙齿咬碎蟹子的大螯,才送到孙子的手中,让孙子玩。
这一幕幕的情景,好像是昨天,可是,那已经是昨天以前很久很久的昨天了。冯大岸再也看不到那个光着屁股在海里滚来滚去的范天齐了。现在的范天齐,是个身材颀长的初中生了,天不亮就骑着自行车,到镇里的学校,端庄地坐在课堂上,只有天快黑了,才能回家,几乎承受不着海边灼热的太阳和腥咸的海风,脸儿养得和他妈一样白,一点也不像渔村的孩子。
和范天齐不再是从前那个范天齐一样,老滩也不再是从前的那个老滩了。从前那个老滩,落潮的时候,只有村里最没能耐的人和猪鸭之类的才去滩涂上赶小海,海物多得随便挖下一锹,就能从泥沙中摸出一把蚶蚬蛤蚧。现在的老滩,十里八村的人都来赶小海,每落一次潮,老滩里人山人海,铁锹把整个滩涂掀个底朝天。那些日本企业的代理商,开着一溜保温车,守在岸边,就连海里最没用的,被人们称为海虫子的沙蚕,也被高价收购一空。
潮水愤怒了,汹涌地涨上来,驱赶走了人群。潮水像受伤的野兽,伸出长长的舌头,舔舐着遍体鳞伤。可是,涨朝的海水刚刚抚平完老滩的创伤,潮水一落,多如蚂蚁的人群,对老滩又是一轮满目疮痍的伤害。
冯大岸听见了海在呻吟,他相信,他的老桅叔,也听见了海的呻吟。
冯大岸不想看到天翻地覆的老滩,不忍心自己的家园如此地被人蹂躏,可他却没有办法去阻拦,他只能眼不见心不烦,去到大海的深处,去做真正的渔民。
正午时分,天蓝得发紫,太阳直率地洒下来,大海也被晒蔫了,连波浪都懒得推动。港湾里密密麻麻的渔船也像人犯困了一般,在平缓的波浪中接二连三地打瞌睡。
空气腻得发黏,阳光大粒盐一般,白花花地砸下,灼疼了人的肩膀。冯大岸就是在这个时候,带着会看机器的轮机手董航,还有满身蛮力的二憨,悄悄地潜入了码头。渔政的屋里没有空调,热得受不了,谁也不知道孙子跃跑到哪儿纳凉去了。因为是休渔,简易的加油站,也是空无一人,只剩下高高的空油罐在码头上站岗。
原本喧哗的码头,此刻却无比的安静,惟一的声音来自岸上歇斯底里的蝉鸣。
冯大岸本想带着更多的船工去偷捕一次,经验告诉他,大海也禁不住这么暴晒,鱼儿都躲到海底,夜晚的时候,都会浮上海面,来补氧,来觅食,正是下浮网的好时机。可禁渔期,渔工们都返回了老家,再说了,这次是出去偷捕,不适合带更多的人,三个人摆弄120马的渔船虽然有些累,还不至于无法出潮。
当然,冯大岸这次出潮,不会有被渔政烧了网扣了船的危险,因为他看到妹妹冯水花描眉打鬓了。他知道妹妹这一举动的目的是啥,也就无从担心孙子跃会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了。
董航下到底舱发动机器去了,因为机器有一段时间没用了,发动了好几次才发动着。二憨呢,解下拴在岸上的缆绳,跳上船来,走到船尾,扯住了锚绳,用力地拽着。船便顺着二憨的蛮力,徐徐地飘入海中,直至二憨将大锚从海底捞上船尾。冯大岸才将渔船由怠速状态略微加了一点儿油,几乎没有多大的声响,渔船便悄悄地出港离岸了。毕竟是偷着出潮,冯大岸不想弄出多大的声响,二里地都能听到马达声,弄不好谁一多嘴,告了一状,渔政的快艇追上来,这一好潮又白扔了。
好久没有这么蓝的海了,出了岸边没多远,刚刚驶入深海区,海便蓝得让人沉醉。一年三百六十天,辽东湾的海面,不是裹在雾里,就是旋在风中,所以海水不是泛白就是泛黄,像今天这样,天一样的湛蓝,天一样的安静,极为罕见。
岸的影子越来越小了,怀抱着整座渔村的龙湫背,居然是那么小的山丘,渔村里的房子比火柴盒子还要小,就连人们公认的顶天立地的天柱礁,也小得蜡枪头一般。
用不着担心人们听见渔船的马达声了,冯大岸一节一节地提升船速,马达由低缓的轰鸣,渐渐到了“嘎嘎”的脆响。渔船拖着浓重的黑烟,直扑大海的深处。机器吼叫着,船的速度招来一阵阵海风,一种涤肝清肺的凉爽从心底油然而生,酷暑顿时被丢到了岸上。
渔船就这样一味地向着大海的深处驶去,直至晚霞烧红了大海,海面上到处跳跃着血一样的波浪,渔船还没有停歇的意思。冯大岸不是不想在离岸近一点的地方撒网,离岸近了,会躲不开渔政的快艇,人家船上有望远镜,有雷达,能探到十几海里,想逃都逃不出人家的手心。海里的渔政,可不像孙子跃这样的岸边的渔政,说不定碰上辽东湾沿岸哪个市的,说情都没处找人,不罚你个骨肉酸麻,决不罢休。所以冯大岸必须远离危险的海域,去往黄渤海交界的区域。
除了躲避渔政,更重要的是,这几年渔民像抢东西一样,从辽东湾里抢海货,鱼虾蟹贝越来越稀少了。可这些海货却越来越成为关内外人的抢手货,还有日本人,偏偏喜欢辽东湾的海货,说这里的海货肉嫩味鲜,营养丰富,不像冷水里的海货那么瘦,也不像温热带海域的那样懈,比北海道的鱼虾还要好吃。于是,订单雪片一样飞向各个海港码头,海货的价格也潮水一般往上涨。沿岸渔村里的渔船立马多了,泊在海里多得像村庄里的房子。还有网具,大车小辆成天往渔村里拉,哪怕最小的渔村,鱼网连结在一起,抻直了也能绕地球一圈。所以,海里不再有龙兵过了,鱼汛也成了过去的事情。渔民们把眼睛盯在外围海域,盯在公海,那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老滩村的渔船,还没达到随便到黄海、公海走一趟的能力,他们的渔船还没有卫星导航,也没有雷达显示。对于一贯盯着岸边撒网打鱼的老滩村渔民来说,到黄渤海交界处,简直是件远在天边的事情。冯大岸的渔船当然也没有这些导航设备,他敢去,那是相信自己的技术,郑和下西洋有卫导吗?不也照样去了吗?只要有指北针,冯大岸敢把船开到天边去。冯大岸会画海画,会测算风速、海流,无论走到哪儿,都能知道自己这条船的经纬度,所以,他不会迷航。
董航不无担心地说,离岸太远了,该停下撒网了。
冯大岸淡然一笑,他知道船下面的海水很干净,干净得连小虾米都没有,网不能白下到海里。
渔船继续单调地前行,二憨忍受不住寂寞,躺进睡舱,打起了呼噜。
董航回到底舱,忍受着轰鸣作响的噪音,看护着发动机。
冯大岸独自驾驶着渔船,孤独地驶向大海的深处。
夜幕从海平线上渐渐升起,模糊了本来就很含糊的海天分界,慢慢地整个天空也属于夜的王国了。凉风习习而动,海里的鱼虾再也耐不住了,跳跃出水面,打出了啪啪的水声。
渔船终于减速了,冯大岸把舵盘固定住,来到船舷旁,和董航、二憨一块顺着卷扬机往海里顺渔网。
撒罢渔网,渔船终于停下了,孤零零地飘泊在大海的中间,四周没有一点渔火。也听不到习以为常的马达声,满天的繁星却格外的明亮,粒粒都是那样饱满,都在炫耀自己的光芒。
大海静谧,波浪舒缓,三个人都累了,像回到婴儿时的摇车里一样,安静地睡去。睡梦中,他们都看到了鱼虾们自投罗网,都看到了堆满甲板的鱼虾在活蹦乱跳着。
然而,谁也没有梦到,太阳再一次蹦出海面,他们会遇到一件大麻烦。
21
早晨,又是出奇的好天气,幽蓝的天幕上亮着几枚大星,东方的鱼肚白越来越亮,猛然间,红红大日倏地一下子钻出海面,依依不舍地与海水牵连几番,便一跃而起,满海便被滋润成鲜淋淋的红色了。升起的太阳立刻变得炽黄,不遗余力地收敛满海的血红之色,不多久,万丈光芒把一道波光四溢的金桥从天边铺到船头。
照耀着我们的太阳,每天都是这样在痛苦中诞生。
没有风,没有浪,四周更没有渔船,陪伴着渔船的只有昨夜撒下去的那一溜网浮子,有些网浮子沉到水中一尺多深。不用看网,冯大岸清楚地知道,这又是一个好潮,起码能有几千斤的好收成。
冯大岸站在船头,迎着红红大日,憋足了劲儿,吆喝出一嗓子:
起网了——
董航奔跑着,钻进机舱,去发动机器。二憨早就蹽到卷扬机旁,摆好了架势,憋足了力气,只等马达声起,开动卷扬,把坠满鱼虾的网扯上船来。
冯大岸候在舵盘前,等待马达的声音,他好倒船起锚,起网收鱼,满载而归。
本来,这该是他们十分顺畅的航行,轻风微浪,鱼虾满舱。可是,他们期待的马达声却久久没有响起。等待在不断地延长,长得让人不耐烦。发动机器,不过是屁崩的工夫,董航下去了这么久,咋还没有一点动静呢?
二憨忍不住了,要下去瞅瞅。冯大岸阻止住了,董航没上来,肯定遇到了什么问题,二憨缺心少肺的,船上的人本来就少,冒冒失失地扎进机械舱,出了事情可不得了。他要亲自下去瞅一瞅,到底是咋回事儿。
机械舱里,一团漆黑,冯大岸的手摸索到了开关,点了下,没有点亮舱里的灯。他的脚踩着舷梯,向里面问着,怎么了?
董航没有回话,冯大岸心里打起了鼓,追问一句,怎么了?
下面传回董航的声音,忙呢。
冯大岸这才咽下提上嗓子眼的心,慢慢地往下摸索,拐过一道弯,他才看到董航的腋下夹着手电筒,两手正在鼓捣着那些线路。直到近在咫尺,冯大岸才看到,董航的衣服被汗水浸透了,额头上的汗,雨一样往下滚,两手只在颤抖不止。
董航抬头看一眼冯大岸,说,坏菜了,电瓶里的电漏光了,柴油机打不着火了。
冯大岸说,再试几下。
董航说,我试过无数次了,线头都拆下来了,咋碰也碰不出火花。
冯大岸接过了线头,往蓄电瓶上触碰着,可不管怎么碰,一点儿反应也没有。冯大岸的脸白了,以前,底舱下面准会有块备用的电瓶,下达禁海令的时候,让渔政给搬走了,这次偷着出潮,竟然忘了从家里补充上来一块。电跑光了,谁也没办法,不像机械故障,有修复的机会。冯大岸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知道,在舱底呆多久,也是无用功,还是到上面,寻找过往的渔船,请求救援吧。这样想着,冯大岸就牵着董航油腻腻的手,爬出底舱。
大海还是那样静,除了太阳是炽白的,渔船被包裹在满世界的蓝色里,就连叼鱼郎都嫌这里太遥远,不肯把白色赐予给他们。
没有电,对讲机也成了摆设,他们和这个世界失去了联系。三个人背靠背地坐在驾驶舱的顶上,分别凝望着不同的方向,他们企盼着能有船的影子闯进他们的视野。
然而,这是个禁渔的日子,船又驶出了平时捕鱼的海区,到了渤海的尽头,黄海的边缘,不是远洋的铁壳大船,谁肯跑得这么远?于是,他们只剩下望洋兴叹了。
天海连连,一片尉蓝,空中,干净得一片云都找不到。现在,他们的眼睛能把云丝拉出救命的线,可是晴朗的天空,残酷得连希望都不给他们。还有头顶上的日头,也在趁火打劫,毒辣辣地照射,逼迫他们去喝存量并不多了的淡水。
白天,就在他们望眼欲穿中结束了。夜晚,冯大岸把那只手电筒蒙上一块红布,高高地绑在了船顶。那是求救的信号,让夜行船早早地注意他们,赶来解救。只需一块小小的电瓶,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了,他们照样满载而归。
然而,手电筒的电池耗尽了,也没引来一只船,甚至连只飞虫都没吸引来。夜黑得恐怖,满天的星星都成了招魂的鬼眼,若不是海浪推着渔船,世界真的静得死去了一样。三个人彻夜未眠,睁圆眼睛,盯着是否有渔火。有一次,二憨的眼睛猛然发现几盏灯从远方快速地移来,他们低沉的心境顿时迸发出万丈光芒,高呼着快来救他们。然而,几盏远方的灯越走越高,直需仰头才见,随后便有隐隐的轰鸣声,他们这才知道,那是架途经这片海域的飞机。他们的心情从极度的高亢一下子跌落入谷底。董航还埋怨了一句二憨,瞎吵吵啥呀,狗咬肥皂泡,白欢喜了。
太阳再一次把老天和大海染得血一样的红,三个人睁着血一样的眼睛,仍在四处观望。他们的眼睛开始出现海市蜃楼般的渔船,欢喜过后,揉揉眼睛,一切都消失了,真正的船只从没扑入他们的视野。太阳在升高,也在散布它的火热,三个人的情绪也被这火热点燃了。船上最后一口淡水被二憨一饮而尽,董航举起拳头,砸向了二憨的脸。二憨还手了,浑身力气的二憨,揍扁董航是不成问题的。
刚才,二憨那一口痛快的水,让冯大岸也感到了不舒服,茫茫的大海,上哪儿找淡水呀,头顶的大太阳,每时每刻都在攫取他们身上的水分,冯大岸也是焦虑呀,心就差被太阳烤爆了,可他必须忍住,船上他是主心骨,他若是崩溃了,他们是真的活不成了。
冯大岸拉起了二憨,怒吼道,不就是水吗,这么大的海,还缺你们喝的水。
董航吼道,海里是咸水,能喝吗!
冯大岸压住了火气,他说,等一会儿,我就让你们喝上淡水。
走进船上的厨房,拿过一只橡胶水罐,拴好绳子,冯大岸走到船舷,把水罐抛到海里,提上了一罐海水。然后,冯大岸又回到厨房,把海水倒入锅中,将锅歪出一个倾斜角,盖上锅盖,又把一只铁勺塞进锅里,在锅盖的最低点上,支撑出一个小缝,小缝的底下,放着一只铁碗,他便点燃液化汽。没过多久,锅里的海水开了,水蒸气凝结的水珠,顺着锅盖,一滴接一滴地滴入铁碗里。
没等水聚成半碗,董航已经等不及了,端起来就喝光了。那水虽说略微有点咸味儿,毕竟是淡水了。船上吃的不用愁,都在网上坠着呢,想吃啥,伸手就成了。可没有水,却能把他们活生生的渴死,是液化气帮了他们的大忙。
每逢锅底结上厚厚的盐碱,他们便将罐里的海水倒进去,洗净盐碱,重新注入海水,再煮出水蒸气。尽管船上只有三个人,冯大岸也觉得,必须立下严格的秩序,否则,他们会熬不到获救的时刻,就精神崩溃了,在船上自相残杀而死。这在渔村的历史上,有过多次先例了,甚至援救的渔船赶到时,他们身上的血还没凝固。他们必须尽最大的可能,延长生存时间。
冯大岸严格规定,每个人只准在锅前守一时辰,喝有限的那几滴淡水,多一秒钟也不可以。
第二个白天,就这样过去了,第二个夜晚也这样过去了,他们所有等待的结果,依然是等待。不同的是,第二个夜晚,他们轮番睡了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