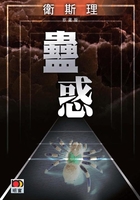卖鲜这行当,化妆打扮有一套。买户偏认这样的办法。掀开鱼的鳃盖,看鱼的鳃丝,这个部位是鱼无数的毛细血管组成,形成一瓣一瓣的鳃丝,是鱼气体呼吸交换的地方。如果是活的鱼,这里边的鳃丝,必鲜艳红润,刚死的鱼,这里边的鳃丝,外表浸暗红色,你用手轻轻一戳,里面流出的是鲜红的血;如果里面流出的是暗红凝固的血块状,这些都是鲜度极高的鱼。有些鱼,不鲜了,这里的鳃丝,会变黑色,且会发出烂臭变质的气味。有些行贩,鱼不鲜了,将邻摊的黄鳝血,用手指头添进去,买户来问价,他回价。买户说鲜不鲜。人家早已等他问这句话,他忙拿起鱼,掀开鳃盖,给你看,说:鳃丝血红血红,你说鲜不鲜。人家一看意会鲜,马上说:秤来秤来。行贩还想赢话儿,说:包鲜包鲜。作为买户,十个九个会上当。
道贵,在我们的行贩话里,属于一个数:6。在我家乡人的眼里,6是看作最美好的数,称它为顺。
说到变质,光一个诨号,就叫你炸眼。那是一次打风过后去进货,才知道。一般有大风(行贩称有风)时,有船会停在沈家门。隔二三天,再运来,那船里的鱼虾蟹的鲜度,可想而知。那次,我同光头、老五、胖子、小牌都在松门,且他们是早一天来到松门,因为没货,住在那里,等。
那天,我货在七点钟前,已经卖光了。准备乘面包车,早一点赶到松门。临起身时,车关的仙志打来电话,说鲜美皮有百来斤,要不要。我一口说要。他说:货是沈家门运回来的,质量不怎么样。我说:现在没货,不管什么货,都要。他说:那你几时递来。我最怕他说这句话,他开口说:递来,人怎样可以用“递”字。把我当作三岁小孩?温岭的这个字,真叫人不可思议。难道改不了的吗?我只好说:八点半钟赶到,你把货,不用拿到市场里,免得缴重钿(即:管理费先生钿)。
我赶到松门水产批发市场,八点二十分。仙志在冰冻带鱼店前等。我赶到,他过来,说:“闹骚,我货一下来,问的人,多得很。”这我知道,为什么我叫他卸外面的道理。现在没货,谁不想要。我说:“货多少?”“这我不准,好几个人买来。”我说:“给我什么价?”“你讲来。”“子头大不大?”“子头当然大,单拖货。”“单拖货,质量差点。”“人家好几个人出我道贵北,我不卖。我说给闹骚格。”我知道,他有虚。但现在没货,只要有货,就赚钿,比平时更容易。我不能还得太低。我说:“老价钿。”他说:“老价钿?多少?”次数多了,照那次。我说;“北门街。”“北门街?今日照这样的价钿,我那班伙计不说格。”“那我加二角,齐头。”“道贵?!闹骚,你拿去卖得转,再加点。”我知道,人家顶多出得这样的价。却不过我约了人家。如果我今天加,下一次人家以为你出得起,还要你加。我说:“这样的质量,我顶多拿去,添摊凑数。”“那算噢算噢。”“如果下次你自己一个人的货,价钿稍微高一点。”我许愿。
我们在带鱼店秤好,他帮我一起冰好。帐算好后,我说:“过二天有货,全部给我。”“闹骚,到海里去摸啊。过二天绝对没货,这货是船避在沈家门运回来的。”“几时有货,你给我,打我手机。”
他走了。我走到市场里转了一圈,除了市场里的行贩,捉货捉进的大鲳、大带鱼拿出来卖,其它几乎烂散货、空壳蟹。往日没人要的东西。碰上海门卖鲜美皮的行贩,他说:“闹骚,你的钞票镶金的。叫他货卖给我,他讲不卖,一定卖给闹骚。”我当作随便的样子,说:“你出多少?”“现在没货,不高他不卖。道贵,他说不卖。什么样的货,不卖。”“他早给我打电话,数量告诉了我。他卖了,下次生意不做啊。”“卖给你多少?”“道贵北。”我当然说贵一点,下次他不会打他的主意。“贵蛮贵。”“不贵他会卖给你。”“闹骚,你坐吃噢。”“钞票赚不来。”“独卖赚不来?”“赚不来!所以没人卖。赚得来,早已满街摊。”“老格。”
生意人碰上生意人,说了实话,人家反而不相信。生意场上有句老话: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就是这道理。
我赶车,11点20分,时间还早。我坐在带鱼店里,边下象棋,边看外面有没有货运进的车辆。货有运进来时,大伙儿作鸟兽散。我跟着到市场看看。在路上,碰上光头、老五、胖子。我说:“光头,你们乘9点半的车?”“昨夜宿在松门。”“货有买起?”“没有。”小牌不知从什么地方钻出来,老五走过去,在他的肩膀上,熏了熏,说:“小牌,到哪里去柯鸡去噢?”“胡说。”“我胡说,叫闹骚熏熏,你身上化妆品香特浓格。”我没过去,人家自己说:“我家里走出,花露水洒噢格。”我不熏,也知道,小牌柯鸡无疑。哪有卖鲜的人,用花露水洒了出门的。何况是男人。小牌老婆的肚子,弹出来,有好几个月了,恐怕要生了。小牌这么年轻,长期没性生活,是不可能的了。还有小牌的身上,不是花露水的气味。他想说谎,却说错了化妆品的种类,让人一熏就暴露。
记得上几天,光头、胖子一起乘8点半的车,说到小牌吹牛,一天赚二三百元,现在赚了好几万元。我说:“他生意蛮好,几万元有可能。”胖子说:“要得得格。闹骚。卖饭店快餐店,赚多少一斤,你晓得格,利润这么薄不说,货要多少卖出。进来的货有多少。”光头说:“柯鸡啦蛮好。隔壁有间美容院,他去剃头,钞票带着六十元。洗头时说好,一百二十元一炮。放在加二层。他吹牛说玩了个把钟头。把那个鸡弄得贼贼叫,要钞票减半。人家鸡不同意。他把所有的袋子翻个底朝天。瞪着眼睛说:都给你了还要我命怎样。”胖子说:“赖鸡钿,说出来牌子倒死。”光头说:“其实,那个鸡陆拾元有了。”胖子说:“六十元有了,应该开头说好,赖总说不过去。比如我们做生意,好卖多卖点。人家来买,说好街头,算帐时人家说大西有了,你有肯吗?”光头说:“钞票几万元赚来,铜钿没到家里不说,投摊还要向人借。”胖子说:“柯鸡馋了,做生意无心。有一次,他自己接来一张假钞票,他去柯鸡,付给了鸡,倒找伍拾元,还在市场里吹牛皮,有几个人说他好的。”
我们一起走进市场。光头说:“闹骚,你货买好。”“买有买好,有想买点凑数。”“等一下,我有买来,跟你并车开嗬。”
“光头今日格急。”胖子接着说:“闹骚,电话打给车关问一下,船还有没有?”“先前卖给我的那个行贩说:船是没有了,别地方我不知道。”“别地方还有船格?!没了,早点回去,晚头到海门去看看。”我们转了一圈,光头在买蟹,这个行贩,人家都叫他子清儿,去年一段时间,长卖鲜美皮,好几次给我打电话,放好。那时我只有BP机。一次没货,我乘车回路桥。在乘到箬横时,他打我BP机。打了不知几只,是车关的号码。我知道他打来。没法子,乘到路桥回他的电话。人家接电话的小姐,说:“打BP机的人,早开噢。”我刚烧饭,我的BP机响了。是松门的号码。我回电,他说:“闹骚,我不知打几只BP机,你不回电。”我说:“我以为你没货,回来的车上,接到你的BP机,我没法子,到路桥回你的电话,人家说你早开噢。”他说:“闹骚,鲜美皮有二三百斤,要不要?”我说:“要!你给我放在打冰的地方,我三点多钟,赶到。”“价格蛮贵。”我知道,好几天没了货源,贵是肯定的了。松门的价格,是随着货源的多少来决定价格的。上下日差百分之三、四十,经常。且货不一定比便宜时的好。这主要没货时,进来的货,在船上的时间长,货就不一定新鲜。我乘回那辆车,二点钟的车班,赶回去。他们三四个伙计,在那里等。我赶到一看,鲜美皮的子头拎过了的,粗的已经没了。对于我来说,卖快餐店是比较适宜。我问:“什么价?”他的伙计说:“六元半。”我知道,伙计开口,他们做好上下拍。但我没货,必要。我说:“这么贵。”他的伙计说:“什么时候。货买不到,人家都抬价,还要抢。”这我知道,但也没这个价。我说:“你的货,粗的已经拎噢,要这样的价,我吃不下。”这是托词。拿去当然赚,且比平时赚得多。子清儿终于开口了,说:“闹骚,让我讲句,北门街,好用不好用。”我想,人家开口了,不跟人家讨价,人家意会你赚得不得了,改日想他少给你,是不可能的了。我就说:“二北。让我拿去也赚点。”子清儿也同意了,爽快。就秤了。开始一起冰,原来,下面还有许多烂货、竹叶。我说:“这样的货,卖给我二北?”我拎起一条竹叶。子清儿说:“这个货不是我放的,等一下钞票少点。”我知道,少点,是少不了多少。我说:“你们不讲信用,这样的货,也放进去。且不是一条二条。”他的伙计说:“不这样的货放得,给你二北。你意会人家是傻瓜。”你说不是傻瓜,那我是冤大头不成。虽然,保证赚得多。但不能让他们这种作假的方式,强加给我。我说:“那你拎了,给我多少一斤?”他不语。我接着说:“你拎了,我给你道贵北,总说得过去。”子清儿说:“闹骚,等一下少二元多点,总可以。”我知道,他们退步了,我不趁机追击,是少不了多的。我说:“老实拎了,差价北门不值。”我说得多一点,人家算账的时候,总有更多的退步余地。按理这样的货,北门给他是到顶的价。算帐的时候,人家子清儿说少五十元。我想这样比起北门的价,我吃亏了点。我付钱时,说:“既然你说了,那算了,我吃亏一点,没关系。零票拾多元也算了。”他说:“你闹骚说来算数。”我说:“下次这样夹进的货,我不要。如果你货好的话,价格贵点,没关系。”“下次保证不会。”
子清儿卖了几次鲜美皮,虽有我为他作后盾,大旺时,他还是买不过人家。车关的行贩,几乎成了专业化。买什么样的货,卖什么样的货,都有上下连接。购得进,销得出。虽有人为他销,但人家卖给他的是,不说贵,给你不能拎,你就没法赚钿。真正赚钿的,是先拎粗的,统价。后去杀人家的烂货、竹叶。虽然,竹叶、烂货数量不及十分之一,光差价,就差好几倍。那是净赚的钞票。有时货多了,人家就赚这样的钱,卖给人家。你没有这样的差价,有时会亏。子清儿卖了几次,回转到他们的老本行,专卖蟹。这不,今天,他的蟹就有八九盘,光头有时便宜,也买。贵了不卖。光头专卖小带鱼,单位开饭菜、快餐店为主。今日小带鱼,都是前几天的货,质量差不说,价格又贵,光头想夜里到海门买。一般小带鱼海门比松门便宜。只怕海门货不多,光头觉得蟹不贵,先买点蟹来。光头在讨价还价。外面有货运进来,有行贩迅速地攀上车厢,有的抓住车厢外的钢管,脚踏在铁板口上,瞧。车子照样慢慢地驶进通道。有行贩下来,买的行贩,如我,碰上老生意的行贩,就问:“大头,有鲜美皮吗?”有些买斧头鱼、金丝鱼的行贩,就问:“斧头鱼、金丝鱼有吗?”总之,各人问各人要的货。行贩边回话,边卸货。有说有,没有人家就走人。货卸在地上,有行贩忙伸手撬,卸货的行,就冲撬的人,吼:“不要撬。”有行贩说;“我向你买。”有的行贩,来格开大价,让你走人。有的行贩,又吼:“现在不卖,货没卸完。”那天,没有鲜美皮。我转到子清儿摆货的地方,只见他剩花蟹了。我知道,那些白蟹,一定卖给光头了。我问:“你蟹卖给光头多少一斤?”“那个光头?”“就是早先同我一起来的那个——光头。”“噢!便讲垃圾桶。”我听呆了。说:“你叫他垃圾桶?”“他专买垃圾货,我们就叫他垃圾桶。”我知道光头买好,在冰。去看。光头刚好冰了两盘,第三盘的蟹,全臭了。打冰的老板,说:“这样冰下去,不臭格。”我想,那怎样办?打冰的老板接着说:“先用冰水洗干净。”光头也可能碰上第一次。那时快到禁鱼期。天气很热。光头边打井水,边叫打冰,倒进泡沫箱里,用手搅了几下子。冰化了,开始洗。我说:“光头,这样的货,也放在那里卖,把人吃拉肚,生病噢,你是罪魁祸首。”老板说;“这样洗噢,再放在泡沫箱里,用冰水浸了,保证没气味。”我说:“光头,这箱蟹,白送的吗?”“白送是白送,有好点洗转来,冰水打打过,吃肯定没关系。”光头在洗,在拎,有的实在差劲,拿起来,蟹钳倒转的有,蟹钳急在落的也有。肚里的肉,化成了水,流出来,有米粒一样大的肉,臭得我站在老远,都急忙掩着鼻子。这样的蟹,光头也好像舍不得的样子。但怕把整箱蟹,弄臭,还是扔了。这箱蟹,冰好后,光地上扔了起码有半盘,茅坑苍蝇飞来多得很。光头整理到盘里,倒进垃圾箱里。地上流过的地方,臭气喷天。光头忙打井水,冲洗。那时候,我不常乘十一点二十分的车,光头说包车,就讨小四轮。光头在小四轮的停车场,转了一圈。我知道,光头寻长乘的小四轮,价钿不用讨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