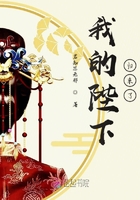我一定要回一次家,因为我的心中积聚了太多的寒冷,自从柳蒲穿走了我的大衣,我的胳膊似乎留下了永久的伤残,胳膊一直感觉到冷,浸入骨髓,就是在炎热的天气里也不例外。我感到我也需要调养,像姐姐一样安静地躺着,等母亲喂我们甘甜的水果罐头。现在,这种罐头是没有了,我们还是喜欢把水果切成小块,用糖水一泡,一进口就是糯糯的甜。还有,用不锈钢的勺子舀着颜色鲜艳的水果,勺子碰在碗的边沿,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清脆,恍然如梦,就像我七岁那年。
我确信那年见到了父亲,他坐在我床边,总是给我一个侧脸。他穿着一件旧旧的绿军装,绿色很朴质,边子泛着白,是荷叶边上那一层亮的白色。他久久地不转过头,他在望窗外的一棵绿白杨。白杨上有一个鸟窝,我不用看就知道。那里以前住着一窝喜鹊,不知怎么换成了杜鹃。杜鹃在叫着“鹧咕咕,鹧咕咕”。父亲的一只手放在我的头发上,我仔细凝望过那只手,白皙、修长,指甲圆润而洁净,绝对不是我和我姐姐赵梨梨共同的父亲赵大山的那只手。他轻柔抚摸我的头发和透过头发的脸庞,使我在以后的很多年里,渴望有人轻轻抚过我的脸。
我的父亲成悟成啊他并不知道,他并不能明白这样一个七岁的在重病中的小女孩对他的感情。他可能是焦急的,急急地赶过几十里路坐在我的床边。医生告诉他我患的是脑炎,已脱离危险了,只是不知道会不会留下后遗症。他坐在床边,他望着绿白杨,白杨上的喜鹊窝被杜鹃占去了。他还有三个孩子,他们都很健康,生活在他的身边,惟独一个我,这时候病了,需要他忘记一切身份前来看望。他来了,虽然这是他与另一个并不合法的妻子生养的孩子,却是他的骨血,他要把她带到最好的医院。
因为我的病,成悟成和母亲的关系彻底暴露了,母亲说,她无所谓,只要孩子好一切都好。成悟成说,他也无所谓,这些年他欠我们的太多了,他的生命都是母亲给的,他还剩下什么?他们相视微笑,热烈地拥抱着。
很多年前的那个冬天,我的母亲还是一个燃烧着红头绳火苗的小丫头,她冲进自己家的小院门,找到了她救下的年轻英俊的保皇派“司令”。“司令”并站在伟大领袖的画像前,让我的母亲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火光暧昧而温暖,使我的母亲鼓起勇气,伸手去摸了一下“司令”的眼睛。那眼睛微微眨动,柔软的睫毛摩挲着母亲的指尖,像抚摸一只小猫的眼睛,他微微闭了闭。我的母亲吓坏了,伸着一只手站着,身体前倾,脸上的表情是那样生动而无辜。
成悟成紧紧把我母亲拥抱进怀中,也许有点快,可是经历了生命的考验,激烈之情,犹如滔滔江海。
这是我母亲第一次被人抱和被人吻,她有些被动,僵立着,一些手使她柔软。手不断地出现在她身体的各个部位,令她迷惑,百思不得其解。然而,她不需要解,她只感觉自己不断变软不断变软,溜在地上去坐着,仰着头。
成悟成坐在矮凳子上,他可以看见微微地泛着青蓝的天。天空已经全黑,可是从没有开灯的房子里望出去,依旧有一些青蓝,如果出现黑色的影子,那就是活动的人。但是他全然没有注意这些,他只感觉到他怀里的物体无限柔软,发出一股青涩的,像绿草那样的气息,使他不断地想去靠近。
当赵大山冲开门时,他还看见这一对男女就那样拥抱着,他赵大山幻想了无数个晚上,如今付之现实,怎么着也有点不对,好长时间,他才明白不对在出现了另一个男人,不是他,肯定不是,他的胳膊手都长在他身上呢。他咳嗽了一声,他背转身去不看他们,他等待他们分开。
成悟成放开拥抱我母亲的手,他在凳子上坐直,他也咳嗽了一声。我的母亲,她还坐在地上,她直楞着眼睛,呆呆地看着赵大山。赵大山突然端起了对面的一只长凳,劈头向成悟成砸去。他说:我打你。
我的母亲身手极为矫健,她一扬身扑上去,抱住了成悟成。赵大山一惊,凳子砸歪了,一条凳子腿斜斜地擦过我母亲的手腕,一条深色的血印子缓缓地流下来。两个男人同时惊呼了,去抓那只受伤的手。成悟成抓住了,赵大山没有。成悟成把我母亲的手放在自己唇边,眼睛一动不动的望着赵大山。赵大山等他们解释,等他们说话,然而没有,赵大山气急败坏,他指着成悟成说:你是他们要抓的人?成悟成说:你想说什么?赵大山说:放开我的女人!成悟成放开了拉住我母亲的手。
我母亲站起来,她与赵大山面对面,她说:谁是你的女人?你做梦!赵大山不知道说什么,他绞着自己的手。我的母亲重新低下头,她温柔地俯视着成悟成,她低声说:你有没有吃饭?
天,她竟然这样温柔的问那样一个男人,赵大山很受不了,他大叫着:不!你们休想,我要去告诉造反派,我要他们把你们全都抓起来!
我母亲轻蔑地看了赵大山一眼,赵大山晃晃自己的手臂:你以为我不敢?
我母亲又温柔地转过头,又温柔地对成悟成说:你先走吧,我等你。在明亮的火光里,她的眼泪温暖晶莹,像苹果上的凝露缓缓坠落。
成悟成他忍不住,他又抱住了我的母亲,他说:跟我一起走吧,只是我会让你受苦。
赵大山觉得很刺激,他不能明白什么人就像在跟他演戏。蓦然,他明白这样很危险,他还明白了他有一个机会。他微微地笑了,眦着牙对成悟成说:你跑不了,你要是跑了,我就叫人把素芬抓去,你们一起走了,素芬还有父母。除非,你把素芬还给我,我就会守口如瓶。
我母亲说:赵大山你无耻!
成悟成说:一切跟素芬无关,我自去投案自首。我母亲一把抱住他:不!我不让你走,你走到哪里去,去哪里还不是危险。
我母亲说着,一转身给赵大山跪下了,她说:放过我们。赵大山背转身去不看她,赵大山说:跟我好吧,我会对你好的,你跟他这个反动派有什么前途?
整个夜晚他们都在商议,这是一场奇怪的战争,我的母亲为了保护一个人,需要第二次献出勇气,完成女人的命运。成悟成不能同意,他不让我的母亲做出牺牲,但是他本身,已经成了赵大山要挟我母亲的筹码,他没有发言的权利。
最后,如果我的母亲不能答应赵大山的要求,成悟成就会被再次抓去,而我母亲也脱不了干系。母亲为了爱他,放弃了自己。
第二年的春天,我的母亲成了赵大山的新娘,有了我的姐姐赵梨梨,两年以后,文革平息,成悟成成为了一个大官,他把我母亲接到城里,有了一份体面的工作,妇女主任。而赵大山当然明白这种变化,他随母亲来到小城,在一个厂里烧锅炉。
母亲本来一直在他的庇荫下生活,直到赵大山终于觉醒,没有爱的婚姻是没有味道的南瓜。母亲有了一个我,是那样地和成悟成眉眼酷似。本来,他也可以容忍,可是母亲从此不让他近身。他像野狼一样嗷叫,他不知道,他分明赢了怎么会输了。他把凳子,桌子无数次扳倒,把菜刀扔下,但是没有用,我的母亲坚韧,她不再让他靠近,任凭手臂和身体伤痕累累,我和姐姐梨梨亲眼看到。
这时候,赵大山已经有了一些思想,他的暴躁也磨得圆润,他和另一个在水房工作的女工逐渐有了感情。他和母亲离了婚,和那个女人一起被调往了另一个城市,从此与我们音容淡远。那女人一定给他生了儿子,从此他也不再回来看我的姐姐赵梨梨。
我的母亲终于安静,却是太安静了,她才二十七岁。
我想到母亲二十七岁的时候,也常常想到柳蒲也已经二十七岁。不同的年代她们的经历多么不同。
我喜欢躺在明亮的椅子上晒阳光,我和母亲的小屋有一个小阳台,阳台上栽着小葡萄架,在春末的时候,会结出碧绿的小果子,一串一串,印在我的书上。也印在姐姐睡在阳台上的脸庞上。天气已经有些懊热了,只是葡萄叶子太浓密,我们又根本不运动,还坐得住。阳光从树叶中漏下来,便是碧绿的,我喜欢。我还喜欢让母亲把新鲜产下的杏子,用糖水泡一泡,盛在洁白的碗里。勺子也是洁白的,果肉的边微微荡漾。杏子啊!我最喜欢的水果。就像我七岁的那年。当然有一些变化,白杨树变成了葡萄藤,只能让我们低着头感觉关怀,盛在自己的小空间里,缩着身子。就好像冬天躲在一间茅草棚里烤火,虽是温暖着,也是权宜之计。
我喜欢这种权宜,在这年春末夏初的时候,我回到了母亲身边,请她给我的胳膊疗伤。母亲带我去看了一个老中医,母亲说,她生养我之后就得了妇女病,总是淋淋沥沥地出血,就是这位大夫看好的,他简直就是一位神仙,母亲说我有多少岁,就认识这位大夫多少年。
我的胳膊总也不好,母亲说:你一定是心不诚,我的病人家药到病除。我说你那是什么病,是常见病。母亲说:你小孩子懂什么。我说:我怎么不懂,王熙凤就得的这个病。说出来,我很惊异自己的机智,其实是我在C市时,一位小姐引了孩子,总也淋沥不止,月经失调,成为我们大家的怕处。
后来老中医建议我们用火罐治疗,他说是中了内毒,风寒当道,病毒乘机而入。火罐拔在手臂上,发出“扑扑”的声音。当取下来时。我的胳膊呈现着一团又一团的黑污。我很惊异,我的身体里怎么会有这些?
好像我人生的污点。然而,现在的这种日子是多么平静啊!太阳每天都自东向西,母亲每天都在我身边,我的姐姐经常能够神志清醒,跟我谈论一些毫不相干的轻松话题。而现在,我的名字又变成了尹小桃,有着尹小桃应该有的生活,她似乎与那个叫梅兰的女人分属两个世界,只有太阳下山的时候,这个我非常敏感的工作时间,我又会想起我作为梅兰的这档子事。这些,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用梅兰的付出支撑着。当我的姐姐有一天神志清醒地质问我时,反而更加坚定了我作为梅兰的决心。
那天,我们在阳台上说着话,姐姐突然像不认识我似的看着我。她说:小桃,怎么回事?难道你不需要在上海上班吗?她又突然像恍然大悟似地说:你一定是因为我做了什么错事吧!天哪!你不可以那么傻,是不是为了给我治病,你也从公司拿了钱?你这个傻女孩,傻女孩!都是我不好,我该死我该死!姐姐着急地一连串打着自己的脸。我急了,连忙劝阻她,拉住她,但她就像惯性作用一样,拼命而用力地抽打自己的脸。我该死我该死,你不能去,我亲爱的妹妹,你不能去!有一瞬间,我甚至都怀疑她什么都知道了,但是她持续而坚决地虐待自己,终于让我明白她又犯病了。我亲爱的姐姐,即使在患病的潜意识里,也是那样深刻地热爱着我,我又怎么能不管她,让她永远置身于精神的黑暗中呢?不,我爱她,因为她是我的姐姐,是我生命的一部分。结果就是更加让我痛惜。我要她恢复,我要她快乐,我必须很紧迫,我要马上变成梅兰。
我站在阳台上,我紧紧地抱住姐姐颤栗的身子,感觉自己站成了一棵坚强的树。无论梅兰将遇到什么样的艰险,我愿意。
我又回到了C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