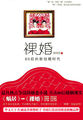这也与小组中的学习有关联。这些小组中的人更坚强,适应性更强,他们能够承受比我们的礼貌制度所暗示的更多的痛苦。毋庸置疑,这将使人们长期获得反对的能力、批评的能力、不同意而又不承担可能会导致灾祸的能力。
好,上述讨论对男人们尤其重要。如果男性在我们的社会中是无实际意义的问题,如果美国的男人总体上是不够雄心勃勃的、不够坚强的、不够果断的,那么,这种敏感性小组训练可以看做是一种男性训练,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在我们的社会中有大量这类男人,他们遇事退让三分,喜欢奉承,他们避开一切争吵、争辩和剧烈冲突,试图缓和每件事情,说话办事圆滑,总是充当和事佬,从不兴风作浪也从不捣乱,当遭到多数人反对时他们会轻易放弃,而不是顽强地坚持和抵制。这是一幅弗洛伊德意义上被阉割的男性的性格图像,他们就像一只摇尾乞怜的小狗,在非难面前只会拍马屁,而不是在必要时冲上去咬一口。
现在我想到了,认真研究弗洛伊德关于敌对行为和破坏的本质、关于死亡愿望的本质的论述,会成为理解这个问题的良好基础。这并不意味着必须将弗洛伊德的全部论述都吞下去,只意味着在探索人类心灵深处的一种训练。
还有一点与这一点有关联,但在管理上有些不同,即我经常想到的统治一从属的整体关系、统治等级制度的权势等级,例如我们在猴子和猩猩身上看到的那些行为(10,9,20)。显然这个变量没有被研究群体动力学的人完全了解,我想我该建议他们读读有关猴子的研究材料等。现在我又嗅到了民主派教条和虔敬的气味,其中人人都是平等的,事实上更强势的人、天生的领导人、统治者、才智非凡的人或英明果断者等被忽视了,因为他们使人人不舒服,好像违背了民主哲学(当然,事实上这并没有违背)。这是群体动力学研究过程一个新的研究变量,应该有意识地感知。在我读过的材料中,没有提到这类数量极多的文献,就像几乎没有提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文献一样。
对迈克尔·默菲的访谈
大多数人了解他,知道他是伊萨兰学院(Esalen Institute)的共同创立人,或者是通过他的畅销书Golf in the Kingdom,The Kingdom of Shivas,The Future of the Body和The Life We Are Given。迈克尔·默菲(Michael Murphy)以与马斯洛相同的方式度过了他的一生:探索人的自我和仔细观察人们如何开发他们的能力。他在默想还没有流行之前就在研究了,并仔细观察精神健康与身体健康之间的关系,默菲的大部分研究已经成为主流。可是,我们与这位美国人的崇拜偶像之间谈话的话题却是他的内心世界。马斯洛称默菲是“我从未有过的孩子……”
两个男人相遇了,这场景可以反映卡尔·荣格的同步性概念。马斯洛和他的妻子伯莎从南加利福尼亚开会回家,驾车经过北加利福尼亚沿海地区,正在寻找旅舍过夜。在小城大瑟尔(Big Sur)的外围,他们注意到一处地方提供住宿,便决定住下来。在登记时,马斯洛要在登记簿上签名。前台的接待员在看了签名后说:“就是亚伯拉罕·马斯洛吗?”接着这位接待员激动地大喊理查德·普赖斯(Richard Price)的名字——他是迈克尔·默菲的伙伴,伊萨兰学院的共同创立人。
他们本想找个旅舍过夜,阿贝与伯莎根本没有想到他们走进了一家作家、演讲家、哲学家、学者和对人本主义哲学有兴趣的治疗师的旅馆。(20世纪)60年代期间,伊萨兰学院主办过由斯金纳(B.F.Skinner)、亚伯拉罕·马斯洛、卡尔·荣格和其他人主持的会议。听众和与会者范围广泛,从普通人到像乔治·哈里森(George Harrison)、琼·贝兹(Joan Baez)、鲍勃·迪伦(Bob Dylan)和艾伦·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那样的名人。激进主观的新闻记者亨特·汤普森(Hunter S.Thompson),当时22岁,是现场的管理者。其余人——如他们所说——都是历史!
迈克尔·默菲和亚伯拉罕·马斯洛的友谊一直持续到马斯洛去世。我们在加利福尼亚圣拉斐尔他的家里见到迈克尔,和他谈论马斯洛和他的研究。我们讨论的话题无所不包,那种正话反说和说隽语的谈话气氛大概也是马斯洛博士所钟意的,我们认为迈克尔·默菲有一堂非常有价值的课要讲给美国的企业听。
之所以要正话反说和说隽语,是因为迈克尔·默菲承认对美国的企业界并不了解,可他又是一个精明和成功的商人。与马斯洛一样,默菲一向拒绝担当领袖角色,可他却成为了人类潜能运动的领袖。马斯洛在动荡的(20世纪)60年代成为文化偶像,可认识他的人却认为他是一个保守者。默菲是伊萨兰学院的领导人——而学院当时是反文化思想的温床。但是,在“夏日之恋”运动期间,默菲一直是一个传统的家伙,而这场运动并不传统。正如他自己所说:“首先,我很早就对幻觉剂严重过敏。其次,非常喜欢山羊绒套衫。最后,我没有大量购买这些技术的热情,我一向怀疑这种尝试。我是一个无外援的爱挑剔的人……”这对任何一位公司领导人来说都是至理名言。
我们注意到对马斯洛的日记的浓厚兴趣又复活了。您怎么看待这件事?
每个人都在探索一些事物。我们有Enreagram,有迈尔斯一布里格斯测试(Meyers Briggs test),有各种领导模型,还有这种或那种的十个步骤。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结构、指导和领导。
人们之所以有极大的兴趣,是因为阿贝极有深度和内涵。他是一个研究者、心理学家、理论家和哲学家。他不喜欢万应药。阿贝的关于自我实现的部分理论,就是讲这种人对被标签化深恶痛绝。日他从来不喜欢看见上述情况。他对兜售领导模型或领导框架之类的问题不感兴趣,他是在真正做研究做学问,他是在研究了人类行为和相互影响的几乎所以方面。从他(20世纪)40年代对人类性行为的研究、对哈里·哈洛(Harry Harlow)的研究、他关于自我实现和人类动机的著作来看,他形成了一套知识体系。
问题是人性毕竟是人性。我们都有自我超越这种能力,把某些人认定为某一类型的人,如INTP型或ENTJ型,是对他们的限制。把你自己或你的同事、团队成员认定是某一类人,是低估了入的创造力,低估了我们重新开始、创造和创造冲动的能力。我们被看做是年轻人,我们被划定为家庭角色,这种事情常发生。我们都有自我实现的潜力,一成不变地看待人是低估了他们。
您非常了解马斯洛,您认为他会对当今的组织潮流说些什么?
他不会喜欢在今天的企业里盛行许多万应药、工具和运动。当一个企业权威来到一家公司时,对他几乎是狂热崇拜。让我们假设你是一个雇员,你希望进步,所以你不得不参加或者接受这个培训。你们必须联合起来!《日常生活的狂热》(Cults of Everyday Life)一书就揭示了所有这类事物的破坏性的一面。
但是,它也有创造性的一面。例如,作为公司强势文化的一部分,有时在公司内部形成狂热崇拜的氛围,也能帮助人们变得更有创造性。它能造成目的共享感。你必须要密切注意这个问题。
我们多么缺乏比喻力
我们的世界是以这种方式建立起来的,就是优秀的思想和优秀的作品几乎完全是逻辑的、结构化的、分析的、书面的、现实的、等等。但是,显然我们需要更有诗情画意、更有想象力、更多比喻、更多荣格所说的原始性……是什么让学术会议、科学期刊、组织采用的思想体系和表达方式不合适或不适当了呢?
——亚伯拉罕·马斯洛
大约10年前,我们参加一个高科技专业人士的大型集会。演讲嘉宾汤姆·彼得斯(Tom Peters)是管理顾问和作家。他开头的几句话至今犹在耳边,甚至今天比10年前更适合。
彼得斯以典型的非正统的方式扫了一眼听众,给我们留下永远难忘的一句话。他说:“现在就是你们这些家伙的问题。几年前我对你们演讲时我扫了一眼听众,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一群人。现在你们大家看上去是一样的,讲一样的语言,穿着一样,住在一样的小湖边,因为你们是‘专业人士’了,现在成功了。”
他的这番话与马斯洛讲过的一段话是一样的。一旦获得一些成功,我们的社会准则就会强迫我们构建我们的思想,整齐划一我们的行为,使我们显得更专业,更有控制力,更像现在的模样。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经常抑制我们的创造力、乐趣、幽默、学习和创新的才华,使其均一化。或者,我们选择保持沉默,因担心遭到排斥而隐瞒我们的贡献。
我们不是提倡不受管理、外行的、松散的组织。我们的主张是全面考察一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失去了(和正在失去些)什么。在寻找损失例子的过程中,我们在亚伯拉罕·马斯洛的日记中找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例。即使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先驱者、我们这个时代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也察觉到了适应社会发展的压力。
1960年,马斯洛要在一个专业人士集会上向其他知名人士发表重要的演讲。他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一直在努力解决他的理论中的一个问题。他说整个经历是高峰体验的典型例子,由于他习惯在纸上思考,他记下了整个经历。他想抛开计划好的演讲,用文字表达那些思想。但他有些犹豫。他写道:
情况就是这样,在忙碌中经历的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高峰体验,它恰好阐明了我想搞明白的几个关键问题。可是,由于它如此不宜公开,如此不依惯例,我发现自己极不情愿当众大声念出来……它不适合我。我意识到这种论文既不“适合”公开发表也不“适合”在会议上宣读,我问自己“为什么”?这些知识分子会议和科学期刊有些什么东西使得某些个人的思想体系和某些表达形式不“合适”或“适合”呢?
在这个“适合”过程中失去的是什么?我们永远不得而知。可是,像马斯洛这样智力发达、富有经验、知识渊博的人,尚且对这个过程沉默不语,我们将来如何能够承受得了组织实际水平的创新和创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