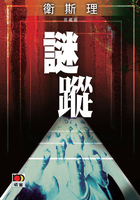现在回想还发生了一些事情。在这些小组中有大量无法做出评价的事情,现在我想起来了,有人认为——我不知道是存心的还是无意的——他们的感情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认为接受他们的意识并口头表达出来是一件好事,认为这并没有赞成还是反对的意思。例如在一次会议上,一个人谈到他对反犹主义反感,当然,这是一种深刻的诚实。他纯朴地承认了他的感觉,并承认需要得到帮助来面对这种感觉。我记得那个小组对此非常感兴趣,他们并没有一开始就争论是应当、应该,还是正确、错误,而是能够接受事实,事实的确如此,然后接受这个事实,而不是说教式地讨论。当然,效果比他们只是进行说教式的讨论好多了,那样的话讨论会变成攻击和反击的攻防战,反犹主义者的态度可能就会更强硬了。
在这个小组里,当领导人要求进一步提供个人偏见的例子并对此作了简短陈述时,他没有暗示任何赞成、辩解或其他什么。一个人也许会说曾做过什么事,他为此感到非常惭愧。然后他们轮流发言,其中的五六个人吞吞吐吐地承认,这在他们的一生中可能是第一次,对妇女、黑人、犹太人、信教的人、不信教的人或其他什么样的人有偏见,每个人都能以不作评价的方式对待这些偏见,就像知道这种有偏见的精神分析学家尽力“接受”所采取的方式是一样的。我认识一个教授,是我的精神分析师朋友的一个病人,两三年来一直在和他想猥亵小女孩的冲动抗争,尽管事实上他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尽管现在清楚了他永远也不会这样做,因为他克服了这种冲动,可事实没有改变——在这个世界上冲动是有的,就像有其他令人不愉快的事情一样,比如蚊子和癌症等。如果我们拒绝癌症患者,拒绝为他们做任何事情,只是因为癌是罪恶的和邪恶的,我们肯定无法攻克癌症。在观察事物和人时要有非常良好的态度,无论一个人是否喜欢它们,是否赞同它们——都要承认有些事情事实上是存在的,即使它是邪恶的,其实这对打算改变精神世界的任何人而言,都是绝对必要的。
现在,我记得它是在我修订爱的定义时想到的,也应该包括进来。我一定指出过爱是不评估的。一般来说,爱与公正、判断、评价、报酬和惩罚、功过必定是不同的,那么在小组治疗中无意识学到的这种不评估,实际上是一种爱的行为,也许还是训练爱和了解爱的感觉的一个方面。当然,我曾碰到过,我想其他人也曾碰到过。在我的治疗经历中,我对他了解越多的人,在向我讲述他对自己的罪孽、对自己干下的卑鄙龌龊的勾当感到多么痛苦时越谦卑,结果是矛盾的,我越发喜欢他而不是相反。在这些小组中也发生过这种情况,他们偶尔坦白出各种卑鄙的事情来,这倒使我更加喜欢他们而不是相反。也许这是因为有不评估、不判断、不惩罚的整体准则的缘故。该准则强调接受而不是拒绝。不能去爱的一种情况是好挑剔、说教、反驳别人,并试图改变、改造、重新塑造他人。当然,这是许多婚姻不幸福的原因,也是许多离婚的原因。有人也许会说,只要他们能够原封不动地接受别人,而且喜欢他们、钟意他们,而不是恼怒、激怒和讨厌他们,人们才会成为好伴侣。
所有这些都与我试图要证明的一个观点有关,即在一个小组里,对于上司和领导人等等,区分两种作用是非常有利的:一方面起判断、惩罚、控制的作用,充当警察或行刑人的角色;另一方面起治疗、帮助和爱的作用。例如,我曾指出过,在校园里治疗师最好不要是教师,因为他们不得不评分,即不得不赞成、反对和惩罚。而且,这个观点可以更充分地加以阐述,例如在芝加哥大学,教师完全不评分,而是由主考委员会来做这件事。这无疑会使学生与教师的关系更密切,教师成为单纯的建议者而不是建议者和对抗者的结合体。在这些T-小组里,教员仅仅是建议者,他们不评分、不奖励、不惩罚,不做任何这类事情,他们只是不加任何评估地接受。
同样,在印第安黑脚族的家庭中也能看到非常良好的关系,惩罚者是部落的老人而不是父母本人。当惩罚者出现时,父母为孩子调停,他们站在孩子一边。他们是孩子的保护者和朋友,而不是孩子的行刑人和惩罚者,所以这些家庭要比美国人的家庭更亲密,在美国人的家庭中,父亲必须既是爱的给予者,又是惩罚者和斥责者。也许这也应该写进治疗小组的目的和目标的陈述中去。
现在我回想起坦南鲍姆在访问非线性公司时我们谈论过这个话题,我们一致同意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观点。我想用这个观点来分析一个企业上司面临的问题,这个上司有权雇佣和解雇,有权提拔和加薪,等等。我要指出的是,对于一个在判断、行刑人等这类位置上的人来说,期望他对人人不存先入之见,期望他对人人信任和友爱,等等,是完全不可能的;除非指定一个不是法官的人,一个对我们没有权力的人。
是的,我想我会详述这个观点的,因为它非常重要,特别是作为所有当代管理政策的评论文章。谈到当代管理政策,我对盲目乐观倾向的模糊感觉再次出现了。这一定是其中一种——认为良好的管理政策、良好的参与管理不管怎样都会使上司和工人组成一个快乐的大家庭,或成为好朋友,等等。从长期来看这完全是有可能的,我甚至怀疑它是值得向往的。我确信在这种情形中友好和开放等的程度都是有限度的。有个事实是不变的,即最好让上司、法官、行刑人、负责雇佣和解雇的人或警察等,不要与他可能不得不惩罚的人关系过于密切和友好。如果惩罚的作用是重要的,它确实也是重要的;如果惩罚是必要的,它确实也经常是必要的,那么友好事实上会使该项工作难以执行,不论是对法官还是对接受惩罚的人。例如,受到惩罚的人会觉得被人出卖了——让他降职的人是他视为朋友的那个人。再例如,一个非常友善的人不会推荐朋友担任总裁,人们会非常难以理解。
反过来,如果上司必须对朋友履行职责,这会使他的日子很难过。事情很可能变得复杂起来,各种内疚的感觉会出现,这是导致胃溃疡的重要病因。最好保持某种程度的不偏不倚和社会距离,就像军队中的官兵关系那样。如我所知,全世界许多人做出过努力使军队民主化,但效果并不理想,因为这个事实没有改变——有人必须下达让另一个人冒被杀、甚至去死的命令。这不可能通过民主的方式做出决定,因为没有人愿意去死。因此,有人必须做出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选择,将军最好是一个孤独、冷漠、没有感情的家伙,不能与任何他可能必须让他们去死或他也许不得不下令将其处决的人保持友好关系。也许对医生来说也是这样,特别是拒绝为其朋友做手术的外科医生,或者对拒绝将其朋友或亲戚当病人的精神科医生来说也是这样。这是非常容易明白的事实,人类很难处置将爱与公正集于一身的同一个人。我知道这与我读过的有关管理政策的作品的看法是对立的,特别是与说不清楚的参与管理是对立的。权力就是权力,甚至大到掌握生杀之权。对这个掌握着我生杀之权的人,我肯定不会像爱我的一个没有权力的亲爱的朋友那样去爱他。
凯(非线性系统公司总裁)在与我讨论这个问题时,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观点,即开放的概念变得有点混乱了。他认为开放有两个不同的含义,我想过这个问题,完全同意这是非常有价值的区分。在上司和参与管理的理念中,开放意指(也应该是指)大量提供给他任何建议、任何事实、任何反馈或信息,不管这些信息是让人高兴的还是让人讨厌的。他对开放的理解应该是这个意义上的,对此毫无问题。他必须得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
但是,在表达、摆脱所有抑制和言语的意义上,我认为对法官、警察、老板、船长和军队的将军而言,开放肯定是不利的,在此类情况下,不将担心外露经常是领导人的责任之一。我想如果我现在一条远洋船上,船长将他的担心、焦虑、不确定和疑惑和盘托出,我下次就不会再搭乘那条船了。我更喜欢他承担起所有的责任,我更喜欢他把自己看做是有能力和能胜任的人。我不想去体验认为他可能是一个不可靠的人、他可能会搞错罗盘方向等等带来的焦虑。这对医生来说也是如此,我不愿意他在给我体检时还在沉思,他在为我检查结核病、癌、心脏病或天晓得的病时,我更喜欢他保守他的怀疑。
这对军队的将军来说也是如此,而且如我所知,对家庭里的父亲和母亲来说也是如此。如果父亲将他的担心、疑虑、焦虑、懦弱等天天讲给妻子和孩子听,他就失去了作为整个家庭顶梁柱作用的一半责任。这对母亲也一样。事实上父亲的部分作用是做一个信心培育者,做一个承担责任、可以依靠的领导者。我一定会向任何男士建议,他应该向他的妻子、孩子和朋友们完全开放,但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他负有领导责任时,他最好保守烦恼,让烦恼消失在他的心中,而不要通过公开表露来缓解忧虑和解除痛苦。
对企业老板也是如此,人类的各种担心、疑虑、沮丧等,他心中肯定也有,但他应该有力地控制和着眼于未来,应该压制、克服或消除所有这些疑虑和担心。他必须保守它们,至少做到在外面而不是在组织内部表达它们。
在教学生涯初期,我当然喜欢我的学生,想与他们打成一片,想成为他们的好朋友。慢慢地我明白了,尽管我可以把面露笑容、友谊等等和分数分开来,尽管我一定会爱每个人,包括并不非常适合读心理学的学生,但他们很少能够接受和理解。通常,我成为学生们的朋友,如果他们成绩不好,他们会认为我背叛了他们,会认为我是一个伪君子,是一个叛徒,等等。当然,并非所有学生都是这样,我发现,意志坚强的学生能拿得起,意识薄弱的学生则不行。慢慢地我不得不放弃了这一观点,一直到现在,特别是大班上课,我会保持一段距离,维持英国式的关系,而不是与他们走得很近和像好朋友一样。我建立密切关系的唯一情况,就是我为此特地给他们进行了预备教育,或向对方解释并预先提醒他们我可能不得不给较差的分数,等等。但以上论述并非期望、希望或建议上司或领导人不要表达开放,尽管我们肯定会建议和期望他在这个意义上学得更加开放,即用他的耳朵和眼睛广泛地接受信息。
概括我对这些治疗小组与个体心理疗法之间关系的感想的一个方法,是回到人人熟悉的结论,即对小组治疗好还是个体治疗好的争论是没有意义的。首先,每种服务都有许多不同类型,而且目的不同、服务对象不同,等等。其次,它们在具体方面有不同作用,因此,有待我们解决的问题就转变成了什么问题、在什么环境下、对什么人、为什么目标、我们应该采用小组治疗还是采用个体治疗、是结合采用还是轮换采用。
另一个总体概括的陈述是这些T-小组显然是成长刺激、人格发展、促进精神作用(与使病人康复的精神疗法截然不同,精神促进使健康人更健康)。这些小组与他们遵守的规则是良好的成长土壤。这里可相比拟的事物是耕作,优秀的农夫播下种子,创造良好的生长环境,在种子生长的大部分时间不用管它们,只有在真正需要时才帮助它们。他不会拔出秧苗看看它生长得是否正常,也不会拨动它,不会修整它,不会把它挖出来再种回去,等等。他只是让它自个儿生长,给它最低限度的必要帮助。毫无疑问,在这个意义上阿罗海德湖的小组环境是良好的生长环境。当然,可以相比拟的也包括优秀的教员或领导人,优秀的领导人像是农夫,更多的不是训练、塑造、加速提高、影响人们,而是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要么为他们提供种子,要么激起他们内心的种子,然后让他们在没有太多干扰的情况下成长。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刚刚想起来的,几乎忘记了,这完全是一个隐私问题。近来读书碰到了五六个问题,当然,在阿罗海德湖我也发现了这些问题,甚至可以说这个欲望和隐私需要的问题几乎完全被这个领域的作家们忽视了。当然,训练小组部分地学会了放弃病理学意义上的隐私,即强制意义上的隐私。这种自然性训练教这些人不公开或自我公开,如同他们自己的愿望。他们大多数人都知道他们所谓的隐私不过是一种担心、强迫、无能、抑制等等。事实上,如果我对自我实现人的研究对此还有一些指导作用,我们也许可以期待人们对非强制的真正隐私、能使人快乐的欲望越多,对神经质隐私、保守无必要和愚蠢的秘密、掩盖一个人的伤疤、试图愚弄人和伪装等的需要越少,他们会越健康。
我对阿罗海德湖这个问题的想法部分地是受了伯莎的启发,她是一个非常隐私的人,她是一个在20人的小组中吐露她对隐私事情的想法会发抖的人。这肯定不是神经质隐私,因为她完全能够向她亲密的朋友吐露心事——仅仅是向他们。当然,许多人有隐私的正常需要,自我选择过程使得他们永远不会出现在阿罗海德湖。他们会觉得将要发生的事情使他们不愉快,他们根本不愿意来这里,即使强迫他们来,我也不知道这对他们有多大作用。他们可能继续保持着警觉,保持着对开放裸体主义的反感,甚至整个小组都接受了他们也不改变。我想我是在说我们必须区分健康的、有利的隐私和神经质的、强迫性的、不能控制的隐私,这是完全不同的隐私。在我们为消除神经质隐私——它实际上是一种抑制,是愚蠢的、无聊的、非理性的、讨厌的、不切实际的,等等——所作的努力中,我们容易忘记欲望隐私的存在,而且我们还容易忘记个体差异。根据我的个人经验,我认为用一个从自我公开者到健康隐私的统一体来测量人是有可能的:一端是更喜欢以自我公开的容易方式隐私的人,另一端是以非神经质方式隐私的人。
我认为,为了证明这个观点,我甚至可以说学会放弃神经质隐私是达到健康隐私水平的先决条件,当然也是能够喜欢隐私和独处(大多数神经质者,甚至大多数普通人是做不到的——当然不是在美国)的先决条件。在这个意义上放弃神经质隐私是走向健康的趋向,但健康本身还包括对隐私、喜爱隐私、有能力隐私等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