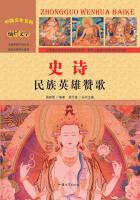为了安全起见,两人决定从不同的火车站走。夏小妹陪哥哥去了永定门火车站,而任燕则护送田源赶往北京火车站。直至火车的车厢缓慢地移动起来,任燕那颗扑通扑通狂跳的心才逐渐地平息。她看见了久久地伸在车厢外面那只摇动的手,又想起了半年前她在遍是花圈的天安门广场上看见的那只摇动的手。那天田源是挥着手臂在朗诵,朗诵的是夏建国临时写就的诗“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那一刻,田源的脸微微扬起,手势幅度很大,额前的头发一颠一颠地,那范儿很是有点像激动的话剧演员。
她那一刻很为田源激动,更为夏建国激动,她很不明白夏建国怎么会出口成章,一下子写出那样铿锵有力的诗句来。而且夏建国那么富有想象力,他把一串闪闪发亮的小瓶子挂在一根竹竿上高高举起来,当时广场上的人们一下子就明白了“小瓶”与“小平”谐音的这个意思,一起大喊“小平,小平”,声若排浪。这个重要的情节,可能也是公安部门向上报告之后引动最终镇压的原因。
现在,幸亏两列火车把夏建国和田源分别带到了离北京很远的地方,让他们摆脱了“黑名单”的威胁,这才让任燕稍稍地松了一口气。但是下一步又怎么样呢?她所在的新华社每天的政治空气都很紧张,什么时候这种空气能稍稍显得松动一些呢?走出车站的时候,这位已经入党八个月的漂亮姑娘一直在作这样的思考,眉头皱得很紧。
两辆军车在宽街丁字路口路北的一个院落前停下。一身戎装的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兼八三四一部队副政委刘鑫从首辆军车的副驾驶座上跳下来。在他的指挥下,片刻工夫,训练有素的两车军人迅速前后列队,等待着刘鑫的命令。
这里是邓小平在北京的住处,也是他在被撤销党内所有职务之后被软禁的地方。这是一个秋夜,气温急剧下降,凉风滑过夜空。
宽街上很安静。往年闷热的秋夜,北京的大小胡同都有不少乘凉的人,可是今天的秋夜之街却是格外安静,也许是人们享受惯了夏天的温暖,不适应如此稍许微凉的气温,也许是人们还沉浸在毛主席去世的阴影中,不愿出门感受一个天理不彰的秋夜。
黑暗中,一名警察和几个工人民兵走了过来,见到刘鑫和军人身影,惊讶不已。警察问,怎么回事儿?这是我们的管片儿呀!
刘鑫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命令递给警察说,我们奉命执行重要任务,你们的公事完了,可以收队了。
警察愣了愣神,看看刘鑫和军人们,侧目对几个工人民兵说,八三四一部队,御林军出动了,肯定有大行动,没我们事儿了。
在警察和几个工人民兵屁颠儿屁颠儿走了以后,刘鑫便径直去敲大院的门。大门打开了一扇小窗户,里面的人见是刘鑫,并没有多问,门扇对开。
这是位于宽街十字路口路北的一处不起眼的小院落。这院落离东面的增归园只有五十米远的路,增归园是民国时期外交总长顾维钧的住宅,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先生就病逝于此。邓小平“文革”复出后和家人一直住在这个普通的两进四合院里。前院住着几个中央办公厅派来的监管人员,后院住着邓小平一家。院内中央搭着一间地震棚。墙壁上有些裂缝,明显留有大地震的痕迹。
院内的大屋和里屋靠着一盏光线微弱的灯勉强维持着照明,足见主人的节省。大屋里高挂着披着黑纱的毛泽东遗像,下面是一捧鲜花,略显哀伤气氛。里屋不时传来调试半导体收音机的声音。
洗脸架边,一位老人提着暖水壶往半旧的脸盆里兑热水,一只手在盆里试着水温。壶口冒出的热气映出一张慈祥沧桑的脸。这是刚刚度过七十二岁生日的邓小平。
卓琳走进屋来说,老兄,还是我来吧。
邓小平放下暖壶说,你刚从医院回来,眼睛不好,要注意休息。
老两口端着脸盆走进里屋。邓朴方正躺在床上摆弄收音机,从床头一大堆半导体零件看出他的摆弄似乎并不顺利。邓小平看到满身大汗的儿子很心疼,从妻子卓琳手里拿过毛巾递给儿子说,来,胖子,擦擦身子吧,当心捂出痱子。
邓小平喜欢这样叫自己的儿子,一来是邓朴方生下来就比较壮实,二来胖子这个词叫起来更显得亲人间的随和。
邓朴方放下收音机说,爸,我自己来。邓小平说,想法是好的,但你身不由己呀,有些事要靠别人呀!来,把上衣撩开。
邓小平弯下腰给儿子擦身体,卓琳在一旁帮忙涮毛巾。热腾腾的毛巾在邓朴方身上来回摩擦着,邓小平一会儿就累得气喘吁吁,额上冒出了汗滴。接下来,老两口又费力地帮助儿子翻过身来,继续为儿子擦身。
邓朴方把头深深地埋在枕头里,眼泪夺眶而出。邓小平假装没有看到儿子的眼泪,坐上床沿,轻轻拍了拍儿子的肩膀,让他注意穿好衣服,当心着凉。朴方没有回答,一时,老两口难过地看着大儿子,相对无言。
半晌,邓小平打破了尴尬的宁静,转移话题,关切地问儿子修理无线电的技术达到什么程度了。朴方小声告诉父亲,每天都有一点心得,只要钻下去,肯定能学会。往后,只要国家政策允许,他就用修收音机的技术自食其力,挣钱养家。
听了儿子的话,邓小平感到一些宽心,又感到一阵心酸。孩子们一个个都长大了,都想凭着自己的真本事吃饭,这是父亲很愿意看到的事情。
急促的脚步声就是这时候传进屋里来的,慌慌张张进门的是小女儿邓榕和小儿子邓质方。邓榕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咱家附近全是解放军,好像是“八三四一”的,院子里也添了好几个人,像要出事。邓小平摆摆手,示意孩子们都不要紧张。他问,除了当兵的之外,还有谁来了?质方说是那个刘副政委。邓小平问,刘副政委说要见我吗?质方说,没有,就说是要加强警戒,做好保卫工作。
邓小平想了会儿,挥挥手说,大家都去睡吧,没有事,这也是正常情况。
邓小平回到卧房之后,点燃一根烟。
他心里明白,警卫的突然增多,八三四一部队副政委刘鑫的突然现身,并非正常情况,中国的政治肯定是有一根弦正在绷紧。随着毛主席的去世,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角力,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对于宽街的这所小宅院来说,事情有可能向好的方面转,也很有可能向坏的方面走。如果有某一种政治势力飞速膨胀,那么“反击右倾翻案风”加码升级,甚至将“右倾翻案风的头子”加以极端措施以剪除心腹之患,都是有可能的。
邓小平缓缓地喷出一口烟,用缓缓的声音对老伴说,该开个家庭会议了。
邓小平的思虑并没有错。
中国的政治局势,在毛泽东主席逝世后,正依照自己的惯性,不可避免地朝那个方向滑去。一系列严重的情况都在向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的案头聚集,或清晰,或模糊,但都很说明问题。
江青一再纠缠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要求把主席的全部文件转交给自己,说自己是遗孀,理应得到这些文件;然后又去纠缠纪登奎,要查看保存在毛家湾林彪住所的相关材料。这些政治动作,显然是想控制或修改毛泽东的文件,以便为自己更上台阶“加封”。不久,江青又赶往清华大学,激动地鼓励年轻学生“战斗到底”。而张春桥的弟弟张秋桥,这位时任总政宣传部的副部长,悄悄赶往某坦克师活动。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也是动作频频,先是为自己拍“标准像”,然后又擅自在中南海设了一个“值班室”,用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各地,说凡是重大问题,都要向这个值班室请示报告。他还火急火燎地去了一趟上海,特别要求上海民兵“加强训练”,做好“拉出去”的准备。张春桥这时候也托人带口信给上海方面,说是“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其时,上海民兵指挥部的实力已经是三十个师、七个独立团、两个高炮营,是一支颇有实力的武装力量。而《光明日报》又杀气腾腾地推出了一篇署名为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叫嚷“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决然没有好下场的”。
不仅华国锋对这些情况忧心忡忡,住在西山的叶剑英也是终日坐立不安。他在看了《光明日报》十月四号发表的这篇杀气腾腾的文章后,当即就去找了华国锋,表达了自己对中国命运的担忧。而在这之前,华国锋也已经委托李先念上了一趟西山,秘密地会见了叶剑英,商量了必须阻止“四人帮”篡权的果断行动。李先念的那一趟西山之行,采取了“声东击西”的战略,他假托要去北京植物园赏红叶,继而摆脱了跟随的警卫,悄悄地走进了叶帅的西山住所。
在那些天里,叶剑英几乎每个晚上都没有睡好。他回忆起临终前的毛泽东已经说不出话来,只是用眼睛久久地凝望着自己,嘴唇不断地翕动着。他凑近耳朵去听,但是也没能听清一个词汇。他知道毛泽东是有“嘱托卫护江山”的意思的,但是这座以中国千千万万革命志士的鲜血与生命打下来的江山,到底如何卫护,是一道严峻的考题。叶剑英好几次在半夜里披衣下床,盯着桌子上的一排电话机,咬着牙关想,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用鲜血凝成的红色江山,绝对不能落到几个搞极左路线的人手里。
叶剑英想,这恐怕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这应该是全党的想法,是全国人民的想法,很可能也是已经与世长辞的毛泽东主席本人的想法。任何一种考虑,都比不上“人民的江山依旧掌握在人民手里”这一点来的重要。解放军是干什么的?解放军就是干这个的。
在那些夜晚,叶剑英的手轮流地抓起了电话机,一架又一架。
还有华国锋,还有汪东兴,他们都是彻夜不眠。
为了中国健康的前途,正直的中国领导人拉满了弓弦。
箭在弦上。
这关键的一箭是必须射出去的。
中南海对于世人而言不是一个地理名词,而有中国最高权力机构的含义,甚至是最高领袖的含义。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这里上演了一幕惊心动魄的剧目,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被中共中央宣布隔离审查。
这个决策作得非常果断,也执行得十分顺利。尤其是拘捕江青的那一幕几乎是波澜不惊。中央警卫团团长、八三四一部队负责人张耀祠严肃地对住在钓鱼台、已经吃过晚饭的江青说,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隔离审查,到另一个地方去,马上执行!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而一言不发的江青,当时也变顺从地从腰间解下一串钥匙,还把钥匙放进一个牛皮纸信封里,写下“华国锋同志亲启”七个字。“四人帮”另外三位成员的落马,就更加没有戏剧性了。他们都是在中南海怀仁堂就擒的,并没有对“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的通知发生怀疑。只是王洪文有一点挣扎,有一点拳打脚踢,但很快就被制服了。
当夜十点整,一辆辆满载军人的汽车风驰电掣驶出中南海。
一个身穿中山装、意气风发的老人带着一队军人急匆匆跳下军车,走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大楼。在大楼门口,他当场对随行军人下了个死命令:从现在开始,只准进,不准出。接着,他就大步进门,直奔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的办公室。
这位穿中山装的老军人就是耿飚,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他这一次没有带枪,出发前华国锋确实也问过他“你要不要带支手枪”,而他的回答是这样的:手枪不必带了,但是须有你的手令。
他走到邓岗办公室门前迟疑了一下,然后突地推门而入。
邓岗大惊失色,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此时,耿飚便将那张至关重要的手令递在了他这位老同学面前,说,老同学,我奉中央命令正式接管广播电台,从现在起,这里听我指挥。
接过这份手令,邓岗目瞪口呆。
看出邓岗的怀疑,耿飚说,派我来这里主持工作是华总理和中央的决定,你要不相信,打电话向姚文元请示也可以。但不许出去,电话就在这里打。
邓岗回过神来,赶忙把那手令还给耿飚,苦笑着摇摇头,表示自己一定会服从中央的决定。
这时,耿飚爽朗地笑了,他命令邓岗立即把电台的党委成员和各部室负责人全部找来,先开个紧急会议。
半杯茶的时间,会议室里面已经坐满了人,耿飚开始传达上级命令,说从现在起,我就和诸位在这间屋子里集体办公了,至少一周时间。你们谁也不许离开,吃饭、喝水,部队的同志都会给大家送来。所有节目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和监督。大家各司其职,不能出任何差错,明白吗?
一屋子的人都大眼瞪着小眼地互相张望着,谁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最后,大家都把目光转向邓岗。此时的邓岗倒是显得很平淡,说,没什么好说的,听军代表的吧。
耿飚最终决定让邓岗睡床上,自己在邓岗屋里打地铺。但是,对节目变动之后播什么内容,耿飚一时没了主意。他问身后全副武装的警卫战士,你们爱听什么歌?
其中一位战士笑着回答,老房东查铺。
耿飚说,那就放这一首吧。
就这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节目变动后第一个内容就是循环播放歌曲《老房东查铺》。耿飚后来又说,还是再多播播那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吧,多放它几遍,这样的时刻就应该多放几遍这样的歌。
接到深夜开会的通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心头一动,他想,事情应该是成了,叶帅与汪东兴的计划应该是很周密的。走了几步,他眉头又一皱:时局微妙,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这么想着,一颗心就咚咚咚跳得厉害起来。
李先念夫人林佳楣见丈夫从里屋走出,赶紧就拿着帽子追出来说,玉泉山那边风大,带上帽子吧。说着,她就为李先念戴上帽子,又扶扶正。
林佳楣看丈夫的脸色一直很沉重,心里也是一紧,但她不敢多问,只是嘱咐李先念万事小心。
李先念知道妻子心中的担忧,笑了一笑,又拍了拍妻子的肩膀,让妻子宽心。临出门时,李先念似乎想到了什么,回转身摘下手表放到林佳楣的手上,平淡地说,万一回不来的话,就作个纪念吧。
不等夫人说话,李先念大步走出门外。
望着丈夫远去的背影,林佳楣拿着手表,双手一直颤抖。
这年头,在中国,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这确实是关乎中国命运的重大时刻。
一个重要的会议即将在玉泉山叶剑英住所的会议室召开。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陆续走进会议室,这些人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锡联、纪登奎、吴德、苏振华、陈永贵,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倪志福。
大家按照习惯排列座次,围坐在会议桌前。
没有一个人说话。每个人都表情严肃,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每个人心里都清楚,即将有大事发生。
几名小战士进来为与会者的水杯倒水。陈永贵和吴桂贤像往常一样站起来致谢。陈永贵看见坐在对面的陈锡联抽烟,也从口袋里掏出烟斗来,一口浓烟喷出,坐在他身边的吴桂贤被呛得咳嗽了好几声。
钟声报时划破沉寂,二十三点整。一扇房门推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大步走了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