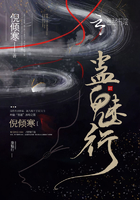我再次站在圣彼得堡的街头,给这座多色彩的传奇城市行深深的注目礼,我的心充满了崇敬,也灌满了沉重,更泛起阵阵深思的波涛,耳边则响起那悠扬的歌声:亲人的蓝头巾在船尾飘扬……
(发表于2006年《南方日报》《海风》版)
老地方在哪里?
"老地方在哪里?"每当到一个地方参观游览,当地人迫不及待地带我们到那些雄伟高大的标志建筑、气派恢宏的现代楼宇和堂而皇哉的形象工程参观时,我总免不了要问这句话。
老地方,当然包括那些古代数百数千年留下来的古迹文物。但这些,当地人也是不会忘记带你去看的,因为这也是城市的品牌、地方的特色和经济效益的源泉。但我指的老地方,更多的是人们不愿意带去的或者是不屑于带去的地方。那多半是那些未经过改造的居民住宅,那些经历过几十年风雨剥蚀已显得破残不堪的旧街老巷。
为什么想看这些?并不是想挖城市的疮疤,揭当地的老底。究其实,是想寻找一种文化,一种深藏在民问的,虽然非常粗陋、残缺、破旧,却是十分真实的、原汁原味的文化。因为那些现代建筑和形象工程,尽管不乏设计上的功力,尽管不乏震撼人心的壮观,尽管也会给人以很高的欣赏价值,但毕竟千篇一律,千人一面,使你看后,除了嗟叹一番其奇伟壮丽外,似乎并未找到城市的文化底蕴,并未感受到当地的文化特色,更无从辨别这个城市为什么叫这个城市而不叫别的城市。相反,在那些老地方,从那些鳞次栉比的低矮房舍中,从那些残头拙尾的旧街陋巷中,从那些沿街叫卖的商贩小摊中,从那些错落参差的食肆店铺中,你完全可以领略到当地居民的家居文化、饮食文化、邻里文化、婚丧文化、商贾文化……在你面前展现的,是一幅色彩斑斓的风情画,是一道朴实亮丽的风景线,使你仿佛重新回到了欧阳山笔下的巷陌骑楼,老舍笔下的胡同院落,巴金笔下的里弄街坊……还有那青青的石板路、颤颤的吊脚楼、悠悠的清水河……更有那飞机榄、炒米糖开水、冰糖葫芦、串烧羊肉……。所以,老地方就是老地方,其深藏的魅力,其蕴含的诱惑,就全在这个"老"字上。这也就使我想起了怎样才算找到文化的真谛这个问题。文化其实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和折射,是真实人间的写照与实录。因此,不一定冠冕堂皇,现代超前的才叫文化。越粗陋、越简朴、越原始的东西,正由于它越贴近生活,所以才真正蕴含着文化的真谛,让你品尝时会感到如同嚼一颗余味无尽的甘榄,品一杯余香馥郁的清茶,听一曲余音绕梁的乐曲,无比惬意,无比舒畅。因此,对这些"老地方",切勿以其粗陋而嫌之,也勿以其破旧而弃之。不要轻易拆掉重建,推倒重来;更不要轻易用一些时髦的瓷片一贴了之,使之变成千篇一律、古今不分、不伦不类的怪物。而应该尽力地去挖掘、抢救、修缮,使之永远保持其特殊的魅力。《岭南文史》杂志在发掘岭南地区历史文化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为此,特借贵刊发表我的一点感想,愿与从事文化工作的同志共勉。
(发表于2004年广东省参事室《岭南文史》"卷首语")
"白云松涛"名不虚传
广州的"羊城八景"脍炙人口,名闻遐迩。但"羊城八景"的具体景点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评定,有的同一景点名称也有改变。我记得现在叫"云山锦绣"的一景,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叫"白云松涛"。为何叫"松涛"?那时山上只种一种树--松树,自然就以松为名了。但"涛"呢?原来我以为那是修辞手法,意即漫山遍野是松林松海,风吹过处,宛如波涛翻涌。后来一回的偶然亲历,才使我顿悟其真实含义所在,并深为起名者的良苦用心所折服。
那天我住山庄旅社,傍晚饭后,信步出得山门,沿山间公路漫走。是时太阳还没下山,斜阳穿过无数针叶撒射进来,仿如千万支金箭扎满山岭,煞是好看。未几,太阳悄悄下山,天色骤然暗了下来,大团雾气从四面八方涌向山边路旁,景色越来越朦胧。一阵山风吹过,竟然有几分凉意侵入肌肤,令我不觉有几分怵然。正在这时,从身后突然传来一阵阵"嗬……嗬……"的声音,先是很轻微,像小溪流水,又像丝丝细雨,仿佛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但仅一会儿声音就大了起来,越来越大,一阵盖过一阵,像山洪暴发,又象海涛奔涌,而且感觉已逼到身后。我赶忙掉头一看,却什么也没有,空落落的公路依然静静地躺在暮色中,满山的松针叶子在微风拂摩下轻轻摇曳。这时声音变小了,并渐渐归复平静。
我又放心继续前行。但未过一会,一阵晚风吹过,声音又起来了,而且比上回更大了,一时间好像滚滚的洪水好像澎湃的波涛从身后乃至四面八方呼啸着奔涌而来,我又一阵寒颤,可回头看还是什么都没有,黑黝黝的。如是一惊一恐的好几回。这时候,天色完全暗了下来,夜幕莽莽涛声依旧强弱起伏。偌长的山路就我自己孤零零地走着,我忽然觉得好像被洪水包围住,不由得从心底升起一阵恐怖,猛然一掉头就飞步往山庄跑回,一回到房间,立刻把涛声风声全关在门外,屋内一片寂静,才终于止住心跳,缓过神来……
白云山后来由于受一种病虫害,松树生长受阻,就逐步改为现在的多树种,当然就再也看不到松海,听不到松涛了。我也问过一些人,以前如是白天,也未必能听到涛声,只有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才能体会和感受得到。于是便把当年的境遇记录下来,以餐读者。
(发表于《羊城晚报》《晚会》版)
庐山含鄱口谜
登庐山,那里有很多很多好看的景点。不要说那曲径通幽的"花径"和峰峰岭岭,那里留下了白居易、李白、苏东坡等历代文人墨客的遗宝遗迹;不要说那道佛儒同尊、甚至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都尊为圣地所留下的文化瑰宝;更不要说那依山傍水而建的中西合璧的连绵起伏的别墅群,不但每一栋都隐藏着一段令人叫绝的故事,光是那建筑艺术就足够建筑学家和考古学家们叹为观止了……
然而,在庐山,最令我叫绝的是登上著名的"含鄱口",鸟瞰浩浩淼淼的吴楚大地。汽车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斗折蛇行,两旁是密密丛丛的古木野林,太阳光全给挡在绿林外面,到处是阴凉阴凉的。不知道转了多少个弯,打了多少个旋,一个急转弯,车终于钻出了树海林涛,眼前豁然开朗,一个海拔一千多米高的巨大的壑口出现在脚下。这就是名闻遐迩的"含鄱口"了。我定睛一看,真的好气派!背后有仿如埃及金字塔般的尖三角形的庐山第一主峰"汉阳峰"(1474米),就像一张大大的"龙"椅背高高的耸入云端;左边是郁郁葱葱如绿伞如荫屏的香炉峰,著名的"三叠泉"瀑布隐匿其间;右边是连绵起伏如奔马如走狮的"狮子山",一直绵延到天边;最奇特的是三面环山的壑口的正前面,完全敞开的偌大的吴越大平原尽收眼底,浩瀚搏大,无边无际,烟雾茫茫,水气氲氤,著名的鄱阳湖以及弯如丝带的长江朦朦胧胧地依偎在大平原之中,极目处那一堆小积木据说便是南昌城。站在这里,真有一口吸尽茫茫山林江湖之感……这时候,心中不由得豁然呼出的是毛主席的诗句:"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我终于顿悟"含鄱口"的含义,那不是含鄱阳、襟三江、吞吴越?中国民间对山讲灵气讲风水,这含鄱口简直是最典型的风水山,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样样齐全,而且其气势之磅礴,可以说穷天下都难以再找到第二家:讲青龙,有李白所写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瀑布;讲白虎,有盘旋绵恒的丛山;讲朱雀,有浩浩淼淼的鄱阳湖;讲玄武,堂堂正正魁梧雄伟的汉阳峰无与伦比。
但这样一座风水郁郁的庐山,数千年来却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皇帝的封禅,皇帝留下的脚印和墨宝亦绝无仅有。仅有一点传说,说朱元璋当年在江南一带活动时,与陈友谅在鄱阳湖打了一仗,大败而逃,走到庐山的锦绣谷,前有天堑,后有追兵,突然一条天龙臥陈两山之堑,朱元璋刚一跃过,天龙呼啸一声腾上空中,追兵只好隔堑而叹。朱元璋转脸大声说:"请秉陈元帅,感谢相送,后会有期!"但这不过是传说而已,是不是真的,没人知晓。据《明史》载,朱元璋败后是乘船从水路回应天府(今南京),可见并未上庐山。如是真的,后来朱元璋当了明太祖,照道理应该对这个让他化险为夷的地方大书特书、大树特树才是,可只留下一个"御碑亭",也只是为一个神话人物周颠仙人所立。朱元璋是有一首《庐山诗》:"庐山竹影几千秋,云锁高峰水自流。万里长江飘玉带,一轮明月滚金球。路遥西北三千界,势压东南百万州。美景一时观不尽,天缘有份再来游。"充其量是一首旅游观光诗,没多少寄托,且诗又没放在庐山上。
因此,这就是一个令人不解的谜了。这么好的风水,却得不到皇帝的青睬。是不是他们没真正登上"含鄱口"呢?
总有慧眼相识。时代翻过了一大页,到了二十世纪,便有人注意它了。1926年12月4日,担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从南昌乘坐火车到九江,再换乘轿子从莲花洞经好汉坡,一步一步上了庐山,到达牯岭。此行是要在这里召开会议,研究国民政府迁都之事,没想到一下子便被庐山的"奇绝"(蒋介石语)风光所叹服,当即萌发"异日退老林泉,此其地欤"的感慨。特别是蒋介石站在含鄱口上,傲视天下如蚁蝼如虫穴如鸟巢,更有一番执九州之牛耳的王者气概。从此,庐山便变成了政治山,这次会议被称"庐山会议",竟定夺了以后几十年在这里开会的统称。传说蒋介石不主张迁都南京,一直坚持定都南昌。个中缘由,是不是担心南京为虎踞龙蟠之地,龙争虎斗,难守易攻,不易稳坐,历史上坐镇的好几个王朝不是短命夭寿(如宋、齐、梁、陈、南唐、太平天国)就是中途易主(如明建文帝);反而南昌就在含鄱口和庐山的怀抱中,吸尽山川灵气享尽风水哺育?这一点,就只有他老人家自己才心知肚明了。
总而言之,蒋介石自从登上"含鄱口",便深深爱上了庐山,依恋了庐山。从1926年开始,一直到他即将被赶出大陆的1948年,短短23年间,除了抗战八年蜗居重庆实在上不了山,他一共登了18次庐山,每年至少一次。据说,每次上山,免不了要携宋美龄,到"含鄱口",面对浩浩淼淼的湖光山色膜拜一番,感慨、抒怀、寄志、祈祷……尤其是1932年,他在这里指挥对鄂豫皖红军的围剿,竟出人意外地获得成功,把红军往陕西方向赶。他像是得到了什么启悟,对庐山更是钟爱有加,立刻在这里办起了军官训练团,专门训练对付红军的将士,还建起了庐山传习学舍和大礼堂,把庐山变成了他的"夏宫",他在这里坐统天下,不少大事都在这里研究定夺。也巧,此后在庐山的几年,蒋介石竟然大发风水,他在这里指挥了五次对红军的围剿,虽然前几次丢兵折将徒而无功,但最后一次毕竟大获全胜,把红军赶出了江西。要知道红军是他一块最大的心病,对付红军又是他最头疼的事情啊,他该多么感谢庐山给他带来的好运才是!
及至到了蒋介石从重庆迁回南京,国共两党两军开始对垒时,蒋介石都不会忘记庐山给他带来的好运。1946年到1948年,当战场上不断传来风声鹤唳的战报,他简直是神不守舍,如丧考妣地匆匆赶往庐山,几乎全坐镇在那里,多次召开反共军事会议。最为严峻的是1948年,三大战役陆续打响,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气急败坏的蒋介石无计可施,更加离不开庐山,更加祈求庐山会给他带来奇迹、带来转机、带来运气。然而,连他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风水如此壮丽如此灵验的庐山,这回却失灵了。于是,到了这一年的8月,他只好在他和宋美龄居住的"河东路180号"别墅题上"美庐"二字,便匆匆离去,再也不复返了。"美庐"之意,后人猜测和附会很多,有说"美丽的别墅"(庐即房子),有说"宋美龄的别墅",有说"美丽的庐山",依我之见,固然有为宋美龄所题之意,但更多是赞叹庐山之瑰丽,因为庐山对于他,的确是太牵肠挂肚了。
有一个成语叫"鹊巢鸠占"。风水也是轮流在转,蒋介石没想到的是,风水早已转到对立面去了。事过十年,1959年,又一个伟人登上了庐山,而且也是一眼就爱上了庐山。这就是毛泽东。传说毛泽东一上山,就为庐山的蜿蜒曲折所迷,询问旁边的人究竟有多少个弯?回答说四百个,于是就有了"跃上葱茏四百旋"的诗句。又传说毛泽东一开始就住进了"美庐",也爱上了"美庐",一进庭院的大门,就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大声说道:"哦,久违了。蒋委员长,我来了!"这个"占"不但是占定了,而且是那么的不可动摇,无论谁与之相碰,都会碰得个一败涂地,碰得个鸡飞蛋打。庐山,继续扮演着其政治山的角色,在这里演出了多少出政治活剧,彭德怀、陈伯达、林彪,一个个都被"含鄱口"的风风雨雨打得花落残红。是啊,连一代统领的蒋介石都无法改变得了的历史趋向和命运,又有谁能改变得了呢?此时此刻,才令人顿悟"一山飞峙"四个字,不仅压倒了无数歌咏庐山自然景观的诗章,而且更展示了一代伟人"横空出世,阅尽人间春色"的英雄气概。至此,应该毋庸置疑,如果不是站在"含鄱口"上,毛泽东又怎么能喊出"一山飞峙"这样的穷尽古今的名句?
庐山的云飞雾度、襟江带湖、岚影波茫、层峦叠嶂,迷到了多少文人墨客。庐山的景色是迷,庐山的王气更是谜。古往今来,抒写庐山的诗篇中,单是感叹庐山的神秘幽深的即林林总总。苏东坡的诗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可謂对庐山意乱神迷的景观的绝叹。李白的诗云:"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一个"疑"字显尽暧昧。(顺便说一句,三千尺,原以为是一个槪数,但到实地一看,瀑布上流约1000来米,刚好三千尺,可见李白观察力之深)。白居易的诗云:"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一个"不知"道尽奇妙。连堪称与"五老峰"媲美的党内"五老松"徐特立、谢觉哉、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1959年在庐山七步赛诗,也尽以庐山真面目为题。谢觉哉词云:"牯岭雨声喧,气象万千。爱听东谷水潺爰。日照香炉知何处?雾里云端。||智慧何人先?卡尔开山。重峦叠嶂更新鲜。一二三四大手笔,宝藏兴焉。"(《浪淘沙庐山即景》)董必武诗云:"庐山面目真难识,叠嶂层峦竟胜奇。乍晴乍雨云出没,时高时下路平陂。盘桓最好寻花径,伫立俄延读御碑。如许周颠遗迹在,访仙何处至今疑。"(《初游庐山》)林伯渠诗云:"匡庐胜景都争识,流水高山特呈奇。崖拥翠松几日月,云如沧海起陀陂。清泉终古漏仙洞,化径何人写石碑。栗里先生留雅韵,桃园是处不须疑。"(《庐山即景步董老初游庐山韵》)谢觉哉意犹未尽,补写一首《游海会秀峰等处》:"又是中华第一山,从庐山外看庐山。一泉飞跑自天下,五老从容席地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