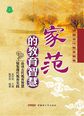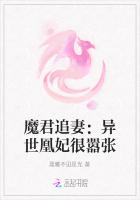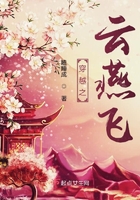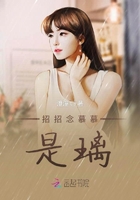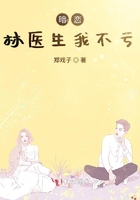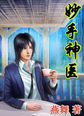心体光明,暗室中发青天;念头暗昧,白日下发厉鬼。
——洪应明
太阳是光明的,它普照大地,施惠于万物;月亮是光明的,它皎洁明亮,光洒人间;白昼是光明的,它正气浩然,朗朗乾坤;蜡烛是光明的,它燃尽自己,照亮别人。
做人,也应当是光明的。面如明镜,心如清泉,行如骏马,言如玉石,堂堂正正,光明磊落。
古人说过:“人心贵乎光明净洁。”心地光明,襟怀坦白,是高尚的思想品德。一个坦荡的人,必然是一个淡泊私利的人,一个正直善良的人,一个忠诚老实的人。
对人,应当坦坦荡荡,不应小肚鸡肠。北宋时期的欧阳修,不但以文著称于世,而且他那种捐弃前嫌、奖掖后进的坦荡胸怀,更为后人称颂。嘉佑五年(一零六零年),欧阳修升任枢密副使,次年又任参知政事,身居宰辅,手握重权。在他当朝问政时,他不是用权力来排斥与己不同意见者,而是积极地奖掖后进,为国荐贤。有一次,英宗要他推荐三名可以担任宰相的人,欧阳修同时推荐了吕公著、司马光、王安石。这三个人不但不是欧阳修的至交好友,反而与他都有过前嫌,有的甚至竭力反对过他。如吕公著在庆历年间曾力攻欧阳修,认为他是范仲淹的同党,为此,欧阳修被贬谪滁州。英宗即位时,曾围绕濮王称为皇伯还是皇父问题,朝廷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司马光的观点与欧阳修完全对立,王安石也阐述了自己不能苟同欧阳修的某些主张。尽管如此,欧阳修并不耿耿于怀,却认为他们确有宰相之才,于是一同举荐。时人曾说欧阳修“于晦叔(吕公著)则忘其嫌,于湿公(司马光)则忘其议论,于荆公(王安石)则忘其学术,世服其能知人”。
对己,应当襟怀坦白,决不文过饰非。澳大利亚前总理鲍勃·霍克,有一次在电视发表演说,坦诚地讲到了他过去的私生活,只见他声音颤抖,双眼闪着泪花。五十九岁的霍克说:“是的,我对妻子不忠,但那是短时间的、早年的事了。”他说:我与同庚妻子黑兹尔是在十七岁时相爱的,至今已是四十余年的夫妻了。他夸黑兹尔是一位很能谅解人和体贴人的贤惠妻子。霍克此举并未使他失掉面子,相反,却赢得了赞扬。第二天,澳大利亚的许多报纸都以显要版面发表了霍克的谈话,用了醒目的通栏大标题:《霍克承认不忠行为时哭了!》、《霍克勇于承认过失,举动非凡,真是奇迹!》。
对事,要秉公而行,决不鼠窃狗偷。公元七十三年,班超为联络西域各国抗击匈奴而出使西域。汉章帝初年,北匈奴卷土重来时,班超已在西域驻扎十余年,他奋力坚守,英勇反击。卫侯李邑奉命护送使者至于阗,见烽火连天,不敢西进。为掩盖自己的胆怯,遂上书皇帝,言“西域立功不可成”,又诋毁班超“安乐外国,无内顾心”。帝知班超忠心,令李邑受班超节度;而班超却能大度为怀,秉公处事,不留李邑在西域,而将其遣返京师。班超光明正大,问心无愧,可以为人师表。
磊落者,真也,说真话,办真事,实实在在,真真切切。虚假的东西,永远是卑微的,无力的,令人生厌的。“贼怕响声鼠怕亮”,对待虚伪者,最好的办法是用事实将其戳穿,让他在阳光下无地自容。
然而,除伪亦非易事。明朝吕坤在《呻吟语》中说:“用三十年心力,除一个‘伪’字不得。或曰:‘君尽尚实矣。’余曰:‘所谓伪者,岂必在言语间哉?实心为民,杂一念德我之心便是焦;实心为善,杂一念求知之心便是伪;道理上该做十分,只争一毫未满足便是伪;汲汲于向义,才有二三心便是伪;白昼所为皆善,而梦寐有非僻之干便是焦;心中有九分,外面做得恰像十分便是焦。此独觉之伪也。余皆不能去,恐渐渍防闲,延恶于言行间耳。’”
当然,吕坤所言,是从严要求,自慎其独,表里如一,无分毫相悖,一般也是难以做到的。不过,一个人要真心求得光明磊落,朝这个方向努力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