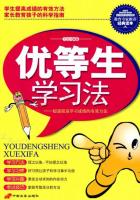她在吵嚷的学校食堂里,隔着小小的柜台看到他,便即刻失了语。
那时她刚刚高中毕业,父母没有钱再供她复读,她一句话都没有,便收拾了行李,随一个做厨师的亲戚来到了北京。每天,她都会站在柜台后面,做着千篇一律的工作:盛菜、打饭、端汤、收钱。但她从来没有厌倦过,能够站在自己心仪的大学里,隔着柜台,看一眼那些比自己幸运的人在面前穿来梭去,于她,已是一种幸福。而能够瞥见他们手中抱的一本本书,哪怕只看到封面,她的心里也会激荡起层层的波浪,它们一次次地冲击着她心灵的海岸,让她在一片喧嚣里,却始终觉得自己是一只鸟儿,有结实的翼翅,可以与他们一样带梦飞翔。
而当她的梦里有了他的时候,头顶的那片天空,则愈发地明朗澄澈了。
她依然记得那一刻,他走到她的柜台前,敲敲玻璃橱窗,指指那份一元的土豆丝,而后将钱递过来。她接过那枚带着他的体温的一元硬币,慌乱地看一眼他温和的面容。这是她第一次遇到自己喜欢的男生,那种感觉像是一朵荒野里的花,在寒风里忽然被一双手,温暖了片刻,欣喜中便绽放开来。她也知道这样的绽放,是不合时宜的,那双手不过是无意中碰触到了她而已。可是,所有的爱情,都是这样毫无预期地来到的吧?她只知道那一刻,她不仅脸红心跳,不敢看他,甚至为他盛了三两米饭,却忘了告诉他,只买一份一元的菜,是不能赠送任何米饭的。
其实,他是个很平凡的男生,常常穿的是一套学校的校服,一双白色的运动鞋,但无论什么时候看到他,都永远是干干净净的,就像一朵天上的云,漫不经心地飘在那里,却不知道那样的存在,有多么的纯净。尽管从他每次买的菜上,她能够猜测出他是来自于偏远的山区,父母没有多少的钱可以让他在吃穿上,更讲究一些,但是她却固执地欣赏他的这种素朴、安静。她永远都不会喜欢上那种衣着前卫,却满口脏话的男生,甚至当他们毫无礼貌地冲她发脾气,嫌她打饭慢时,她会下意识地少给他们一些。而他,尽管与他们一样,或许从来没有注意过她穿了什么衣服,头上戴了什么发饰,但是眼睛里却始终藏着一股暖流。
这种温暖,只有她能够明白,因为她正一步步地逆流而上,而那股暖,也一阵阵地拍打着她的手背,溅起细小的浪花。她知道他读工科,比她提前一年来到这所大学。她知道每个周三上午的最后一次课,他一定是学的英语;而周五的下午,他会去球场上打球。他还在校园里,为一家书店打工。有时候隔着食堂的门,她会看见他骑着自行车,飞奔而过,她知道那一定是他在去上课的路上。她一直觉得,他和那些各式各样的菜一样,是有味道的。他在她的心里,如一份清凉可口的沙拉,或者一盘碧绿的油菜,一碟清爽的泡菜。她喜欢这样简单的味道,胜过那些她无法奢求的山珍海味。那是家常的幸福的味道,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品味出来。除非,她是在爱里。
是的,她已经在爱里走了许久,而他,或许不过是将她当成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打工妹。他只是习惯性地会到她的柜台前,打已经温凉的特价菜。或者在视线与她相遇的时候,冲她和暖地笑笑。再或走过她的柜台,却并不停留,只是将眼睛淡淡扫过橱窗上的菜价表。她不知道他有没有觉察过,那些只有她才知道的秘密。她会故意地将一两片鱼,放到特价菜的角落里,只等着他来的时候,装作不经意地舀入他的盘中,而米饭,她从来都是给他多盛一两的。她知道他喜欢吃鱼丸,但因为价格,只每次将视线在上面停留几秒钟,便迅速地移开,但她却是每次都记得为他在米饭里,藏一个小小的鱼丸,而菜的分量,必定是冒出勺子的,它们在勺子里,像她心里满满的爱,溢出来了。
但她知道,即便是她的爱解冻的小溪一样,哗哗地流过他的身边,她也会小心翼翼地不去溅湿他的脚。她知道自己的卑微,尽管她偶尔听说他是贷款读书的。可是学校的大门,她可以进来,但从食堂到教室的二百米的距离,她却是永远也无法跨越,除非她能与他一起,站在柜台的外面,哪怕只是点一份最简单的土豆。
没有人知道她的这个向往是如何地炽烈。它在她的心中,如一团火,熊熊地燃烧着。几乎每天晚上,她都会在别人躺下的时候,拿一本英语书到走廊上去,借着微弱的灯光看到梦神温柔地过来唤她。日间的疲惫,因了这一段无人知晓却快乐充实的时光,而青烟般散去。她在来到这所学校后的第一个月,认识了他,却为此付出了十一个月,来昼夜兼程地追赶着他。昔日那些难懂的习题、拗口的单词、总也记不住的文章,全都在她的心里,如一株藤蔓落在窗户上的剪影,被他这股温暖的风一吹,便即刻生动起来。
一年后的一天,她又在食堂里遇到了他。他对着给自己打饭的女孩,疑惑不解地问道:“你们食堂的菜和米饭,为什么比昔日少了呢?”柜台前的女孩,散漫地瞥他一眼,便将盛米饭的盘子扔在秤盘上,计量器的针,精确无误地指向“2”这个数字。他站在那里呆愣了很久,才将手伸向盘子,扭头走向对面的餐桌。而她,就坐在同一个餐桌上等着他的到来。
从食堂到教室的那段距离,她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而今,她终于能够有机会亲口告诉他,那一两多出的米饭的秘密,还有,她曾怎样深地爱恋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