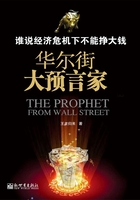白云生道:“你没别的事做?”
周学儒嘿嘿一笑道:“照料你们就是我的事。”
白云生道:“看你模样,却不是军中士兵。”
周学儒道:“我家原在沈阳,只是平常乡下农家,鞑子占了沈阳,残暴得紧;前年有两个鞑子不知怎的误打误撞来到我家,肚子饿了,要我妈将鸡笼里的鸡做给他吃;妈要将鸡杀掉,却很心疼,家里平日靠这只鸡下蛋,便像宝儿一般;我气愤不过便与他们理论,说道你们头领说不侵扰我们汉人,你们这时怎么忘了他的话啦。那两个畜生哈哈大笑,说我们王戏弄你们,你也当真,却拿这话来压我们;就将长枪对准了我胸口。我那时也是吓得呆了,却不知他们只是吓唬我,跑开也就好了。我爹以为他们真要动手,操起菜刀就上去拼命,娘只在旁哭叫,说我给你们烧鸡吃,你们放了他。可这时爹已冲了上去,却被两个畜生一枪刺在身上,就这么死了。妈疯了一般上与他们撕扯,也被那两个畜生使枪杀了。只恨那时我已吓得只是哭,没敢上去动手。那两个畜生本也要杀了我,却不知怎的又没动手。后来我逃到宁远,见袁大人正在修城,我一心敬重的就是能杀鞑子的英雄,便千般求肯留在了袁大人身旁,做些寻常事务。”要知当时满人全不当汉人作人看,一个人也不过一头牛的价值;时常有金军将汉人虏来,到集市上交换牲畜等物。
白云生心里道,原来这也是个苦命的人,乱世之中,皆是不幸之人,又何止我一人。
只听周学儒又道:“白大哥你也是个大英雄,这两天你与满大人交手的事已传开了,你只一出手便将满大人摔了一跤,还摔得满大人心服口服,本事当真厉害,可让小弟羡慕得紧。”
白云生道:“这话你不要乱讲,我也不是什么英雄;你既有心,何不做一番叫人称道的大事。”
周学儒道:“我自知不是那块料,想当英雄真是痴心妄想;我这辈子也不过两个心愿,一是盼我们大明早日打败鞑子兵,收复辽东;二是娶个媳妇,生一堆孩子,一家人平安喜乐,也就心满意足了。”
周学儒与白云生熟络起来,也不拘束,只当白云生是自己大哥一般。
白云生道:“听你说的,倒让我想起宁做太平犬,不为乱世人那句老话。”
周学儒道:“当人当狗自己是坐不了主的,全得看老天爷的意思;不过还是做人有意味。我死以后,倘若阎王问起,小周,你下辈子是想做人啊还是想做狗啊;我自然告诉他,阎王大人,小人是一千个一万个想做人;要是阎王问起一条死狗,死狗啊,你下辈子是想做人啊还是想做狗啊,那狗只会汪汪直叫,叫得阎王爷心也烦了;道,连句话也说不清,拖下去继续当狗吧。哈哈,由此可见还是做人好些,要是能像白大哥一样的英雄人物,更是好极。”
白云生道:“莫再说我是英雄了,我实在是称不上的。”
周学儒道:“要是连白大哥你都不算英雄,那谁又算得上英雄。”
白云生笑道:“待你封大哥回来,你可去问他。”
到了午时,封万仞与柳如风也未回来,就只柳茵与白云生一起吃饭。柳茵却似胃口不好,吃了几口就停筷不食;待白云生吃完,柳茵对白云生道:“白大哥,左右无事,你能否教我习剑。”
白云生道:“你剑法本也精妙,又何必让我教你。”
柳茵心里一动,暗道他却何时见过我使剑法,莫非那日与韩山及其手下恶斗,他早已注视着自己;想到这里不由得脸一红,道:“我学的是三华门的剑法,只是凭我的资质,怕再难有进境。日后找韩山报仇,更是妄想。白大哥你剑法通神,若能指点,我自然,自然是极感激的。”
白云生见她脸红,以为她羞于剑法不精,便也不再推辞;再者他对柳茵也实在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只觉得见她一面便有一种莫名的欢喜,虽然自己言辞脸色仍是一旧云淡风轻,但自己的心思却再也清楚不过;只告诉自己,如此美貌女子,谁不心动;爱美之人,人皆有之,自己也不过是出于人之常情罢了,毕竟自己心里还惦念着那人。
两人来到院中,白云生将使剑时的手眼身法步一一讲给柳茵听;一是柳茵剑法未精,二是三华门的武艺与白云生所习剑法实在天差地别,是以柳茵用心习来,自是受益匪浅。
到得晚间,封万仞与柳如风两人醉醺醺的回来,二人脸上都是说不尽的春风得意;周学儒安排众人到厅堂落座,将饭菜端了上来,周学儒亦与众人同食。
柳茵忽道:“柳少侠不是不饮酒的么?”
柳如风哈哈一笑道:“酒逢知己千杯少,与封大哥在一起,一千杯却也不多。”
周学儒夹了一块五花肉送与口中,不料中途一滑,那一块肉啪地一下掉在了桌子上;周学儒赶忙用筷子将五花肉由桌面上挑过来,嘴里却道:“封大哥,今日我说白大哥是英雄,白大哥却不认。”他为免尴尬,随口就将白日里与白云生所谈讲了出来。
封万仞道:“他自然不算。”
周学儒问道:“白大哥怎么不算?”
封万仞道:“这小子出道之时太过狂傲,现在又这般木讷,哪有半点英雄气概;他的功夫我是佩服的,不过此时也怕比不得我。英雄嘛,先要有一身惊人技艺,再就是心怀侠义,敢为天下公;这小子可不成。”
周学儒阴沉着脸道:“这样看来,封大哥你可算得一位了。”
封万仞道:“我自然也算不得。且不说普天之下,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单说我自己,喜的是美酒美人,宝马宝剑,快意恩仇,若要枉称英雄,只怕被人笑掉大牙。”
周学儒道:“袁大人又如何?”
封万仞道:“袁大哥功夫差极,何况他心里,只一半是百姓,另一半却是酬得壮志,名满天下。”
周学儒闷闷不乐道:“依封大哥之见,谁又当得上英雄呢。”
封万仞嘿嘿一笑道:“你莫要不服,当今之世已无英雄;如岳飞岳将军一般,如戚继光戚将军一般,方称得上英雄二字,可在我心中,郭靖郭大侠才当得上大大的英雄;他武功盖世,重情重义,孤身抗金,为国为民,此等人物方才让我等高山仰止。”
周学儒见他说的有理,无从反驳。众人吃罢了饭,各自休息。此后时日,白云生常教柳茵剑法,周学儒大多在旁观看,两人有时不经意碰触,都是急急分开;柳如风与封万仞自然每日里玩得不亦乐乎,袁崇焕若得空闲,便来与众人吃饭谈心。
这一日已是初十,天空中落起雪来,柳茵与白云生时时在一起习剑,只是白云生性子沉默,除了讲解招数虚实变换、劈刺技巧外,很少谈及其他。不知为何,柳茵却很难定下心来,一个招式使了多次也是不成,更别说身形步法了。
到了晚间,柳茵仍是耿耿于怀,想到这一生恐再难报杀父之仇,又悲又愤。她推开屋门,雪仍未止;屋内灯光顺着敞开的门斜照出去,落在丈许长的白雪上,终究越来越暗淡,与那黑夜中的风声一起,都不知去了何方。柳茵见柳如风屋里灯光亮着,暗道平日里见他一面也难,这时何不去向他打听打听白云生的事,却又想夜色里自己一个女子去到单身男子房里着实不妥;于是轻敲窗棂,道:“柳少侠,可否到我房内一趟,我有关于黄恩公的事情要请教。”
柳茵声音不大,但是几个屋子里的人还是听得见的。
柳如风推门而出,道:“雪夜遇杯酒,月下会佳人。妙极妙极。”
柳茵引他入屋坐定,道:“此番到长白山,不知为何,黄恩公会在给先父信中提及我,柳公子可知晓?”
柳如风笑道:“这个我也不知,莫不是要你给他做儿媳妇。”
柳茵怒道:“你若再胡说,不如这就回去罢。”
柳如风赔笑道:“是我失礼,不过我实在不知黄老伯打的什么主意。他也只是与我说知让我南行接应你们,若不是在张家店听人谈起那日拼斗之事,恐怕多半还要与你错过。不过你们赶路也太急了些,我还以为你们多半只在山东河北一带。”
柳茵道:“先父说多在路上一日便多一分的危险,是以行路极快。”喉咙哽咽一下,又道:“只是无论如何,却还是没逃过这一劫。”
柳如风知此等事安慰也是枉然,便陪着柳茵沉默半晌,又听柳茵道:“杀我父亲的是那韩山,赵公子却也脱不了干系。我这些日子随着白大哥练剑,只是他剑法深邃,不是一时半刻能领悟的,你可知他那剑法有何名目。”
柳如风道:“我自然知道。”
柳茵见他不再说下去,道:“知道为何说不出。”
柳如风呵呵一笑道:“我不是说不出,只是不想说。莫说那剑法,就是白兄过去的事情我也晓得。”
柳茵心头一动,道:“能不能说给我听,白大哥他,他救了我的命,我总是该回报的,多知道他的一些事也是好的。”
柳如风嬉笑道:“也不是不行,只不过有个条件。”说完对这柳茵眨了眨眼。
柳茵道:“你偏有这么多说法,是什么条件。”
柳如风正色道:“却也不是什么难事,只要日后让我叫你姐姐就可以。”
柳茵哭笑不得,佯作怒色道:“你又胡说八道来戏弄我。”
柳如风道:“我说的是真心话,绝非胡说八道。”
柳茵想,倒少见他如此认真,看他年纪未必有我大,叫声姐姐也是寻常。便道:“那也随你,我年纪比你大,就是当你姐姐你当得。”
两人初见之时,柳如风便要叫柳茵做柳姐姐,只是那时柳茵大觉不便,两人仍做柳姑娘、柳少侠一般称呼。
柳如风脸现喜色,自顾自咕哝了好几声姐姐,好像小孩子在学人说话一般,柳茵道:“现在可以讲白大哥的事了。”
柳如风眼中光芒闪动,转瞬消失,又回复那满面生花的神情道:“白兄那剑法名为孙武,若不是久经江湖大有名望之辈,恐怕也不识得。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略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霆,此乃孙子兵法中所载,说的是军队行军作战之要,以此化作剑法确有万钧之势。柳姐姐你也见过他使剑,其中利害也不用我多说。难得是这剑法江湖中仅寥寥数人会使,而如今天下恐怕只有白兄一个人会了。以此剑法现江湖之中莫不是声名大噪之辈,其人如剑,也是神鬼莫测,天意难知。”
柳荫见他翻来覆去只是说这剑法,却不谈白云生之事,便道:“白大哥的剑法我是亲眼所见,确如你所说一般。”
柳如风微微一笑道:“柳姐姐你莫急,要说白兄之事,必要先从这剑法说起。二十多年前,江湖上忽然出现一奇人,专向江湖上各家各派的名家挑战,不过几个月,连伤各派掌门,连其时赫赫有名的武当掌门天禅道人也伤在他剑下,而江湖中竟无人识得其来历。不但无人知其来历,就连他那剑法也从未有人见过,只知那剑法有时沉稳,有时灵动,有时迅捷,有时诡异,当真是通天彻地之能,鬼神莫测之机。这也就是那孙武剑法初现江湖的事了。这人与各派名家比试,接连几个月下来,无人能当其锋。比试之时,对手问他姓名来历,他只道是鬼谷门人,所用剑法乃是孙武。”
柳茵道:“鬼谷子乃是东周奇人,号称其才无所不窥,诸门无所不入,六道无所不破,众学无所不通;只是这一门传承如此之久,却当真匪夷所思。”
柳如风道:“鬼谷子不世奇人,名满天下;只是要流传至今,也是不能;昔年王禅居于鬼谷,称鬼谷子,难保不出现第二个王禅,且还是个武林高手,隐于鬼谷,以此自居;毕竟这鬼谷不是你王禅家的,许你待的,就不许旁人待的?其实这事只要问一问白兄,自然知晓。”
柳茵点头道:“照你说来,这人习得孙武剑法,竟是天下第一了?后来又如何。”
柳如风道:“那时黄老伯武功未成,虽有心,却始终未有与鬼谷门人交手的机会;然而天下之大,不乏藏龙卧虎之辈,要说天下第一么,嘿嘿,孙武虽强,怕也没那么容易。”
柳茵暗道,你这般说,定是那时连黄恩公也非此人对手了。只听柳如风继续说道:“那人震动江湖,未逢敌手,大有天下谁能与之相抗之意,终于找到了少林门上;他孤身一剑上少林,如此风采,确是令人钦羡;那时少林早已严闭门户,绝不允其他人进入,江湖上有人不免怀疑少林虽武林正宗,泰山北斗,怕还是敌不过鬼谷门人,失了面子;然而自此以后,那人就从江湖上消失了,正如其突然出现一般。有传言说那人武功虽强,终究还不是历经千百年传承下来的少林对手;也有人说少林倚多为胜,那人只身难敌,被少林杀了;江湖上传言种种,却始终没有明确的说法。然而那些说少林靠人多取胜的多是早前败于孙武剑法下的武林人士,这人心当真歹毒得紧。”柳茵却想起那日柳吉荣身亡,镖局众人不告而别的事。
柳如风又道:“十四年前,不,该是十五年前,却又出了一个人,此人亦自称鬼谷门人,所使亦为孙武剑法,然而江湖中人称其为鬼叫门,正所谓晴天遭霹雳,夜半鬼叫门,此人自现江湖以来,滥杀无辜,作恶多端;他武功虽强,却从不找武林中有名的高手麻烦;说来也巧,此人初出江湖,就遇到黄老伯,那时黄老伯武功大成,可说是震古烁今;那人初出鬼谷,遇一行路人家,妄图抢人钱财,恰被黄老伯撞见,两人交手之下,那人不敌而逃,那时黄老伯不知此人日后会惹出许多风波,否则也不会容他从容遁去。你猜猜黄老伯那时所救的是什么人。”
柳茵惊道:“莫非,黄恩公那时搭救的就是先父。”
柳如风道:“不错,柳老伯正是那一年入京取回轮回典。后来黄老伯与柳老伯相谈之下,竟都曾师从王学,是以黄老伯知晓轮回典一事。”
柳茵暗道,莫非他竟知道轮回典中奥秘,却不发问,只待柳如风接着讲。
柳如风却不再提黄柳两家之事,又讲到:“那人此后在武林行下那无尽歹事,我也不细说了,江湖中人大多敢怒不敢言;那人武功高强,少有人是其对手,又在江湖上招揽了一群奸恶之徒,耳目众多;那人又向来不招惹比他厉害之人,是以往往能制服他的,却也不去管他。黄老伯听闻他的恶行,几次去找他麻烦,却被他闻得风声,早早避开了。一时间,武林中人人自危。其实以江湖中人之力,铲除他也不是不能,人人只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尚有大多人仍对二十年前那位鬼谷门人极为忌惮,生怕惹出更大的事来;如此行径,却也与助纣为虐无异。然而所谓善恶有报,恶贯满盈也就如此,那人作恶不过一年,江湖中出现了一个少年。那时是早春之时,那恶人正与一众奸徒在园中饮酒作乐,大地回春,花香满园,可怜了这一番大好光景,只听得门前有人吵闹,看门的在喝问什么人,只听得有人答道,我叫白云生。那话声虽不响亮,却传到每一个人耳中,那恶人正举杯欲饮,手却停在半空,竟呆住了。只见院门洞开,从外面走进一个少年,呵呵,那就是你白大哥白云生了。那恶人见了白兄,脸上堆出笑容,抢步过去握住白兄的手,连连对他那些爪牙道,这是我的好兄弟,叫白云生。白兄却只是道,师傅听闻你冒鬼谷门人的名讳,为祸不浅,要你立即回归鬼谷;那恶人脸现惧色道,是谁知会他老人家的。白兄却只是瞧他,并不答话。那恶人忽然退身抓起长剑怒道,白云生,我是看着你长起来的,你可不要欺人太甚。他手下奸徒见他畏惧,一时间也无人敢上前。白兄说道,师傅嘱咐,看你长年服侍师傅及师兄的份上,你肯回谷,便放你一条生路;你若不肯,便将你毙于剑下。原来那恶人竟只是鬼谷的一个仆人。那恶人大笑道,老头子从不出谷,丁若水已死多年,你一个毛头小子却也想来教训我。白兄回道,没想你忠厚老实,一出谷便会如此模样。话一出口,剑已随人冲了上去,一出手便是疾风剑。那恶人只道白兄年纪尚小,却未曾想到他已习得鬼谷武学精髓。两人交手之下,那恶人立处下风,于是嘴中连连求饶。白兄却不加理会,只十八招便一剑洞穿那恶人胸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