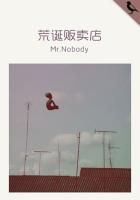且说,李君正要为池县县令吴良的失职、行贿动怒,只听得郡府外一片骚动。“何人喧哗?”李君问道。听到李君问话,郡首府管家张林走进会议厅道:“回禀老爷,是几个不懂事的百姓喊冤,打扰您公务了,我们马上把他们赶走。”李君听后脸一沉道:“嗯?对百姓的冤情不闻不问,对民间的疾苦置若罔闻,这是什么态度?”“大人教训的是。”张林唯唯地道。李君看了看吴良道:“这次过失先记下,你先回去,下次再犯数罪并罚。”吴良连声说道:“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便要退出。“把你的东西拿走。”李君冷冷地说道。“这些东西是孝敬大人您的。您看……?”吴良试探地道。“拿走!”李君训斥道。吴良无奈,只好将礼物原封拿走。
“凤郡的问题大了。”一个闪念在李君的意识中一闪而过。“升堂。”李君对张林道。
随着李君的一声吩咐,凤郡大堂之上三班衙役迅速排列齐整。李君坐在大堂上传令带进击鼓鸣冤者。十几个凤郡百姓被几个差役带到堂上。“跪下!”众衙役喝道。李君扫视了一遍下跪的百姓。看到里面多数为老者,便道:“请起。”众老人不解缘由,故不敢起来。“请起,请坐。”李君再次补充道。众衙役搬来了椅子时,十几名百姓才恍然大悟,受宠若惊地坐下。
“乡亲们,你们是哪里人氏,有何冤屈?”李君和蔼地道。
一位看似德高望重的老者站起来道:“禀大人,我们是凤郡各县的百姓代表,我们来……”说到这里,老者欲言又止。
“但说无妨,请坐。”李君道。
“我们来状告……状告……草……。”
未等老人说完,管家张林怒斥道:“大胆,竟敢在新任郡守大人面前胡言乱语,你想造反吗?退出去,砍了!”
“嗯?”李君吓住张林,继续问道:“没关系,但讲无妨。”
老者见状,忽然似犯莫大的罪行一般,跪下哭道:“小民糊涂,小民知罪,小民冒犯了草大爷,小民下次再不敢了。”
“斩了!斩了!你们TMD都是聋子吗?”张林吼道。
两个刀斧手进来就要将老人带走,李君怒喝道:“谁敢?”
此时,李君似乎明白了什么。他继续和蔼地对老人道:“老人家,刚才我的手下冒犯了您,我向您道歉。请您稍稍休息,咱们一会再聊。”说完,李君愤怒地一拍惊堂木道:“大胆的张林,跪下!”
张林闻听,不服不忿地道:“哎!大老爷,你让我跪下吗?”
“不是你,还能有谁?”
“我这可是为你好!”张林指着李君的鼻子道。
“看来你蛮横成性,历任郡守拿你不得。今天我就要拿你。”李君愤怒地道:“革去张林郡府管家一职,杖责三十,赶去郡府,永不再用!”
众衙役平日被张林欺压地有苦难言,一个个只愁无泄愤的机会,今天闻听李君之令,纷纷走向张林,要将其绑缚。
“你们哪个敢?”张林吼道。
班头陈杰走到张林面前,不容分说将一记耳光狠狠地摔到张林脸上。张林瞬间鲜血迸出口腔。
陈杰道:“死到临头还敢撒野,绑了!”
众衙役将张林五花大绑,押到堂口。“弟兄们,报仇的机会来了。别惜力气,揍他!”一个衙役高喊道。
张林此时才知道,新来的李大人乃正人君子,绝非和他同流合污的贪官恶棍,只恨自己平日作恶太多,将一府衙役得罪殆尽。此时,谁还能手下留情?
衙役们将张林按到堂口,两名衙役放下手中的水火棍,接过其他衙役递过来的另外两根水火棍。
张林看到衙役的这一举动,顿时吓得脸色苍白,五官挪移。他高声苦苦哀求:“老爷饶命!弟兄们,平日里我做了得罪大家的事,我不是人啊!看在咱们同僚的份上,手下留情啊!”
看到这一幕,李君全明白了,暗道:“今天,我饶他不得。”
“打!”李君一声令下,并将一根令签扔到地上。
只见一名衙役高高举起水火棍,狠狠地砸在张林腿上。再看张林一声杀猪似得嚎叫后,鲜血已浸透裤腿。这一棍,就将张林的两个膝关节打得粉碎。另一名衙役愤怒地举起水火棍,他怒火翻腾的眼睛如同看到恶魔一般,恶狠狠地砸下。这一棍正中张林的后背。“哇!”一口鲜血从张林口中涌出,已无力气哀嚎。这一棍下去,张林的脊椎骨随之一分为二。将张林打成这等惨状,仍未泄去衙役们的愤怒,前一名衙役再次举起水火棍,泰山压顶般砸下来,正押到张林的肩胛骨。由于用力过猛,张林的肋骨随之震断数根,其中一根扎穿心脏,当场毙命。
“禀大人,张林被当场杖毙!”衙役们禀道。
坏菜!出人命了。一个不祥的念头闪现在李君意识中。可他又一转念,这不是现实世界,凭我现在的地位,别说打死个管家,就是打死十个八个县令也是顺理成章的。再说,现在正是我表明立场的时候。
想到这里,李君道:“干得好!这等恶人,留他不得,拉出去暴尸荒郊。”
众百姓见到这一幕,纷纷跪倒高呼:“青天大老爷来了!”
李君再次道:“乡亲们请起,请坐。”
众百姓再次落座后,李君问道:“有何冤情,请讲。”
那老者擦了擦眼泪道:“我们是凤郡周边县的百姓,就高告刚才您打死的那个管家,还有草上飞。”
“请详细讲讲。”李君问道。
老者长叹一声,道出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这个郡的百姓多年来饱受三股势力的压迫和欺诈。这三股势力是:官、商、黑。所谓“官”就官吏为了共同的利益而结成的关系网、利益同盟。他们一方面为了自己的骄奢淫逸,另一方面为了自己能够有晋升所需的钱财,无休止地剥削百姓。所谓“商”就是散布在一郡中的大小商贩。他们为了利润的最大化,弄虚作假、以次充好,肆意操纵物价,搞得百姓民不聊生。所谓“黑”就是黑势力。他们惯用为人不齿的一切手段,打家劫舍、欺男霸女、无恶不作。这三股势力往往又是沆瀣一气,为了各自的利益互相勾连的。
这个草上飞在凤郡一带亦商亦盗。此人在凤郡城和周边县经营着数家饭店、当铺、钱庄等买卖,可谓家赀万贯。此外,草上飞仗着自己的财力,勾结官府、黑心商人和黑势力,尤其是和刚刚死去的张林关系密切。他二人在凤郡一带打家劫舍、欺男霸女,无恶不作。每隔三五日,他们便在凤郡和周边县乡寻觅合适的女子,并将其抢回自己的窝点,百般凌辱。多少女子不堪凌辱寻死自尽。
上个月,草上飞、张林带着一帮打手在凤郡城的集市上闲逛。他看到一个卖酒的老人,便走过去问卖的什么酒。老人道:“正宗的烧刀子酒。”这草上飞打开酒桶盖闻了闻,又拿起酒勺,盛了酒尝了一口。突然他将酒吐到地上大骂道:“敢拿这样的马尿哄你家爷爷,什么烧刀子酒,明明是马尿!”老人辩解道:“哎?这是自家酿的烧刀子酒,祖上传下来的配方,怎么会是马尿呢?”一句话激怒了草上飞。他愤怒地道:“什么?你还敢顶嘴?今天爷非治治你。给我上!”数十个打手将卖酒老人抬起来,将头插入靠墙的一个酒瓮中,用力打老人的肚子。没打几下,老人当场身亡。打手看到老人死亡,便将老人的尸体,拔了出来,在张林的吩咐下扔到了街旁,并砸了老人的酒瓮,提起那两桶烧刀子酒,扬长而去。
老人的子女自然不会善罢甘休。他们将张林和草上飞告到了凤郡府,谁知上任郡守竟说他们诬陷,没有审问半句,便以扰乱治安罪把他们收监了。
此次闻听郡里换了新郡守,众百姓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前来郡府击鼓鸣冤。
李君听罢,对乡亲们道:“我大概知道了。请乡亲们先回去,我调查一下此案,一定还大家一个公道,让大家过上太平日子。”众人听罢,对李君千恩万谢后,离开郡守府。
送走了乡亲们,李君回到后堂的书房中。他感到凤郡的问题比想象中的更严重。他传来班头陈杰道:“草上飞的案子你们是怎么办的?”那陈杰忙跪倒道:“大人息怒,恕小的直言。前任郡守不允许我们办草上飞的案子,还发了话,谁和草上飞过不去,就是和他过不去。我们不敢动他啊。”“前任郡守现在何处?”李君问道。陈杰道:“因为查出了贪污罪,被处决了。”穿越到帝国时代游戏中的李君,已经知晓这里的官员只要查出贪污罪,不计所贪数量、种类,一律定为死刑。也就是说,贪污一丝一毫和贪污万金的,一旦查出都是一个结果——死。
“传本郡谕:自今日起,全郡官员通力破获、捉拿草上飞。”李君道。班头领命,刚要走出书房草拟命令,李君又道:“传本郡牢头。”陈杰答应一声,走出书房。
不多时,凤郡牢头赵彪走进书房。赵彪施礼已毕,李君道:“前翻状告张林和草上飞的人,还在牢里吗?”赵彪道:“回禀大人,在牢里。”“放人”李君道。赵彪领命,走出书房。
不能在房间里宅着了,得出去看看。说不准能发现什么线索。想到这里,李君向外高喊:“陈杰!
”陈杰问声走进书房施礼道:“伺候大人!”
“全郡哪个县最贫困?”李君问道。
“大人,这里最贫困的县就是池县了。”
“明天一早跟我去池县。”
“是!我去准备”陈杰答道。
“准备什么?”李君问道。
“准备大人的仪仗、卫队,通知吴良迎接大人。”
“只有你我二人去,不通知、不准备、着便装,悄悄去,悄悄回。”
“大人,这不安全吧?”
“我刚到凤郡,谁认识我?有什么不安全的?就这样办吧。”李君果断地说道。
陈杰无奈,只得照办。
翌日清晨,李君早早起床换上便装洗漱已毕,用罢早饭。班头陈杰一身便装走进后堂道:“大人,一切准备齐备,不知您何时启程?”
“马上启程。”李君说罢,在陈杰的陪同下,走出府门,拾级而上,来到了城镇中心门口,打马奔向池县。
天近当午,二人进入了池县界。
”站住!抓住他们!”二人忽然听到后面一阵喧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