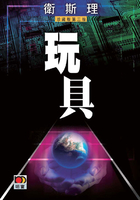据说李烈钧在南方起事讨袁,绥远都统急电后大套的“花头勇骑兵团,横贯鄂尔多斯高原从五里村过黄河,然后从河曲入关护袁。这个团全部骑花马,人们俗称”花头勇。上千色彩绚丽斑驳的花马咴咴嘶鸣着衔尾从山上翻了下来,花马上的官兵提刀挎枪好不威武。杨旺、盛生贵早接绥远都统的飞文,在村口恭迎。
花头勇骑兵团的团长叫梅上贤,足蹬黑皮靴,头戴火红狐皮帽,傲慢地在马上欠身道:我那两万两烟土军饷,你们给我筹划好了,我就当是过路。要是没有筹划好呢,我这团人马就在这住下了。我瞅着这街面还繁华,怕是误不下吃喝。杨旺壮着胆子说:都统飞文令我和盛局长筹划一万两烟土,这两万两烟土怕是一时难以筹齐。梅上贤摇晃着马鞭子说:那就慢慢筹,反正我也不着急。要是误了我的军务呢,我就砍人。盛生贵吓黄了脸说:一定筹齐,一定筹齐。梅上贤说:这还算句人话。
他挥了挥手,“花头勇们就在街面上号房子住下。梅上贤和他的团部住进了垦局的小学校里,金子、国贤早把学生们放了假,他二人也都各自回了家。一时五里村街面上兵吼马叫,遍地都是马粪马尿,家家户户都浸在马味中。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全躲进了山药窖里,怕被”花头勇们摸捞住。四红楼的粉头们忙着接待“花头勇们,”花头勇们又想白干,便打闹了起来。要不是梅上贤又放枪又抡马鞭子驱赶,四红楼的粉头们全都得成了筛子。催粮的,要油的,捉猪的,绑牛的,五里村一片哭喊乱叫。仅一天闹腾下来,五里村的乡亲们就有了共同的心声:快把这些爷爷们打发走!
俗话说请神容易送神难,不请自到的神神那就更是难以发送。梅上贤开口就是两万两烟土,这是多大的气魄,多大的手笔,多大的吃口窟窿!人家到底是从富庶的后大套来的爷爷,不像河对面河曲县那些穷神,像三先生和刘鬼头之流,几顿酒肉外带粉头就能打发服帖。后大套是甚地方?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瞅瞅这兵马,人家吃过见过!这回见到真神了吧?两万两,嘴上连个磕绊都不打!这是十五万块大洋啊!洋烟是好种的?光看见罂粟花好看了?哪知这是血浆子泡出来的!洋烟这玩意儿太金贵,哪是土头巴脑的庄户人侍候得了的?心疼也没用,快交给爷爷们吧,快把爷爷们打发走吧!
黑界地的乡亲们被乌黑的枪口逼着,马刀抽着,吊在二道梁上思考着,终于迸发了交烟的积极性。翻箱倒柜,掘地三尺,仅仅两天的时间就凑齐了两万两烟土。这让梅上贤大吃一惊,他原以为得死几十人,烧半条街才能筹划得差不多呢!他感到低估了黑界地的潜力,好不容易来一趟,仅筹划了区区两万两烟土,这不是犯傻是甚呢?当时说要四万两烟土,不也是上嘴皮碰下嘴皮的事,费甚劲呢?要有四万两烟土,就能再拉起一个团,到时我就是师长?天啊,我咋把师长误了呢?!他懊悔得直拍大腿。副官告诉他,杨旺、盛生贵在四红楼摆好了饯行酒,梅上贤火顶脑门子骂:我日他们的祖奶奶,这是想撵爷爷走哇!告诉狗儿的们,爷爷在这扎老营了!
一听梅上贤要在黑界地扎老营,杨旺、盛生贵不禁面面相觑,听到讯的乡亲们也都面如土灰。金老万像走磨道的驴,在屋里转着弯儿说:真把鬼引来了!真把鬼引来了!我早就说过,早就说过!这次为“花头勇筹烟土,是按地亩摊的,金老万不动窝就被抢走了四千两。破了这么大的财,头上的灾星还不见动,金老万眼里也蹿出了火星子。赵良说:老掌柜,咱的烟藏得严实,不怕狗儿们的犯抢!金老万说:这还叫庄户日子?我琢磨着,咱们早晚让这烟给带害了。有甚法?明知是黑窟窿,也得在里面瞎扑腾!老张头说:咱们再忍忍,兴许狗儿们的就走了。咱们多当点心,把门户看严点!金老万说:也只得这么办了。甭想跟人家来硬的,咱这十几条快枪经不住人家打。别说”花头勇,连骑警队都近不上。以后这庄户日子,越来越艰难了。赵良说:老掌柜,我看开了春你得把院墙加固加固,把角处得建起放枪的楼子来。咱惹不起官府,得防防土匪甚的。金老万说:我不怕土匪,土匪叼人还有个数。这官府,就像一条会吃人却又没血肉的狼,我也说不清究竟是个甚东西。赵良说:你不知是和甚东西打交道,它却又想咋吃你就咋吃你,你说怕不怕?老张头说:咋不怕?说杀你就杀你,就像在滩上打兔子。
金老万说:我刚才眯了一小觉。又梦见鹏举娘冲我龇牙咧嘴地吼:快了!杀人放火的日子就要到了!这狗儿的是不是在咒我?是不是想变成墓虎害我?不行,我把狗儿的刨出来烧一次,再把坟地倒倒?老张头说:你这是亏心,自己闹腾自己呢!倒甚坟地?烧甚尸骨?有甚血仇,值得你把人家再杀一次?你明天让鹏举上次坟,多烧几张纸就行了!金老万说:听你这个老王八蛋的!说起鹏举娘,你就冲我不依不饶的?你咋不想想,她狗儿的想断我的根毁我的家业?咋?我还办错了?老张头拍拍金老万的胸脯子说:对错这里面知道。我保证再也不提半个字!
赵良说:黄秃子昨天找我,说花头勇有个姓邵的连长,想给咱们倒腾十几条快枪,五两换一支。老张头说:这价格合适,我给刘鬼头倒换那几只比这不便宜。金老万问:把握不?赵良说:我吃不准。黄秃子这种人咱有数,可姓邵的那人真吃不准。这邵连长说着话,眼珠子骨骨碌碌乱转。我跟他哼哈了一阵。金老万说:这就对了!甭钻进人家的圈套,贪小便宜准吃大亏。像咱这种人家,黑眼算计咱的人太多了!怕是咱瞪着大眼都有提防不到的地方哩!
梅上贤执意不喝饯行酒,杨旺和盛生贵也没了办法。一团“花头勇住在地面上,又不大讲究军法,光是枪走火,就够黑界地的乡亲们喝一壶的。所有的店铺都封了门,”花头勇们就拥进了庄户人的炕头上。几乎家家炕头上都供着几位爷爷,庄户人们给他们好吃好喝好招待。爷爷们还隔着门缝往外撒尿,而且动不动就掀桌子。村子里一片鬼哭狼嚎,梅上贤对这种声音非常满意,他说:住兵就得有个住兵的样样,让****的再给我喝饯行酒。
杨旺和盛生贵只得再求梅上贤再说个准数,说是不敢误了护袁讨逆的军机大事。梅上贤伸出了两个手指头,冲脸面大变的杨旺和盛生贵说:再凑两万,我立马就过河!当着梅上贤的面,杨旺,盛生贵大吵了起来。杨旺说筹烟是烟局的事,盛生贵说烟长在地上,不是垦局的事是谁的事?杨旺骂盛生贵自掌烟局,把黑界地搅得周天寒彻,一片肃杀;盛生贵骂杨旺沽名钓誉,中饱私囊。杨旺骂盛生贵阉党,盛生贵笑杨旺没色的王八。俩人越骂越凶,一阵捋胳膊挽袖子,幸好没动起手来。梅上贤说:我咋瞅你俩也没一只好鸟!我就打你俩的大户,你们把这些年吃喝黑界地的多少给我吐出来点,要不我就把你们这对王八蛋全吊在二道梁上!说着就要吆喝马弁、卫兵吊人。
杨旺说:梅团长息怒。我不过是个穷文官,吊死梁上又能榨出多少油?盛生贵说:我上冻时才当局长,好不容易收点烟全都上缴了。我算甚大户?杨旺说:这黑界地要说大户当属金老万!这狗儿的肉头!盛生贵也说:烟全在金老万手里!他光烟地就好几百顷,不打他打谁?杨旺说:快把狗儿的打了!盛生贵说:他狗儿的连自己的婆姨都杀,快把这祸害除了!梅上贤冲他俩啐道:呸!你们把我当成甚?想借爷爷的手杀人,做你们的美梦去吧!杨旺说:不动金老万,这黑界地确实是再难筹两万两烟土。盛生贵也说:杨督办说得不差。我们委实是为梅团长着想。
梅上贤说:你们狗儿的不是设好套让我往里面钻吧?杨旺和盛生贵连说:不敢,不敢。梅上贤说:你俩要是敢把我当猴耍,我就把你们给活剐了!杨旺说:我咋敢了?盛生贵说:你得给金老万动真格儿的。那狗儿的嘴硬,一般刑法不管用!梅上贤哈哈笑道:我就喜欢嘴硬的!我拉杆子三十年,甚茬没修理过?你们打听打听,后大套的狼见了我敢有脾气不?你们听说过狼怕花马的不?告诉你们,后大套的狼见了花马跑都跑不及!杨旺说:梅团长的队伍真神勇!梅上贤说:说甚我也要见识见识这个金大掌柜!我这辈子就喜欢英雄!
打发走了杨旺和盛生贵,梅上贤找来了邵连长,邵连长说:金家大院的人不上套,黄秃子也说金老万是只老狐狸。梅上贤说:我在后大套就听说过这老狗儿的。这可是只大肥鳖,我说甚也得把狗儿的咬下一块来!邵连长说:黄秃子说金老万是惜财不惜命的主儿。你要是挖不到他疼处,屁也拿不出一个。梅上贤说:我早摸到了金老万的疼处,就是他那个大烟鬼儿子。邵连长转着眼珠说:每天绑着去脱坯背砖,他疼甚?梅上贤说:这才是大疼哩!我说明白了不?邵连长说:我明白。梅上贤说:你也跟我一年了,咋就办不成个明白事?邵连长说:我这次一定办成件明白的。
第二天一大早,邵连长就带着八匹快马埋伏在鹏举平时脱坯的砖窑附近,可日上三竿还未见到鹏举的影子。正思谋着撤兵,却见鹏举被绑着从河滩上徜徉而来,国栋跟在他的后边。邵连长打了个手势,八匹快马就包抄了上去,还未等国栋醒过味儿来,几只快枪就抵住了胸口。邵连长一把将鹏举揪上马来,一声呼哨,八匹快马踏雪而去,眨眼跑了个无影无踪。
国栋踉跄着跑回金家大院,院内立即一片惊慌,赵良、国贤、老张头也闻讯赶来,所有的把式匠都操起了刀枪。赵良问国栋:你看清了是那个姓邵的连长?国栋说:绝对没错!国贤说:认准人就好,去告这抢匪!老张头说:你还是去回家看书吧!这是告的事?我思谋着,这次要响枪炮了!金老万稳住神说:人家正架好枪等咱们哩!咱这几十号人马,够不够人家马蹄子踩的?国贤说:官军咋成了绑匪?我就不信咱们告不赢他!还讲个军纪国法不?金老万说:我娃,这就是你读的书?我看你也该去砖窑背背砖了。赵良说国贤:你快去给金子说些宽心话去吧!这种事,听不成你的!国贤悻悻地去找金子。金老万说:咱也别像热锅上的蚂蚁乱窜悠,就等着来讯吧!赵良说:黄秃子跟狗儿的邵连长熟,我去摸摸他的胃口?金老万头说:我估摸着姓邵的没这个胆,他也做不成主。赵良说:你是说姓梅的?金老万说:不是他还有谁?咱们耐心等讯吧!这不是着急上火的事。说不着急上火,金老万还是一夜未睡,早上饭也没吃。天快晌午,国栋跑进来说:姓梅的来门前找你。金老万问:带多少人马?国栋说:就他狗儿的一个。咱把他逮住换鹏举?金老万瞪圆眼珠子骂国栋糊涂,然后起身去迎梅上贤。梅上贤说:梅某不才,治军不严,骚扰了金掌柜。金老万说:这里面的事我门儿清呢!梅团长也别绕弯了,你就给我来个直截了当的。
梅上贤干笑了一阵儿说:金掌柜,你就是咋不愿听,我也得说说。你放心,小少爷在邵连长手里平平安安的。金老万斜睨着梅上贤那张红润的大脸盘说:这话我相信。姓邵的保证比侍候自个的亲大还当心哩!梅上贤说:我这人马两季没发军饷了。当兵的没饷银,还有不闹事的?这姓邵的就四处拱火,还想拿枪换烟土。我就想办他,可他****的一急,绑了小少爷还纠集了百十条枪,扬言不补发军饷就撕票。我要是硬剿他吧,这一动枪炮五里村肯定没了,就更别提小少爷了!金掌柜,这兵带不好就成了土匪,你说我这光景过得玄不玄?
金老万说:兵匪一家,这我早就知道。梅上贤说:你说我难不难?这人吃马嚼的我得操多大心,犯多大难?咱打开天窗说亮话,你先帮我应应急,把这两季的军饷糊弄着发给弟兄们,他姓邵的就得放人!这是十万白洋的借据,你要是答应借这点钱呢,我保证把小少爷白白胖胖地送回来。金老万说:我要是不答应呢?梅上贤说:那我就给姓邵的来硬的,用炮轰,用机枪扫,用火烧,用马刀砍,不管小少爷是死是活,我肯定能给金掌柜送回来。我也清楚,你一个庄户人出这点钱也不容易,可谁让咱摊上了这种事呢?金老万说:这么一折腾,我可就甚也剩不下了。梅上贤说:你可有活灵灵的少爷呢!
金老万说:钱到手你就放人过河?梅上贤说:军中无戏言,袁大总统还等着我保驾呢!再说,我还给你留下了借据。等到上面发了军饷,我一定如数奉还。金老万把那张借据慢慢撕碎说:我也不识字,看不明白这玩意儿,咱们心过心。你前脚走我后脚把十万块大洋的银票送到。梅上贤一撩袍子,抽出两把大镜面匣子枪往炕桌上一放说:这是兄弟的一点心意。在黑界地面上过日子,这玩意儿好用哩!金老万说:那就多谢梅团长了。稍有奈何,我是不动这玩意儿。梅上贤笑着起身,金老万说:你还得把姓邵的狗儿的给我砍了!我得让街面上知道,我金老万的头不是那么好剃的!梅上贤面挂迟疑,金老万冷笑道:你就不整肃一下军纪?就这么马尿一泡马粪一堆地走了?是绑票不该砍还是倒腾枪不该砍?这活口留着不是害?
梅上贤说:钱这东西是厉害!我梅某给你这个面子,把狗儿的砍了!金老万仰天大笑。梅上贤前脚走,金老万就找来了柴进文,两万两烟土换了十万大洋银票。金老万说:柴掌柜,你狗儿的等于打劫了我一次。柴进文说:现过现,我这买卖人没一点儿不规矩的地方。金老万转着眼珠子说:闹了半天,咱黑界地上全是规矩人哇!
他怀揣银票,坐上国栋的牛车去领鹏举。鹏举正在热炕头上睡觉,梅上贤说:这娃瘾可是不小,昨晚闹腾了一夜,这才刚睡着。金老万把鹏举拍醒,又把手伸进鹏举的热腿根上摸索了一阵,梅上贤说:咋?不缺甚吧?你狗儿的还怕我做害娃娃?金老万说:这是接票的规矩。梅上贤说:你也规矩吧!
金老万递上银票说:姓邵的咋砍法?梅上贤接过银票说:我要当着你和乡亲们的面军法他!我早把狗儿的四马攒蹄捆好了!金老万说:快砍了他!梅上贤说:你就看好吧!这种祸害乡里,扰乱军纪的害群之马,说甚也不能容他。军号嘀嘀嗒嗒猛吹了一气,的马蹄声把河滩震撼,不大的工夫“花头勇们列起了三个方队。黑界地的乡亲们黑压压地站满了沙梁,都伸长了脖子观望。姓邵的连长被五花大绑拖至沙滩上,刚跪下,执行军法的刽子手就骑马而至,高扬起马刀一下把邵连长的头颅给削了下来,快得让乡亲们都来不及细看。梅上贤在马上挥了挥白手套,”花头勇们呐喊奔跃着冲向河边,渐渐地消散在苍黄的黄河冰道上。
望着满地马粪马尿,乡亲们喜笑颜开道:爷爷们总算走了!并且开始评判刚才的马刀削头,经过一阵面红耳赤的争论,大多数人认为削头不如炸子爆脑花花好看。尤其是王剃头匠跑得好,枪子儿躲得也好。应该让姓邵的这没头鬼也撒欢跑,刽子手在后面抡着刀追,那才红火热闹呢!黄秃子说:你们懂个!这军法讲究的是一刀之罪,刽子手一刀砍不死邵连长,邵连长就可以砍他!乡亲们笑歪了嘴说:互相砍起来那才更好看哩!老张头说:毛都让人家刮得不剩几根了,还他妈妈的闲傻笑!乡亲们这才心疼起来。花头勇们把他们一年的辛苦都带去了!好在他们把地皮刮不去,庄户人脑瓜顶上的太阳还在,阳光普照下的黄河湾还会滋生出诱人的罂粟,乡亲们的眼前又是一片春天般的灿烂。
春风掠过,黄河文文静静地开了冻,既没叉冰坝,又没泛凌洪,咕咕嘟嘟的黄泥汤从冰缝中钻了出来,僵卧一冬的玉龙满身鳞甲就呼呼塌塌脱落了。红拐子鲤鱼不时从浊涛中跃起,在浩渺的水面上画着弧线;捞鱼鹳在浪谷波山间飞掠着,尖尖的嘴巴不时叼起小鱼,然后振翅冲上天去,满河鼓起捞鱼鹳啊啊哇哇的愉快欢叫。河滩上的苇草钻出了嫩黄的小芽,一种俗称跳儿的沙鼠在河滩的沙丘间跳来跳去,转着滴溜溜圆的小眼睛,伸着精巧的小爪子搔弄着稀疏的胡须。春风也是那样的和煦,带着湿润,带着土腥,在广袤的河滩上打着旋,钻进牛马驴羊的鼻子里,撩拨它们的春情,让它们骚动,让它们不安,让它们莫名地扬脖嘶鸣。小虫子也钻出来了,拖着星星点点的硬壳,在牛马粪****来钻去,春天也属于它们!要是老约翰还在,准会泪流满面地跪在黄河岸边,赞美主的厚爱仁慈,造物的精深博大,生命的无比强悍!
老约翰滩静悄悄的,春风像一个轻柔的少女伸出纤纤手指轻拂着国贤的脸颊,国贤靠着老约翰墓前的石马闭目小憩,一滴泪珠在他那长长的眼睫毛上扑闪抖动。不远处,王大爪子正在光着膀子挥动铁锹吭吭哧哧地切草坯,一块块草坯像晒盖儿的王八铺了一河滩。春日高悬,洒着光晕,撒着温暖。河浪喧哗,无休止地拍扑着岸陂,溅起浪花水沫,在阳光下闪着七色的光彩。国贤被黄河湾的宁静与美丽所陶醉,晕晕乎乎地欲睡欲醒。忽然,一阵呼呼的响声,打破了这动人的宁静。国贤不用睁眼就知道是烟局的小火轮游弋过来了。一下子睡意全无了,一股烦躁把他拉回到这飘着血腥味的现实中来。烟局这帮狗儿的,真在人身上打窟窿眼哇!昨晚街上那个叫球球的后生,带着七两干烟划小划子过河,走在河中间被小火轮上的探照灯罩住了。当这白炽光柱划破河面和糨糊般稠浓的夜色时,只知油点灯的球球从骨子里感到震慑和恐惧。球球拼命想使小划子摆脱这白色的光柱,还没挣扎几下,就被一阵排子枪打下水去。今天早上被河浪冲在河滩上,身上光看见的血窟窿就有七处。球球娘一头栽在儿子的尸体上,再也没有缓过气来。球球的大一下子就疯了,在河滩上拍着手跳来跳去的。黄秃子跑了过来,冲着疯笑的球球大就是一记脆响的耳光,球球大转了个圈,才揪扯着自己的头发喊了起来:种洋烟种洋烟,这回让洋烟日了吧?天老爷,地老母,我一家子都是信教行善的哇!黄秃子说:好了,好了,这老汉骂出来就好了。乡亲们也都说:火往外走就好了。球球大又趴在地上,像牛一样哞哞哭着,乡亲们这才放下心来说:哭出来就更好了。眼泪这东西最去心火。
国贤肃然地站了起来,冷冷地看着越窜越近的小火轮。小火轮的汽笛像示威似的,发出了刺耳的怪叫,几下就把黄河滩的宁静和自然撕扯成碎片。几个巡警挎着长枪站在船舷上,就像船头上的鱼鹰一样,监视着浊浪滔滔的水面。王大爪子叉开双腿,挺着腰板,哗哗地冲他们撒着尿,表达着最原始的轻蔑。一个巡警端起长枪冲他瞄划了两下喊:王大爪子,小心我把你狗儿的打碎!王大爪子打打尿噤喊:爷爷大不了不贩烟,我都圪蹴下了你还能把我的咬下?巡警在船上骂,王大爪子在岸上骂,一直骂到小火轮拖着一条油汪汪的尾巴突突远去。
国贤走到王大爪子跟前说:你招惹这群恶狗做甚?王大爪子说:我看见这群狗儿的就来气!国贤说:正经庄户人躲他们还躲不及哩!王大爪子咧嘴嬉笑说:那我就不是正经庄户人了?国贤说:庄户人就得种庄稼!王大爪子说:你就甭替庄户人瞎操心了!该种甚,庄户人自己肚肚里清楚!你和金子小姐走东家串西家忙活了一春,拦住哪家种烟了?你瞅瞅这河滩,不都是绿央央的烟苗苗?当好你们的教书先生就行了,管这烟亩的事做甚?国贤说:位卑未敢忘忧国哇!这满滩烟苗,又使多少好人家家破人亡哇!咱们哪是种地?是种害!害人害己哇!
王大爪子感到怪好笑的,暗笑自己这位未来的舅爷又上来了读书人的傻劲。他也不理国贤,往掌心里呸呸啐了两口唾沫,使劲切开了草坯。国贤也在他旁边一阵吭吭哧哧,十分卖力地切开了草坯。赵良怕他把身子养娇嫩了,就让他抽教书的空帮家里做些农活,但国贤死活不肯沾家里种烟的事,还发一些书呆子话。一次竟振振有词道:种洋烟是肮脏事,玷污了庄户人的心灵。它使劳动丧失了美好,丧失了尊严!这种话赵良似懂非懂,更感刺耳钻心,只是说:你吃的是甚?穿的是甚?
个尊严不尊严!国贤也上来了书呆子脾气,扬言要把家中的百十斤洋烟籽种全倒进灶锅里煮熟,气得赵良抡起二股叉就往他的肩上拍打。小姐对国贤说:你去帮奎子切些草坯吧!这娃要盖房,秋天好娶你的妹子。
国贤这才来到河滩上切草坯,领略劳动的美好和尊严。他哗哗地淌着汗,手上也被锹把子搓起了泡,被汗水蜇得钻心疼痛,不禁吸溜着气说:惭愧,惭愧,多日不事农桑,我一个庄户娃手上竟钻出泡来。王大爪子说:你散散筋骨就行了,累了就歇歇。国贤说:我刚才在老约翰的墓前眯了一阵,竟梦见老约翰跪在黄河边上为黑界地祈祷呢!王大爪子说:我咋梦不见他?我最恨洋教士了,杀了我大我娘还占了我家的地,逼着我从小就当讨吃子刮野鬼!要不是碰见金掌柜我能有今天?金掌柜把这老约翰滩租给我种洋烟了,我把房建在沙梁梁上,往下一看全是我的烟地!国贤说:连这么块干净地方都没有了!
他刚要发感慨,二女子提着米汤瓦罐送饭来了,她的身后还跟着一个半大小子,这是黄秃子的独生儿子跑跑。跑跑长得文文静静,又勤快又乖巧,聪明相一眼就能看出来。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家里,是个谁见谁夸的好孩子。就连黄秃子都说:我这辈子是甚恶都做了,可我这娃良善的是个小天使哩!国贤问跑跑:你咋来这河滩上了?跑跑说:金子老师让我找你哩,说是有急事。国贤一听,立马就要往学堂去,二女子拉着他说:哥,你咋也要吃喝上一口!国贤说:不了,我还有急事呢!王大爪子说:你就让他去吧!你留着他,他也吃不下。二女子只得让国贤匆匆而去。
跑跑说:奎子哥,我帮你切草疙瘩吧!王大爪子说:这活苦重,你吃不下!跑跑说:前两年我就切过草疙瘩,一点也不咋!二女子拉着跑跑的手说:你是洋学生,咋干这些粗活?听我哥说,你夏天也要去考河曲中师学堂?跑跑说:我还不知考中考不中呢。要是考中了,我娘甭提多高兴哩!王大爪子好奇地问:听说你会说洋话?跑跑说:小时候,我大常不在家,老约翰主教看我可怜,就把我留在洋堂里。我跟他学过一些洋话,这几年也记不住甚了。王大爪子说:还是忘了好,要不你就不算中国人了!跑跑说:我大我娘都是中国人,我咋不是中国人?王大爪子说:你瞅这小人人,多会说话!二女子说:跑跑,快去温习你的功课吧!考中了,给你娘争口气!跑跑答应了一声,蹦跳着奔向了沙梁。
王大爪子呱呱唧唧地吃着饭,二女子问:香不香?王大爪子说:你做的,咋都香!二女子俏皮地说:才不是我做的呢!王大爪子说:丈母娘做的,更香!二女子刮了一下他的脸皮说:没羞臊!你连房都没起哩,还丈母娘?王大爪子说:我这不是接种好烟亩,就忙乎起房?二女子说:我恨天过得慢哩!一下子到了秋天多好!我在这滩上养猪,养羊,养鸡,还要养耕地的大牲口!王大爪子说:你说了半天养这养那,就没说给我养娃!二女子用手蒙着脸说:你灰说甚哩,羞死人了!王大爪子说:咱俩灰说的还少啊!你眼见着要坐轿了,却秀气起来了!二女子说:我就是要秀气!到那天,给你一个整西瓜!王大爪子抱住二女子说:你知道我现在在想甚?二女子闭着眼,偎在王大爪子的怀里,一只手在他的胸脯上摸来摸去,赞叹着说:你真结实,就像一头大犍牛!王大爪子紧紧拥着二女子,忽抽着嘴唇说:我在问你我想甚?二女子已强烈感受到他的威武粗壮,她躲避开那逼人的东西,哧哧笑着说:瞅你那东西,都要把裤裆撑开了!你想甚?还不是想把这东西戳进人家的肚肚里去!奎子,真坏死你了!你那东西好怕人呀,就像驴的。王大爪子并紧双腿说:你瞅,我把这东西摁老实了。二女子说:你可不敢把它窝巴坏了。王大爪子说:它是纸糊的?哪有那么娇嫩?我就在想,你那东西是甚样样?是不是像洋烟花那样鲜嫩好看?二女子在他的脑瓜顶上轻轻拍击了一下说:你咋这样没成色?比个甚不好?我告诉你它的样样吧,它像桃花儿、杏花儿、山药花儿、胡麻花儿、苦菜花儿、山丹花儿、菊花儿、喇叭花儿,甚花儿都像,就是不像毒透顶的洋烟花儿!王大爪子说:我咋就盼着洋烟开花呢?二女子说:官府比咱还盼呢!烟刚出苗,小火轮就把河封了,到时甭又来哪路爷爷呢?王大爪子说:那咱种这洋烟闹甚呢?二女子说:我大说了,咱庄户人是在刀尖尖上刨食呢!这叫甚窝屈日子?盼洋烟开花又怕洋烟开花。
在庄户人期盼和心悸的焦虑之中,绿森森的五月悄悄降临了黄河湾。满滩罂粟开始抽出了花骨朵,再有一场透雨一催,花儿会竞相开放,黑界地将变得无比妖。
庄户人开始盼雨,夜晚揪心地望着满天星斗,白天对着红艳艳的太阳叹气。人们的心不大不野,只求一场雨,救救这些烟苗。老天爷,你主宰万物一切,你不管我们这些可怜的庄户人谁来管我们呢?就一场雨,一场!可老天爷根本不理睬庄户人的央告,照样每天把狗儿的火盆子挂在天上,无情地烤灼着黑界地。土地龟裂了板结了,表层成了一脚踩上去扑地荡起一股黄烟的面缸地。烟苗子的枝叶打起了卷,含苞欲放的花骨朵又枯萎了,而洋堂地是地地道道的水地,支渠遍布,阡陌交错,渠水汩汩地流淌着,上百顷烟地的罂粟花开得花团锦簇,吸引着花蝴蝶,小蜜蜂。渠内渠外俨然两个世界。
黄秃子率着洋堂卫队的人每天巡渠,常发感慨:咱中国人真是瞎活,连种地都种不过洋人。我是彻底宾服洋老爷了!就连赵良也不得不佩服老约翰、默里这些洋教士是种庄稼的好把式。他管辖的几十顷滩地就与洋堂地毗连,当年老约翰主教曾与他和金老万商量共同挖渠的事,却被金老万一口回绝。金老万对老约翰道:你懂个!河滩地是下湿地,挖渠做甚?老天就是一滴雨不下,照样收庄稼!真他娘的稀罕,你倒教我种庄户了?你不是装大肚子驴是甚?当时,老约翰除了祷告上天,又能说些什么呢?
赵良眼见着绝收,急得火烧火燎,就想借用洋堂的渠水。巡堤的黄秃子说:默里洋老爷说了,借水可以,先交五万块大洋。赵良对金老万一说,金老万红了眼道:我就不信黄河水也是洋堂从外国带来的!他默里凭甚白用中国的黄河水?!金老万自从被梅上贤敲走十万大洋后,庄稼火就有些搂不住了。眼见着今年的烟亩绝收,更是急火攻心;这几十顷烟亩一绝收,家业可是说败就从根上败了。鱼死网破,金老万豁出命来也要搏一搏。一声令下,藏在柴火垛里的两门土炮剥去了伪装,炮口原先就对着河滩上的洋堂。火药填足,就等着点火呼啸了。他冲老张头说:枪一响,你就开炮。管它是洋堂,还是垦局烟局,打着哪儿是哪儿!老张头说:你就放心开你的枪,我这儿误不下事。
金老万率着提刀端枪的三十多名把式匠和伙计,气势汹汹地朝洋堂大渠扑去。一路上又卷进了几十个提着锄头铁锹的佃户,浩浩荡荡足有百十人。金老万想:咋就是咋了,老丹丕勒抗垦也不过是这么个阵势。太阳毒辣辣地烤灼着大地,一切生命都蔫蔫的,黑界地在阳光的照耀下发出炫目的晃颤,显得是那样的寂寥和苍黄。缕缕水气被阳光拔起,像条条五彩的小龙摇头晃脑向天空飘去。金老万说:天,老天爷收地气呢?庄户人都感到大难临头般的森然。在庄户人眼里,地和人一样,也是靠一股气撑着。地气一散,那便是寸草不生的死地。金老万冲赵良说:咱活出活不出,全看今天的水借成甚了。水要是能浇上,这地还有救。赵良晃着手中的大片刀说:我今天是豁出这一罐子血了!国栋说:我这枪子儿专爆默里的脑花花!金老万热泪盈眶地说:我早说过,你们赵家的人品质好!我早说过,我早说过。人和人过甚?是心。
金老万原以为洋堂卫队的人马枪炮全聚集在渠背上,这里将会爆发把空气都撕成碎沫的恶战。可想不到长长的渠背上就跪着一个手执十字架祈祷的默里。一种肃穆渐渐笼罩了火气冲天的金老万,他不禁把闪着烤蓝的大镜面匣子枪插回了腰间。乡亲们也没见过这样等着挨刀的牲口,手中的刀枪都垂了下来,呆望着跪在渠背上的默里。
田间静悄悄,默里那浓郁的充满晋陕口音的中国话在天空飘荡:主,仁慈的主,我看到了你,我亲吻你!我们充满罪恶,我们将承受一切苦难,默默地承受人世的一切不幸。承受不幸将洗涮我们的罪恶,涤荡我们身上的污垢!在苦难的洗礼下,我们美丽,我们纯洁,就像刚从产道中滑出的婴儿!主,你看到了,你笑了,你那每一条细细的皱褶都洋溢着仁慈,都闪烁出宽厚,都跳动着无所不在的包容!你包容,胡燕可以觅到小虫,瞎眼的麻雀飞进了谷仓,折断翅膀的秃鹫一头扎在死马的背上!黄芨草盼雨水,苦菜花要开放,红橄榄要抽枝条,人间万物要生长!主,仁慈的主包容的主,你不会拒绝罂粟的美丽!给狗儿的雨水吧,让它自由自在地开放吧!阿门!
默里的一声阿门,叫得嘶哑而又苍凉,深深地叩动着金老万的心。赵良贴着他的耳根说:这狗儿的别是猫哭耗子假慈悲?金老万说:我跟洋堂打了几十年交道,心中有数!这狗儿的也长了出息,张嘴也是一套接一套的。我觉得还是咱们的枪炮把狗儿的上帝吓了。他背着手,摆摆地走上了渠背,默里还在为自己突然迸发的宗教情绪所感动,两只大眼泡子里泪汪汪的。金老万开门见山说,你为黑界地求雨,我不敢说你有甚坏心眼。可你的地喝饱了,长醉了,却让渠中的黄河水白白流淌!你听清了,我是说黄河水。这黄河水是甚?是我们亲娘的血浆子,奶水子!我们要喝娘的奶水子,这不是天经地义是甚?你还朝我要五万块大洋,这不是趁火打劫是甚?
默里微笑道:中国有句俗话叫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的地南低北高,水平差不下于三尺,就是把渠扒开漫灌,这水如何浇得上去?我看金先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还要为办不到的事大动干戈,甚至不惜肝脑涂地,主可以原谅你的愚蠢,但你自己如何原谅自己?面临黄河,不思开发,兴办水利,一味广种薄收,这是惜地爱地?我看是糟蹋地!金老万暗想:骂得好!骂得好!这狗嘴里也能吐出象牙来。但他嘴上不服输,大咧咧地说:我是死马当做活马医,能浇多少是多少。你就开渠漫灌吧,浇不上的地方,闻闻水气也好!默里说:漫灌是破坏地力的耕作方式。有灌无排,必将碱化土地,这无异于饮鸩止渴!你金先生不是今年活了明年不活的人吧?
金老万暗暗叹服,瞅瞅人家洋人这眼力,这远谋,这惜地爱地,好像这地是人家从家里带来的!人家不更上一层楼谁更上一层楼呢?他有些伤感地说:你说咋办吧?总不能眼瞅着我的烟苗苗成了柴火棍吧!默里悲天悯人地说:让我们接受主的仁慈宽厚吧!让主撕裂自己的身躯,用自己的血浆拯救可怜的人们吧!亡羊补牢吧!死马当作活马医吧!过了一天少两半晌吧!该死朝天,好活一天算一天吧!能吃就吃,能喝就喝吧!明天早上鞋还不知道能穿上穿不上呢!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吧!老天爷饿不死睁眼的家雀吧!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吧!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吧!是神神上案,是闺女嫁汉吧!伸脖一刀,缩脖一刀吧!拼了吧,反了吧,咋就咋吧!****八辈子姥姥老先人吧!扒渠放水先好活狗儿的吧!
金老万说:你这是拿鞋底子扇我的老脸哩!你没听人说过,打人莫打脸,揭人莫揭短?默里说:这话我也就是跟你说,黑界地上有资格听我这话的,怕是找不出几个。你也不用放枪响炮,我也不要你半两银子,我现在就给你扒渠放水!默里说着,挥着铁锹挖渠背,刷刷几下子扒开了一道尺把长的豁口,汩汩的黄水涌动跳跃着冲破豁口,渗入渠北那几十顷干涸的土地。渴极的土地大口吮吸着,黄水流经之处嘶嘶直响,喷起一团团水雾,庄户人们噢噢地叫着,像久旱逢甘霖的土地一样欢腾喜悦。遇水的烟苗立马抖擞了精神,枝叶变得舒展,就像大烟鬼美美地吸足了烟。
金老万也忍不住咧嘴嬉笑,默里冲他吼:你还笑!我都想为你哭哩!你要是再不挖排水渠,明年这块地就是一片盐碱滩。你要是一个真正的庄户人,不是刮野鬼的流寇,不是时刻想扒门窗走人的无赖,就应当马上挖排水渠,救救这块土地!我告诉你,根据这渠水的水平高度,你有一半的地还是浇不上。金老万说:保住一半是一半。这排水渠我是挖定了,马上就挖!我还要挖灌渠,我就不信你比我更喜欢这块土地!默里主教,我欠你一个情,我金老万不是那没心没肺的不义之人!默里说:你把排灌渠修好,就是还我最大的情。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你懂不懂?当你的这片地成为盐碱滩时,我也难以逃脱。金先生,当你仍继续你的愚蠢的耕作方式时,我会向你宣战,甚至不惜动用炮火!
金老万说:瞧,我们的上帝是多么慈悲!默里的眼睛闪出狼眼一样的幽幽蓝光说:我无法容忍愚昧和落后的生产方式,当教化黯然无光时,炮火会为它增辉!我甚至不怕流血和掉脑壳!我很欣赏你们这句话:砍头不过碗大的疤!金老万咧咧嘴道:我这辈子甚毛病都有过,伤过风,拉过稀,咳嗽过,气短过。从小到大,就是没有被甚吓着过!
最早嗅到干旱气息的是住在老约翰滩沙岗子上的王大爪子。他的烟亩全在沙岗子上,秋上他就在这里烧荒。他扶犁,二女子为他拉犁,一寸一寸地把大地母亲的胸膛犁开,到上冻时才开出了十几亩沙岗子地。乡亲们听说王大得爪子要在沙岗子地上种洋烟,都说他是羊拉套,瞎胡闹。洋烟籽贵得数颗颗卖,这狗儿的不是把银两往水里扔哇!冬天,当天冻得乡亲们出不了门,关在屋里淡时,王大爪子忍着刀割般的西北风,在河滩上捡牲口粪。一天刮白毛风,把树枝子都冻断了,他还在滩上捡粪。脸上冻起了两个大胞,他都不觉得。迎着满天风雪,他喊喊二女子;走在地冻如铁的沙滩上,他喊喊二女子;只要他一呼喊二女子的名字,天寒地冻,风刀霜剑全都不复存在了。二女子成为了他的上帝,他的宗教,他承受一切苦难的源泉!二女子,我捡了一筐牛粪;二女子,我又拾了一摊马粪;二女子,我不冷,我给咱的地加料哩!二女子,咱的地消冻了;二女子,咱的地升水气了!咱的地,咱的亲大亲娘,二女子!随着王大爪子的声声喊叫,他的十几亩沙岗子地上堆满了一堆堆肥料,就像布满棋子的棋盘。
当开河风止,完淡的乡亲们出现在地头田间时,目睹了这一切,都啧巴着嘴说:狗儿的这股狠劲,不让金老万!金老万也说:我早说过,这狗儿的长着一双搂财的大爪子!成了成不了气候,就看老天爷助他不助他了!当他把用全部积蓄换来的洋烟籽种点播在土地里时,当这金豆子般的洋烟籽种被粪土掩进犁沟子时,王大爪子心颤了。当他发现第一株嫩黄的烟苗拱出土时,王大爪子伏在烟地上大哭了。他像牛一样发出瘆人的长号:二女子、二女子,咱的烟苗苗拱出地皮了哇!好日子露出了芽哇!根子上长毛了哇!当烟苗抓齐后,王大爪子除了下春雨,几乎每天都挑着水桶从黄河里汲水浇烟苗,他知道沙岗子地缺水,而烟苗子格外吃水。他才不当等老天爷下雨的傻瓜蛋哩!所以当滩地上的烟苗抽蕾时,他的沙岗子地上的烟苗也抽了蕾。王大爪子对干旱的直观领略是,浇上水的花蕾开了,浇不上的渐显枯萎。王大爪子在炎炎赤日之下,一趟趟担水疯跑,双肩压成了发面饼,渗着血丝结着痂。百十斤的担子一压上去,就像一把钢针嗖嗖地往心里钻。实在困得顶不住,就像马一样站着打个盹。小路曲弯,他担着水像醉汉一样晃晃。
王大爪子几乎把命搭上,还有多一半的烟亩没有浇上。望着渐渐发枯的烟苗子,王大爪子的心就像被人用小刀剜。可乡亲们见了王大爪子的烟地,都由衷地说:这地种好了,这狗儿的抓住了。
火盆子仍在天上挂着,乡亲们心中汤煮一般。百般无奈,乡亲们屠猪杀牛祭龙王。戒了房事,戒了荤腥,赤着膊跪在太阳底下求雨。还把龙王泥胎抬上花轿,光着膀子的庄户人抬着龙王一块地头一块地头地游转,以求普降大雨。最不喜欢敬神的金老万也在老张头的撺掇之下,盖了龙王庙,塑了敖广的金身。开光那天,庄户人跪了一地,香火缭绕。龙王庙前的红橄榄树被包裹了几层红布,红布上大都写着庄户人最朴素的愿望:有求必应。
王大爪子也以自己的方式祭着神灵,那就是烤龙王。这块沙岗子地头,也有一个龙王庙,不知是哪辈子盖的,几块旧城砖砌起的一个小神龛。龛里有个尺把长的木雕龙王,黑漆漆的,也不知是什么木头雕刻成的。王大爪子把龙王爷拖了出来,烧红了烟袋锅子烫它的屁股,还观察狗儿的流不流泪。王大爪子认为把狗儿的烤流泪了,保不定就会下雨了。神神这种****玩意儿和人一样,不能光敬着,越敬毛病愈大,架子愈大。得打,得烤,得用尿刺,王大爪子冲着那龙王就是一泡老尿。在王大爪子眼中,这木头龙王真被尿刺得龇牙咧嘴,泪眼迷蒙。王大爪子暗喜:有门!继续用红彤彤的烟锅子烤屁股,那木头龙王真还升起了缕缕水气来。然后天边就聚起了黑云彩,南风呼呼地刮动了红橄榄树梢。风往南,水推船,风是雨头,屁是屎头,王大爪子高兴得在沙地上翻着跟头。云越来越厚越来越黑,咔嚓一声巨雷炸响,一条金龙跃出黑云,铜钱大的雨点子就铺天盖地的浇了下来。
王大爪子在雨雾中像撒欢的儿马窜来窜去,蹦着高吼叫,就像忽然发了魔怔。被金老万招来挖排水渠的庄户人也是一片欢腾,更感到奇怪,这雨真是下邪了,全把雨水下在渠北金老万的滩地和沙岗子地上。而渠南的洋堂水地竟是滴雨未落。佃户们都说:老天爷长着眼哩,知道老掌柜的滩地和沙岗子地缺水哩!这龙王爷再不是玩意儿,也是飨着中国人的供奉香火,咋也得偏心中国人哩!老张头说:挖渠不是好办法,就得靠天雨神灵!洋人的话能听出好来?咱把龙王爷一请回地头,就等着吃哇!佃户们也都说:就是个吃哇!黑界地的乡亲们对天年的判断就是:吃哇和不给吃哇。天年不好,乡亲们见面愁眉苦脸道:看来是今年不给吃哇!风调雨顺,见面就是:今年是吃哇!
这场及时雨一下,罂粟花遍地开放,黑界地响起一片吃哇的喝彩声。这场透雨一下,罂粟花一开,烟地的活就格外忙。锄草,施肥得及时,烟苗才能粗壮,才能割出好烟汁,结出好籽。烟汁和烟籽,这是种罂粟的直接收获。佃户们都想着烟地的活,就没心思挖排水渠,金老万吼着骂着,才勉强把这条排水渠挖成。渠内清得不好,排水不畅,没几日就泛起了碱花,成了一条白乎乎的大碱沟。默里跳着脚骂猪猡,金老万反讥他:咸吃萝卜淡操心!碱花花长在我的地上,你有甚撑不住的?默里冲着金老万咻咻直喘粗气说:我的主,这是种地?!金老万说:这不是种地是甚?默里忽然扑进碱沟里,在黄汪汪的碱水里打着滚嚎啕大哭,看那样子,像是和金老万拼命的心思都有。金老万摇着头叹道:这洋叫驴,这洋叫驴!甚都沉不住气,这排水渠早一天,晚一天有甚?甚是个轻重?不图现得利,正正经经的庄户人种这洋烟做甚?
默里落汤鸡一样从碱沟里爬起,摇晃到金老万跟前,猛地揪住金老万的脖领,鼓目道:主说了,你不配有这么多的土地!你无资格享受主这么多的丰厚馈赠!无知、愚蠢、贪婪,你是魔鬼!你要下地狱!金老万冲他脸上啐了一口浓痰说:狗儿的!给点颜色,你就想开染坊!你是甚?连根好都不是!杀人放火的事你们少做下了?这里不是蒙古人的草场?不是你们拿着洋枪洋炮把人家赶到了山上?你现在心疼土地碱化了?这是老天爷看不下去了!告诉你狗儿的吧,中国的老天爷可没好脾性,他不光收地还要收人哩!一下子就呼喇喇地陷天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