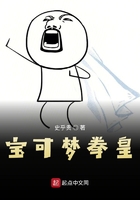待到元妃回去,萧合宫里的人也便渐渐散了,皇上问林言原萧合脸上的伤势如何。林言原答:“眼下是盛夏,伤口处理不好就容易化脓,而且上次刚长好的皮肤又受损,怕要到十月里才能痊愈了。”
“多少时日不碍事,只是女儿家在乎容颜,不要让她脸上落下疤痕才是。”
林言原送走皇上,对镜昭道了一句:“我会回去交代邓大人悉心照料美人。”
祝镜昭看林言原脸色煞白,薄薄两片嘴唇也是皱巴巴的,道:“林大人,主子有她不得已的苦衷。”
“姑姑失言了,她是主子,微臣为主子办事是分内的事情,其他的奴才不敢放在心上。”林言原将地上的胭脂水粉一一捡起,递给镜昭,道:“微臣告退。”
林言原没有回太医院,就那样走着走着,鬼使神差地便到了冷宫门口,他站在冷宫的房檐下,望着干裂的朱色高墙,脚却迈不动了,墙外的天蓝得那样透彻,以后孟昭容见到的却只能是几面高墙围起的四方天了么?他忽然看到角落里什么东西放着光向他扑来,想躲开却已经来不及,他急忙中用广袖遮了脸,却什么动静也没有,过了一会儿,只听见几声惨叫,才将广袖放下,只见一只野猫已经被一个侍卫用剑挑死,那个侍卫收完剑,一见是林言原,忙打了千,道:“是林大人,您怎么到这个脏地方来了?”
林言原倒是经常帮侍卫医些小伤小痛,所以大多人都认得,这个便是在冷宫里当差的,忙道:“多谢了。”又道:“方才没看见你,你打哪里来的?”
“刚安置好新来的孟氏,才从里面出来。大人赶紧走吧,这样晦气的地方。”
林言原望着一旁的死猫,白乎乎一片躺在一滩血里,连挑出的肠子都白花花露在外面,胃里一阵翻腾,道:告辞了。“末了,还是折了回来,道:“望大人转告孟昭容,猫有九命,望昭容好自为之。”
那个侍卫望了一眼那只猫,立刻会意,笑道:“就算命再大,到了这里也是非死即伤。”又打了恭,道:“既然大人交代了,奴才一定把话如实带到。”
阳光转过窗棂,在漆黑的屋中投下一柱光,外面还能依稀听到蝉声,宫内却冰冷如寒冬,孟昭容的眼泪怕是流尽了,她用手轻轻抹过眼角最后挂着的那颗泪珠儿,始觉得手脚冰凉,借着那柱光束,隐隐看见桌上立着一盏油灯,她忽然觉得这样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倒不如一把烧了干净,这样想着,她便瑟缩着往桌边爬去,却听得那扇年久失修的门“吱钮”一声被人推开,她只觉得光线刺得人睁不开眼,忙用帕子遮住眼,原来外面还是白天呢,那人站在门口,她逆着光,只能隐隐看见一个剪影,只听那个剪影道:“给林太医带话,猫有九命,望昭容好自为之。”
接着,仍然是黑暗,只有那闭门的声响在她耳中不断回荡,她还是哭了,哭着哭着却开始笑:“猫有九命,唯有一心哈。”末了,她还是走到桌边,点亮那盏油灯,灯火左右来回晃着,噗噗的声音像是未长全牙齿的孩子呵出的气,她用手仔细护着这微弱的光,护着她在这冷宫里唯一的希望和温暖。
夕阳如血从重重高柳下徐徐沉下,无边林莽皆被染上瑰丽的金色,好竹馆中却隐隐有琵琶音传出来,正是《十面埋伏》垓下伏兵那一段,气氛宁静却紧张,音行到低处,仿佛要把耳朵贴到地面才能听见,就在思虑音是否断了时,接下来便是九里山大战,楚汉两军激战,生死搏杀,马蹄声、刀戈相击声、呐喊声交织起伏,银瓶乍破水浆迸,连着窗外寒鸦宿鸟皆吱吱呀呀惊起,实在让人觉得凄凉而肃杀,打宫门外过的宫女儿丫鬟听到都低眉快步走着,闻曲碎胆,细碎的步子迈得格外急,偶有年轻不懂事的细驻脚步探头往里面瞧,亦被同行的人拉到一旁,道:“你找死呢,里头那一位今儿个刚被人算计,心里正是苦呢,赶紧走吧。”
软玉进来的时候,已是曲终,马蹄声交替,突围落荒而走的项王,紧追不舍的汉军。力拔山兮,虞姬奈何兮,最后四弦一划,声如裂帛,刹住,乐声嘎然而止。
“好,好一出《十面埋伏》。”软玉击掌喝道,声音中却还是没出息地带了一丝哽咽。
萧合见门口碧影已往跟前走来,也放下琵琶,一边褪下手上的薄象牙片护甲,一边道:“软玉,今个怎么回来的这样晚。”
软玉并没有请安,而是走到跟前抚着琵琶覆手,道:“美人读的好书,又弹得一手好琵琶,一定也谈的一手好棋喽。”
萧合并非不知道软玉想说什么,却只能顺着她,道:“略懂一二罢了。”
“美人觉得用软玉做的棋子使着还合手么?”软玉将琴弦往前一批,只听见“彭”地一声,老弦音震得空中沉迹都荡荡的。
萧合迎向软玉的目光,良久,道:“不曾用过,所以并不知道顺不顺手。”
“今日的事情,孟昭容,巧姐姐,镜昭姑姑,林大人,你不想说些什么吗?”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
软玉一把拉起萧合的衣袖,道:“主子,好主子,你没有,我有,你听我说的对不对?杨柳房中的水沉蜜是我在玉壶冬瓶里找到的,而今日李公公就从好竹馆带出去了一个玉壶冬瓶。你们故意让我看见,知道我到了杨柳房中见了瓶子一定会起疑的。”软玉拉着萧合便往妆奁前走去,指着一盒胭脂便道:“这盒胭脂,根本就是平常女儿家用的,有水沉蜜再正常不过,根本就没人动过手脚,七巧不过是你一手安排用来扳倒杨柳的,对么?主子,您这样的谋算,软玉跟着您,是要扶摇直上啊!”
“对,却不全对。”萧合苦笑,道:“这个局的确是我早摆好的,我是利用七巧,利用镜昭。可是你呢?软玉,今日你所说的每一句话,所做的每一件事,是我事先授意你的么?”
萧合感到软玉的手一颤,挣手道:“自己的心思能让别人全然看穿,连一举一动都被旁人掌控,你该反思的是你自己,而不是跑来我这里兴师问罪。”
软玉忍着不让自己的眼珠儿落下,她觉得此刻不让眼泪流出是她唯一的尊严了,良久,才道:“以前咱们同在知春园里当差,我只是嫉妒你人生得美,又圆通懂事。后来你被封为昭容,李公公要我来这里侍奉你,我并不愿意,却没法子。相处了数日,我才觉得你真的和旁人不一样,不议论旁的主子,也不与旁人相争,对待下人又从不拿主子的款,我觉得和你相比,我真的差好多。”
萧合见到软玉这样,语气终归软了下来:”软玉,我知道你委屈,可是宫中十面埋伏,处处险境,时时有人剑拔弩张,我有我的不得已。”说着便拿出缎纹单纱手帕去抹掉软玉的泪水,不料被软玉一下子推开,力道过猛,她又没个防备,萧合只觉得撞在桌角上的小腹隐隐作痛,桌上的东西都落了一地。
镜昭,七巧闻声进来。软玉亦觉得自己做得有些过分,想去扶,却挪不开脚。
还是七巧跪了下来,道:“软玉妹妹,并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弟弟的确从小身子虚弱,日日离不开药的,美人这样做是帮了我。”
软玉始见七巧跪下,还忙着虚扶了一把,如今听她这样说,也不再觉得过意不去,冷笑道:“巧姐姐。难道她给你的银子在你的心里竟比不过两条人命么?你弟弟的命是命,孟昭容和杨柳姑姑的命就不是命了么?”
“软玉,是不是杨柳将美人害死,你就满意了,在你心里,旁人的命都是命,只有美人的不是么?”镜昭喝道:“你知不知道上回美人在知春园脸上不好,就是杨柳害的。”祝镜昭见软玉怔住,又瞧了四下,道:“你以为主子好端端地为何会得皇上宠幸。你知不知道杨柳是庄妃的心腹,你只恨你被人用做棋子,却不知道美人亦是庄妃和元妃争斗的一颗棋子罢。”
软玉在好竹馆的时候其实已经看出一些端倪的,林言原和萧合绝不是那样简单,她常讥讽:“只差把缱绻两个字写在脸上了。”可是,后来萧合为何被封为美人,她倒是不曾多想,只当是宫中传的那样,林言原开罪了柳美人,萧合去求情。皇上相中一个宫女再正常不过,何况是萧合这样绝色的呢。如今听镜昭这样说,软玉才明白里头大有文章,皇上登基不过半年,庄妃和元妃不对付却已是宫中人尽皆知的事情,庄妃前几个月被禁足,她怎能甘心,必然是庄妃想找心腹,而杨柳正好物色到了萧合。照这么说,这条长线竟放得这样长。
软玉倒吸一口凉气,好一个有手段的庄妃,若是搁着元妃的性子,想必是要强来。可是庄妃却不一样,她知道要想让萧合心甘情愿依附她,她只能从旁的地方下手,而连自己这样马虎的人都能看出林言原的心思,更不必说是心思细腻的杨柳了。原来是这样。若是萧合固执于柳星因病痛而拆散自己的一段姻缘,那么萧合自然要怨柳星因,要怨元妃,那样的话,不废吹灰之力,庄妃便和萧合是一路的人了。这样说,连柳星因的心绞痛都是庄妃计谋中的一步了,谁都知道,柳星因那样娇嗔,宫中除了林大人,旁的太医她向来不让近身的。
可是。
“可是,美人是怎么知道这些的?”软玉终于安静了下来,问道。
萧合道:“是杨柳一次来找我闲话,剔灯花的时候,将灯油溅到我的脸上。她还问我用的什么胭脂,知道我用的都是一般的没有水沉蜜的后,她又一番好意送来了那盒胭脂。”萧合指了指妆奁,道:“后来言原告诉我的脸是用了水沉蜜的缘故,我才想通的。李公公也暗中查了杨柳,知道她和庄妃的贴身丫鬟荟涓是亲姊妹。”又道:“今个的事你不觉得奇怪么?那一番话都是我教七巧说的,杨柳连七巧是谁都不知道,可是她却招了,就是因为当时镜昭故意让她看见那天她送我的胭脂盒子,她怕镜昭将庄妃和她妹妹牵扯出来,一心护主,才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
软玉只觉得脊梁发冷,那种寒意是直浸到人心里面去的,萧合头上一支蕉叶碧玲珑翡翠流苏映出生冷的光,软玉犹闻雨打芭蕉,淅沥作响,道:“那孟昭容呢?”
镜昭亦没有隐瞒,望了一眼萧合,见她颔首,道:“孟昭容的事,若是猜得不错,应该是柳美人在背后推波助澜。”
软玉剪水双瞳霎时惊惶失色,十面埋伏,起承转合,烈烈生风,宫中一言一行,竟是这样牵一发而动全身。
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镜昭亦道:“或许你觉得可怕,但我们并不是无缘无故去害一个人,杨柳和庄妃的心思才是深,送来那样一盒胭脂,就算美人起疑,她大可说她是好心办了坏事,便可将此事推得干干净净。一个宫女,不懂医理不是很正常吗。”
软玉才明白,镜昭是都知道了,“美人为何不肯一早告诉我?”
“你在心里已然对我有了成见,我无论如何解释,也不过是加深或者验证你的成见罢了,况且还不到解释的时候。”
镜昭道:“美人和林大人不得相守已经难受,如今还要被林大人和你误会。”
既然她知道庄妃所谋为的就是她能面圣,为何还肯到皇上跟前。软玉想问,眼前却忽然浮现的都是萧合那样温柔和善的脸庞,她从来没有在人前显露过她的绝望。萧合是可怜的,软玉忽然觉得,末了,她还是张不开口去问。
萧合又拿起琵琶,道:“让我一个人呆一会儿。”
等到七巧和镜昭退下,软玉却仍跪在跟前,问道:“美人,您为何今儿个不在皇上跟前将庄妃的事情说破呢?就算杨柳不肯招,皇上也必然会起疑。”
萧合拨了琴弦,道:“翁蚌相争。”
软玉凑到跟前,只见玉户帘外闲潭落花,低树葱茏,轻轻道:“怕是想得利的渔翁并不只美人您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