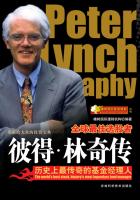船在河面上不停地走着,从早到晚……轮船上的男女老少,不同的面孔的人都离不开一日三餐。船上的人喝酒、吃饭、搞脏了许多的杯盘、碗碟、刀叉、汤匙。阿廖莎的差事就是要把弄脏了的餐具重新擦洗干净。一天中只有下午两点到六点,晚上十点到午夜之间,他的差事少些,其余时间就忙得不可开交。这几个钟头里,食堂的工人有些空闲,他们常常在一起喝茶、闲谈。阿廖莎和他们越来越熟悉了。厨师史默利伊喜欢听阿廖莎给他读书。他回到自己的舱房,递给阿廖莎一本皮封面的小书,他在靠近墙壁的一个吊床上躺下,说道:“你念吧!”阿廖莎翻开书,坐在一只木箱上,用心地念道:
“满天繁星的日全蚀,象征着他们可以摆脱笨人和恶德的束缚,通往天国的道路畅通无阻。坦露左胸标志心地的纯洁……”
“混蛋,他们在写些什么?”史默利伊埋怨起来。
“你再找一本!”他接着说。
阿廖莎打开他的铁皮黑箱子,里面的书可真多,有《奥米尔教言》、《谢里加利勋爵书信集》、《盍尔伐西》、《炮兵生活回忆录》……全都是些莫名其妙的书。
那些古怪的词和生疏的名字使阿廖莎厌恶,可是史默利伊却说:“人与人的区别,在于傻不傻。为了变聪明,就得读正经书。所有的书都要读,那你才能找到正经的书。读吧,孩子,念不懂就念两遍,两遍不懂就念三遍,直到念懂。”
阿廖莎不知不觉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变成了有书在手,不知忧愁了。
一次史默利伊从船长太太那里借了一本果戈里的《塔拉斯·布尔巴》。这本书描写的是乌克兰人民反抗侵略者的英勇史迹。当阿廖莎念到塔拉斯向奥斯达普挑战的那一段时,史默利伊笑起来,他很专心地听着。当念到安德烈叛变时,他骂起来,“不要脸的东西,为了女人……”书念到最后奥斯达普临死,喊着“爹,你听见了没有”的时候,他哭了,哭得很伤心。史默利伊从阿廖莎手中拿过书,认真地看着,眼泪滴在封面上。
后来,史默利伊和阿廖莎一起读《艾凡赫》、《汤姆·琼斯》……阿廖莎简直对读书着了迷。有时,因为读书,耽误了干活。甚至引起了厨房伙计们的不满,有时他们还故意陷害他。一次,食具管理员在盛脏水和剩茶的盆子里放了几只杯子,阿廖莎不知道,把水向船外泼去,杯子也一起泼了出去。伙食管理员把阿廖莎大骂一通,食堂老板也知道了这件事,接着发生了许多对阿廖莎不利的事,甲板上的跑堂谢尔盖几次偷走阿廖莎桌子上的茶具,背着食堂老板卖给乘客。
一天傍晚,食堂老板叫阿廖莎去他的房间。阿廖莎走进他的房间,见史默利伊脸色阴沉地坐在凳子上,食堂老板对他说:“他来了。”
史默利伊问阿廖莎:“是你把茶具拿给谢尔盖的吗?”
阿廖莎很干脆地回答:“没有,是他自己偷的。”
沉默了一会儿,史默利伊又问道:“谢尔盖给过你钱吗?”
“没有,从来没有。”阿廖莎肯定地回答。
“他不会撒谎。”史默利伊对食堂老板说。
食堂老板声调严肃地回答:“那也一样,是他丢失了茶具。”
轮船回到了尼日尼·诺夫哥罗德城,食堂老板辞退了阿廖莎。阿廖莎领到了8个卢布的工钱,这对他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史默利伊和阿廖莎告别的时候,忧虑地说:“以后办事要小心,粗心大意是不行的……”他把双手插在阿廖莎的腋下,双手举起阿廖莎,亲吻着,接着又稳稳地把阿廖莎放在甲板上。阿廖莎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甲板,回过头来看着这位高大、孤独的长者。他为自己而懊悔,假如能永远跟他在一起该多好啊,他几乎哭出声来……十二岁的阿廖莎又一次地失了业。
史默利伊是一名退职的卫队排长,是他唤起了阿廖莎读书的兴趣,为阿廖莎后来成长为一名世界文坛上伟大的杰出的文学家起了重要的作用。
阿廖莎又回到了外祖母的家里。
阿廖莎决定以捕捉会唱歌的鸟雀为职业。他买了网子,做好鸟笼。终于有一天,阿廖莎在一条山沟的灌木丛里捕鸟。一会儿,一群黄雀落在灌木丛里,像一群顽皮的孩子,蹦蹦跳跳,东张西望。太阳升起来了,鸟雀越来越多,叫声也越来越欢快……
外祖母卖掉了阿廖莎捕获的鸟,挣了四十个戈比,她惊讶地说:“没想到这个不起眼的行当,竟能赚这么多的钱!”
天冷下雪了,外祖父又一次把阿廖莎领到了绘图师的家里。在阿廖莎看来主人家的生活越发沉闷乏味,与第一次来时所不同的是:他们家又添了两个婴孩,阿廖莎要做更多的劳役。除了每天在家里洗涤那些婴孩的衣物外,每星期还要有一次把衣服拿到宪兵泉洗涤一番,当然其他的杂活是不能免的。不过在阿廖莎看来和那些率直倜傥的洗衣妇在一起,倒比在绘图师家里快活得多。
此外,阿廖莎还和主人家邻近的军官的勤务兵来往。阿廖莎在板棚里劈柴,那些勤务兵经常到这儿来,跟他谈军官家里的事。有时阿廖莎也自愿到他们的房子里去拜访他们,读书给他们听,并依他们的意思帮他们写家信。闲谈中,阿廖莎也更了解了俄国的农村和军队的生活。
从勤务兵的口中,阿廖莎知道了军官们近日消遣的一种新玩意儿——他们轮流给痴情的裁缝师傅的娇小的妻子写情书,来戏弄她的感情。阿廖莎决意要把这件事的内幕告诉裁缝师傅的妻子。
阿廖莎趁裁缝师傅的妻子一个人在房间的时候,从后面的楼梯进去,溜进了她的房间。阿廖莎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出了事情的真象。她被吓得发呆,渐渐安定后,才觉得这个憨直的孩子的一番好意。她会意地笑了,并说:“你真是个奇孩子!”接着又问:“你上过学吗?你喜欢看书吗?”她开始借小说给阿廖莎看。书向阿廖莎展示出另一种生活,把他引向了更广阔的世界。
阿廖莎越来越高涨的读书热情,也给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难堪和凌辱。
星期六的傍晚,主人一家出外做彻夜祈祷去了,阿廖莎没有去;他开始看一本从裁缝师傅的妻子那里借来的书。他读书入了迷,耳朵听到大门口的门铃声,竟一时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保姆从房间里跳出来,大声喊:“阿廖莎,去开门,你聋啦!”这时他才恍然大悟。阿廖莎赶紧跑去开门。
“你睡着啦?”主人厉声地问。他的妻子一边爬上楼梯,一边埋怨阿廖莎害得她着了凉,主人的母亲却骂个不停,当她看到那支将要燃完的蜡烛的时候,高声叫喊着:“你们看,整整一支蜡烛都让他点完了,他会把房子烧光……”吃早餐的时候,主人一家重新数落阿廖莎过去犯过的有意或无意的过错,并吓唬他日后不会有好结果。他们吃饱了饭,就疲乏地走散,睡觉去了。
不久,阿廖莎又经历了一件不愉快的事。那是一个星期天,主人一家去做早弥撒,阿廖莎在厨房里烧上茶炊,就去收拾房间。主人家的孩子溜进厨房拧下了茶炊上的水龙头,水流光后,茶炊内膛里的木炭开始烧干锅。阿廖莎在房间里闻到一股难闻的气味,当他跑到厨房的时候,看到整个茶炊变成了青色,茶炊的盖子歪到一旁,一滴滴的锡液从茶炊的把手底部流下,阿廖莎用水浇它,它瘫软在地板上,好像喝得酩酊大醉。这时门铃响了,阿廖莎神色慌张地去开门……
主人的母亲,看到瘫软在地板上的茶炊,不由分说拿起一块松木的劈柴,对准阿廖莎的脊背一顿毒打。将近傍晚,阿廖莎的后背就像枕头一样地鼓起来,原来他的皮肤里扎进了许许多多的长木刺。第二天中午,主人不得不把阿廖莎送进了医院。
一个瘦高的医师检查完阿廖莎的伤口,用深沉的话语说道:“这样毒打人,得写状子报官。”
阿廖莎回到了主人家,他并没有去告官,主人一家对阿廖莎颇为满意,他们以后便对他到裁缝师傅的妻子那里借书并不干涉。
过了一天,阿廖莎又到裁缝师傅的妻子那里借书。他读得书越来越多,大仲马、彭桑·杜·特里尔、蒙台潘·沙科涅、加博里奥、艾玛拉、布阿果贝的书,他一本接一本地读。他读书的速度很快,他觉得自己是在参与一种不平凡的生活,这种生活令人激动,令人振奋。
阿廖莎读着龚古尔的长篇小说《泽妞加诺弟兄》,沉浸在卖艺弟兄的悲惨故事中,他两只手发抖了。当他读到那个不幸的、断了腿的艺人爬上阁楼,而他的弟弟正在那里悄悄地练他们所钟爱的技艺的时候,他放声大哭了。
这以后没多久,一本真正的“正当的”好书落到了他的手里,这就是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
葛朗台老头儿使阿廖莎自然地联想到了他的外祖父……
到了春天,裁缝师傅的妻子突然不知去向了。过了几天,她的丈夫也走了。
阿廖莎心里很悲凉,他多么想再见到裁缝师傅的娇小的妻子,向她说几句感激的话啊……
在裁缝师傅一家搬走以前,就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太太带着她的母亲和一个小姑娘搬进了主人家住宅的楼下来住了。一名叫邱弗亚耶夫的士兵,在她家干粗活。小姑娘也像她的母亲一样美丽动人,家里没有专门照料孩子的保姆,小姑娘经常自顾自地玩着。每天傍晚,阿廖莎出来和她一起玩,很快地,他们混熟了。阿廖莎给她讲童话故事,她也滔滔不绝地讲关于她们的生活,在阿廖莎面前又悄悄地展开了一种新的生活。
一天傍晚,阿廖莎坐在门廊上等主人一家从奥特科斯散步回来,小姑娘也在一旁玩耍。她的母亲从她身边经过,轻捷地起身下马,然后头往后一昂,对小姑娘说:“喂,回家吧,该吃晚饭了!”小姑娘顺从地跟着她的母亲走了。但晚饭过后,她家的女仆来叫阿廖莎,说小姑娘不跟阿廖莎说“再见”,就是不睡觉。
阿廖莎得意洋洋地走进她家的客厅,小姑娘迎过来,很热情地拉阿廖莎坐在柔软的沙发上,一边对母亲说:“他是我的小伙伴,是他常给我讲故事……”她的母亲好奇地问阿廖莎:“你读过书吗?”她的脸上露出了愉快的笑容。
阿廖莎说出了几部长篇小说的名字,美丽的夫人站起身来,说了一句,“原来是这样……哦,好吧,以后我可以借给你书看……”她从长沙发上顺手拿了一本黄色封皮的书递给阿廖莎并且说:“读完了,再来拿第二本……”
阿廖莎拿着一本美谢尔斯基公爵的《彼得堡的秘密》回去了,他聚精会神地读着这本书没读几页,他就感到有些乏味。这本书里,只有关于自由和棍棒的寓言值得玩味。
几天后,阿廖莎把书还给了这位美丽的夫人。“哦,怎么样,喜欢吗?”夫人问。阿廖莎没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夫人笑了,走到卧室,取出了一本蓝色山羊皮硬封面的书说:“这本,你准喜欢,只是不要弄脏它!”
那是一本普希金的诗集,阿廖莎如饥似渴地读完了它。普希金朴实无华的语言,错落有致的韵律,使阿廖莎大为惊叹,这些诗句好像鸣响了新生活的钟声。读着这些诗句,他心里充满着愉快和欢欣,他觉得一个人能够认字读书,该是多么幸福啊!
阿廖莎背诵了普希金的那些精彩的童话诗。每当躺下睡觉时,他就闭上眼睛,默读着,直到进入梦乡。有时他还把这些童话诗大声地朗读给勤务兵们听。他们常常听得放声大哭。
阿廖莎不断到美丽的夫人那里去借书,她越来越多地和阿廖莎交谈,从她那里阿廖莎得到了很多益处。她鼓励他“要读些俄国的书,应该了解我们自己的生活。”她列举了若干俄国作家的名字,按着夫人的指点,阿廖莎读了阿克萨科夫的《家庭纪事》、俄国史诗《在树林中》、《猎人日记》……他开始认识到好书是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
阿廖莎因用眼过度而出了毛病,医师在他的眼皮里做了手术,他拆去绷带后,去看勤务兵,正赶上他们喝醉了酒,一个士兵用一根大劈柴打伤了另一个士兵的头部。阿廖莎抱起被打伤的士兵,任他头上的血滴在自己的膝盖上。被打伤的士兵慢慢清醒了,他莫名其妙地勃然大怒,大喊大叫,伸出两只脏兮兮的手,冲着阿廖莎的眼睛,狠狠地打了一拳。阿廖莎大叫了一声,眼前一片模糊,阿廖莎跑到院子里,用冷水冲了眼睛……
第二天早晨,阿廖莎到楼下的板棚取木柴时,捡到了一个空钱夹,他认出这是被打伤的士兵的钱夹,他拿着空钱夹送还了那个士兵。
那个被打伤的士兵生气地眨着眼睛,不相信阿廖莎捡到的是空钱夹。后来真的贼依实承认,这件事真相大白。
阿廖莎无端受到毁谤,他不能忍受这样的侮辱,便悄然离开了这里。
他又去做洗碗工了,这一次是在“彼尔姆号”轮船上。和从前一样,他的好奇心又集中于水手和熙来攘往的旅客,他的眼睛又饱览伏尔加河上无穷无尽的景致了。
阿廖莎的工作是:每天早晨,给师傅们烧好早茶,打扫作坊,挖出鸡蛋黄准备调颜料。然后到铺子里去帮助招徕顾客。每到黄昏,就开始研磨颜料,观摩师傅们的手艺。起初,阿廖莎怀着极大的兴趣观赏师傅们的手艺。不久,就感到厌烦,并发现几乎所有的手艺人对他们的工作也同样感到烦闷和无聊。
闲暇的时候,阿廖莎就给师傅们讲轮船上的生活和书上的故事。阿廖莎在那些圣像作坊的师傅们看来是多么重要,他此时虽然只有十三岁。但对于人生,阿廖莎的见识比他们当中任何人都来得多;而且他的眼界,超越了他们的想象所能达到的境域之外。在大家闲谈的时候,长着胡子的师傅不得不倾耳静听他的谈话。阿廖莎还把他的读书狂欲分给他们,工作之余,读书给他们听,乐此不疲。阿廖莎特别喜欢他们,他们对阿廖莎也很好,有了书,春天就好像来到了他们中间,他们不愿意看到眼前贫穷乏味的生活,他们憧憬着未来……
虽说阿廖莎和圣像师傅们有着愉快的关系,但是他对于圣像作坊里的生活一天一天地觉得不满意,铺子里的日子更使他感到压抑……
春天到了,他的视线又注意到伏尔加河,他原想找一个轮船上的工作,乘船离开尼日尼·诺夫哥罗德到阿斯特拉罕去,因为那是他和父亲、母亲一起生活过的地方。他还想到波斯去,这大概是因为他在尼日尼·诺夫哥罗德的定期集市上,看到过波斯商人,觉得他们很可爱……无意中他又遇见了他的亲戚——绘图师。绘图师很和气地招呼他,并且拿出一支香烟给他吸。阿廖莎受到绘图师好意的软化,终于接受了他的雇用。绘图师承包了市场上的店铺的建筑工程,阿廖莎担任了监工的职务——监视木工和其他工人,防止他们偷懒或偷窃建筑材料。
阿廖莎又来到了绘图师的家里。那位美丽的夫人以前住过的房子里,现在住着一大家子。这家有五个少女,一个赛过一个地漂亮,其中有两个是中学生。他们都让阿廖莎看书,他拼命地读着屠格涅夫的作品,狄更斯的作品也使他羡慕得五体投地。
主人家的制图工作很多,他同弟弟两个人忙不过来,于是请了阿廖莎的继父来帮忙。
傍晚,阿廖莎从工地上回来,进了饭厅。一个人向他伸出手来,“你好……”
阿廖莎认出这正是他的继父。继父看着阿廖莎,露出尴尬的笑容。从前的事一下子像火一样燃烧起来,阿廖莎想起继父曾经怎样地毒打他的母亲,他一句话也没说。
“我们又重逢了……”说着,继父咳嗽起来。
继父的饭量大得惊人。主人家用一种令人难堪的态度对待阿廖莎的继父,这反而缩短了阿廖莎与继父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