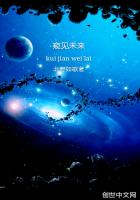唯有波涛在怒吼、在翻腾,
而野兽觉察到人的踪迹,
朝向黑暗的荒野里逃奔。
有一天俄罗斯俘虏听见
深山里发出战争的号令:
“快去,奔马群去!”奔跑、喧嚷;
铜马勒发出叮当的响声,
外套的黑影,铠甲的寒光,
备上鞍鞯的战马在跳动,
整个山村准备走向战争,
从山岗上河水似地涌来
战争的粗犷剽悍的子孙,
他们沿库班河两岸飞驰
去收取那些强制的贡品。
山村静下来了,看家的狗
晒着太阳,熟睡在小屋旁,
黧黑的赤身裸体的儿童
自由的嬉戏中尽情喧嚷;
他们的祖父们坐成一圈,
烟管里冒出蓝色的轻烟。
他们默默无言地倾听着
年轻姑娘们熟悉的歌声,
而老人的心也变得年轻。车尔凯斯之歌
1
汹涌的波涛在河里奔腾;
深山里夜半时寂静无声;
凭倚着精钢打造的长矛,
疲倦的哥萨克正在打盹。
别睡啊,哥萨克:夜色沉沉,
河对岸来了车奇尼亚人。
2
哥萨克划着一只独木船,
顺河底拖着渔网在前进。
正像暑热天到河里洗澡
沉没到河水中去的儿童,
哥萨克,你赶快跳入河中:
河对岸来了车奇尼亚人。
3
在这条分界河的河岸上
富裕的村庄是这样繁荣;
人们在跳着快乐的环舞,
快跑吧,俄罗斯的歌女们,
快些啊,快些回家去,美人:
河对岸来了车奇尼亚人。
姑娘们在唱着。俄罗斯人
坐在岸上,想着如何脱身;
但深深的河水这般湍急,
俘虏的锁链又这般沉重……
暮色苍茫,草原也已入梦,
高高的山峰已一片朦胧。
明月洒下了惨淡的光辉,
照耀着茅屋白色的屋顶;
牡鹿在河岸上渐渐入睡,
苍鹰的叫声也已经沉静,
远处马群在踏踏地奔跑,
深山里沉闷地响起回声。
这时仿佛听得有人响动,
忽然闪出了女郎的披纱,
看哪——正在向着他走来的
是那忧郁而又苍白的她。
双唇好像是就想要说话;
两眼充满了无限的哀愁,
她那秀发像乌黑的波浪,
一直披拂到胸口和肩头。
一只手握着闪亮的钢锯,
另一只手拿着她的钢刀;
仿佛是,女郎正前来参加
秘密的战斗,好一逞英豪。
她向俘虏抬起她的双眼,
“跑吧,”——山中的女郎这样说,——
“车尔凯斯人不会碰到你,
快,不要浪费黑夜的时间,
拿上我这把刀,在黑暗中
无论谁都不会把你发现。”
一只颤栗的手握着钢锯,
女郎向他脚前弯下腰去:
锯着铁镣吱咕吱咕地响,
不自禁的泪珠滚滚流淌——
哐啷一声,锁链落到地上。
“你自由了,”女郎说道,“跑吧!”
但是她如痴似呆的目光
流露出内心迸发的爱情。
她在痛苦着。呼呼的阵风
在长啸,卷起了她的衣襟。
“好人啊!”俄罗斯人哽咽道,
“我属于你,至死是你的人。
我们抛开这可怕的地方,
同我一起逃……”“不,俄罗斯人!
它已消逝了,——人生的甜蜜,
我一切都尝过,尝过欢欣,
而一切消逝得无踪无迹。
这怎么可能?你爱过别人!……
快去找她吧,你快去爱她;
我心中有什么值得哀痛?
我心中有什么值得牵挂?
别了,别了!愿爱情的祝福
每时每刻永远与你同在。
永别了!——请忘掉我的痛苦,
最后一次……请把手伸过来。”
他伸手向车尔凯斯女郎,
向她飞去一颗复燃的心,
而那临别的长长的一吻
给爱情的结合打上烙印。
他们手挽手,满怀着忧郁,
默默无言地走到了河边——
俄罗斯人在喧腾的河中
已经浮游起来,浪花飞溅,
已经游到了对岸的岩石,
已经攀住了对岸的山岩……
突然间波浪中噗通一响
远远的呻吟向耳边传来……
他走到那荒凉的河岸上,
向后一看……岸上清晰可见,
飞溅的浪花闪发着白光:
但是在河岸上、在山脚前
都看不见车尔凯斯女郎……
万籁俱寂……沉静的河岸上
只听见凉风轻微的声响
而月光下哗哗的水波中
荡起的浪圈已平复如常。
他都明白了。他最后一次
用诀别的目光四处一看,
俘虏放牧过牛羊的田野、
荒寂的山村、四周的栅栏、
拖着锁链攀登过的悬崖
和正午时休息过的溪流,
当山中好汉车尔凯斯人
高唱起自由歌曲的时候。
天空中的黑暗渐渐淡薄,
白昼已来到昏暗的山谷,
朝霞升起了。逃脱的俘虏
已走上一条遥远的小路;
在他前面朝雾里已看见
俄罗斯耀眼的刀光剑影,
在一座座高高的土台上
守哨的哥萨克互相呼应。
最后尾声
缪斯,幻想的轻捷的朋友,
就这样一直飞向亚细亚,
只为了给自己编织花冠,
采撷高加索缤纷的野花。
魔女为生长在战争中的
民族的纯朴服饰所迷恋,
她也穿戴上这样的新装
常常地出现在我的眼前;
在那些荒漠的山村四近
她独自个在山岩间徜徉,
而常常在那里倾心谛听
孤苦伶仃的少女的歌唱;
她喜爱那些武装的村庄、
勇敢的哥萨克人的机警、
起伏的山丘、寂静的坟场、
嘈杂的喧哗、马群的嘶鸣。
主宰歌曲与故事的女神
怀着对过去种种的回忆,
或许,她将要重新讲起那
可怕的高加索古代传奇;
她将要讲起远方的故事、
姆斯提斯拉夫的大决战、
背叛的勾当和俄罗斯人
死在格鲁吉亚女郎胸前;
我要歌颂那光荣的时辰,
在那时候我们的双头鹰
嗅到血腥的战争,便飞上
那愤怒的高加索的山峰;
那时茫茫的捷列克河上
第一次响起战争的雷霆
和俄罗斯的咚咚的鼓声,
盛怒的齐齐阿诺夫来到
谢切,傲视一切、威风凛凛;
我歌唱你,高加索的魔王,
柯特梁列夫斯基啊,英雄!
无论你风暴般飞向哪里——
你的行踪像一场黑死病,
杀尽、绝灭了那里的人种……
而今你放下仇恨的钢刀,
战争已不再娱悦你的心;
倦于世事,带着光荣创痕,
在故乡的深山的寂静里
你在享受着悠闲的恬静……
但这时——东方又发出哀号!……
高加索,低下白雪的头颅,
顺服吧,叶尔莫洛夫来到!
战争狂暴的呐喊平息了,
一切俯首于俄罗斯刀下。
高加索骄傲的子孙,你们
曾战斗过,死得多么可怕;
但我们的鲜血不能拯救
你们,无论是耀眼的铠甲、
无论是纯真自由的爱情、
无论是深山、无论是骏马!
正好像拔都的后裔一样,
高加将索背叛它的祖先,
忘掉贪欲的战争的声音,
抛掉可怕的战斗的弓箭。
行人将能够放心地走进
你们聚居的幽谷和深山,
而你们传说的悲惨故事
把你们的苦难永远流传。
《茨冈人》
一大群热闹的茨冈
沿着柏萨腊比游荡。
他们今天过夜,就在那
河上搭起破烂的篷帐。
自由自在的,还有天做他们的篷,
好快乐的过夜,他们的和平的梦。
好些车轮中间,
一半盖着地毡,
点上了灯,一家人
围着就预备晚饭。
他们的马在干净的田地上放着,
篷帐后面一只熊开了锁链躺着,
旷场中间,一切
都是活泼泼地:
小孩子叫着,
娘儿们唱着,
还有车上的
行军灶响着。
这些人家,一早
就又要上路的,
他们要有心事,
也是怪和平的。
游荡的营帐扎下了,
沉默的睡魔也来了。
静悄悄的旷场,听得见的
也就只有马嘶跟狗咬了。
那儿也再看不见火光,
什么都安静,只有月亮
高高的独个儿在天上
照着那静悄悄的营帐。
一个篷帐里面
老头儿还没有睡着,
他坐在炭跟前
借一点儿火气烤着,
看着那远远的田地
罩满了夜里的雾气。
他有个年青女儿,
到荒田去玩了,
她那自由的性儿,
就这么游荡惯了:
她来是要来的,
可是已经太晚了。
月亮送着云儿
要分手也就快了。
真妃儿,真妃儿呢,怎么还不来,
老头儿这顿穷饭也要冷完了。
啊,她来了。跟着她后面走的,
那个人,年纪很轻哪,——
老头儿是从来也没见过的。
姑娘说:“我的父亲哪,
我带来个客人:我在坟场
荒地上找着的他,
我叫他来到我们的营帐,
让他这儿过夜吧,
他说,他要做茨冈
跟我们一样。
衙门里要捉他。
我可要保护他,
他名字叫阿乐哥,
愿意到处跟着我。”
老头儿:
我很高兴。
就在我们篷帐
里面的草堆上
过夜也行,
要是你真愿意
留在我们这里
一块儿来挨这个苦命,
那也没有什么不行。
准有你的面包,
准有地方睡觉,
你就做了我们的人,
只要惯了就成,
虽然说是穷困,
倒也自由得很。
我们明天清早起身
就一块儿赶着车动身;
随便你找个什么事做做:
铁锤呢,阿乐哥?
还是你会唱歌,
带只熊到村庄上去走走?
阿乐哥:
我留着不走了。
真妃儿:
他是我的——
谁也不会来把他赶走的!
啊呀,已经是太晚了……
弯弯的月亮落山了,
田地都已经给雾盖住了。
——
梦魔来了,我真熬不住了。
天亮了。老头儿轻轻的
绕着那个没有声音的
篷帐走着。“起来吧,
真妃儿,太阳也出山了;
我的客人,醒醒吧!
孩子们,好梦别太贪了。”
大家都起身了,好热闹;
篷帐拆了,车子准备好,
这么一大群的人
大家一块儿动身,
那好空旷的平原上,
后面老的少的,家婆男女,
前面还有小孩子,骑着驴:
驴背上背两个大筐
一边一个的挂着,
孩子在里面耍着,
叫唤着,闹着,
茨冈在歌唱着,
熊也在叫着,
它的锁链响着;
花花绿绿的是破烂的衣服,
小孩子老头儿还光着脊骨;
狗的叫声、咬声,人说话的声音,
还有咿咿呀呀的车子的声音。
这是多么烦杂,多么野腔野调,
可是,一切都活泼泼地安静不了,
没有我们那种死沉沉的情调,
没有那样的安闲生活的单调,
——只有奴隶的歌谣
才会单调和无聊。
——
尽看着那空旷的荒地
那年轻人是在烦闷,
忧愁的原因好秘密,
自己都不敢问一问。
现在他是个世界上的自由人。
黑眼睛的真妃陪着他,
太阳也很快乐的照着他,
中午的阳光美丽得那么爱人。
年轻人的心可还在跳动,
他担心着什么,这样心痛?
你看吧,看那上帝的鸟儿,
它不用劳动也不用担心,
夜长呢,树枝上睡个觉儿,
哪儿为着做窝儿去操心。
太阳出来了,
拍拍翅膀就要飞的。
鸟儿唱开了,
好嗓子是上帝给的。
春天景致是最好,
等到热过了一个夏天,
晚秋就又是雾又是烟,
人要苦闷要烦躁,
鸟儿可远远的飞去了,
飞过苍茫的大海,
飞到暖和的天边去了,
等到了春天再来。
他也是只无忧无虑的鸟,
给人赶出来了,到处漂流,
靠得住的巢儿,向来没有,
无论什么,他一概受不了。
四面八方,哪儿都是他的路,
到处的草堆都算是他的床,
朝晨醒来,听那上帝的调度,
一天到晚就这么吊儿郎当。
要过活固然
总要用些心机,
可是他的懒
使他死心塌地。
神妙的福星,有时候
意外的降临,他要有
这样偶然的运气
就过得堂皇富丽;
孤零零的他,
头上也不止打过一次焦雷。
可是他管吗?
他总是马马虎虎倒头就睡。
就这样过活,
管不了许多,
看那瞎了眼的命运
究竟有多大的本领!
然而他的情爱,
触过他的心神,
那是多么难挨,
满腔都在沸腾!
这样的日子过去了有多久,
就算安静了是不是能长久?
那情爱总是又要醒的:
等着吧,不给你放心的。
真妃儿:
好朋友,你讲吧,
你拿掉了那些,
有点儿可惜吧?
阿乐哥:
我拿掉的哪些?
真妃儿:
你自己懂得——
那些故乡的人,
还有故乡的
城市。
阿乐哥:
要可惜人?
可惜什么?
你也知道
你想得到
那是什么?
那沉闷的城市,
不自由有的是!
那里的人要成堆,
四面围着了堡垒,
朝晨也没有爽快的呼吸,
没有青春的草地的气息。
他们爱呢,又要害羞,
思想也要赶走,
出卖着自己的自由,
对着偶像叩头;
讨那一点儿钱
还带一根锁链。
我丢了什么?是卖朋友的干活,
是那些发疯似的要钱的家伙,
是荒谬绝伦的判决词,
还是耀武扬威的羞耻?
真妃儿:
然而那个有大的宫殿,
有的是那花花绿绿的地毯,
热闹的玩意儿,还有酒宴,
姑娘们的打扮是那么好看!
阿乐哥:
城里面的热闹那又有什么快乐?
哪儿没有爱情,哪儿就没有快乐!
娘儿们呢……你没有她们的
珠宝跟首饰,没有她们的
贵重装饰,还比她们强呢!
你不要变心,我的亲爱的!
我……就只有一个心愿——
要给你爱情,
要跟你散心,
就流落也甘心情愿。
老头儿:
孩子,你倒还爱我们,
虽然出身是个富人;
可是谁要是享惯了福
自由就不一定是舒服。
我们这里好久就有一个传说:
皇帝把一个人赶了出来,
叫他来到这里过流浪的生活
(他叫什么,我可记不起来,
虽然我以前知道他的贵姓大名),
他自己已经上了年纪,
可是他的好心,却又活泼又年轻;
他的嗓子可来得稀奇,
像流水的声音那样潇洒,
真有点儿唱歌儿的天才,
大家都爱上了他;
他就在那敦奈河边儿住下,
谁也不肯得罪,
他只爱讲故事,真叫人舍不下。
他是什么也不想,
又胆小又没力量,
真像个小孩子
只等着吃奶子;
打猎捉鱼,都是别人替他干,
河里冻了冰,那可是真为难:
冬天的大风雪,呼拉呼拉的吹着
一层层蓬蓬松松的雪花儿盖着,——
盖着这神圣的老头:
可是,他仍旧不能够
自己关心自己生活的贫苦,
东飘西荡,他脸是那么干枯。
他说这是上帝的震怒,
罚他的罪过,叫他受苦。
他尽在等着饶恕,
可怜呵,总是愁苦;
就这么沿着敦奈河流荡,
多少痛苦的眼泪流得那么冤;
还在那儿回想了又回想,——
想自己的城市是离得那么远……
他死的时候,
悲伤的朋友
还听见了他的遗嘱:
请他们把他的尸骨
一定要送到南边去安葬,——
死都记得这是他的外乡。
阿乐哥:
噢,罗马,噢,伟大的国家,
这就是你子孙的命穷!
爱情的,天神的歌曲家,
请你说吧:什么是光荣?
是坟墓上的呼号,
歌功颂德的热闹,
一代一代传下去的声名?
还是在草堆里借树荫,
支起烟雾沉沉的篷帐,
听说故事的野蛮茨冈?
——
过了两年。这些和平的茨冈
仍旧是那样成群的流浪,
照旧是那处欢迎,
那处有的是安静。
阿乐哥抛弃了那锁链似的文明,
自由自在,和他们一样,
没有什么可惜,也没有什么担心,
就这么一天天的流荡。
仍旧是那样的他,
仍旧是那样的一家;
以前的事情,
甚至于忘完了;
茨冈的生活
他已经过惯了。
他爱他过夜的草堆,
爱那永久的懒惰的沉醉,
爱他们讲话的腔调,
又响亮又那么单调。
那个毛茸茸的熊,
丢掉了自己的洞,
也住在他的篷帐,
倒像个客人模样,
沿着荒郊野地的道路,
靠近莫尔多人的院子
它就在村庄上去跳舞,
一群人围了一个圈子,
人家小心珍重的,
它不臃臃肿肿的,
又那么哼哼的叫着,
把陈旧的锁链咬着。
老头儿撑着旅行的手杖,
懒懒地敲着鼓儿;
阿乐哥唱着歌儿,
牵着那个熊儿,讨点儿赏——
丢一个圈子,可要难为真妃——
去收大家的钱,谁愿意就给……
晚上来了,他们三个人一块儿
煮着人家没有收割的小麦;
老头儿睡着了——什么都安静了……
篷帐里静悄悄的,那么乌黑。
——
老头儿的血已经快要冻了
想一想那青春的太阳
暖和一下吧,女儿可唱动了,
她靠着摇篮就那么唱;
她唱她的爱情,
叫阿乐哥寒心,
阿乐哥的脸
苍白的可怜。
真妃儿唱:
“我的老丈夫,
可怕的丈夫,
你就是斫我,你就是烧我,
我不怕刀,我不怕火,
我的心肠铁硬,
看见你就要恨;
我爱了另外一个他,
就是死,我也要爱着他。”
阿乐哥:
别做声,唱歌真叫我厌烦,
这样的野腔调,我不喜欢。
真妃儿:
你不喜欢?那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唱我的歌儿,我唱给我自己听。
“你就是斫我,你是就烧我,
我可是什么也不说。
我的老丈夫,
可怕的丈夫,
你不会知道他,
你别想知道他
他比春天还新鲜,他比夏天还热烈;
他是多么爱我!多么勇敢,多么年轻!
那天悄悄的晚上,我和他多么亲昵!
说起你的花白头发,我还笑得要命。”
阿乐哥:
别做声,真妃儿,我满意……
真妃儿:
我的歌儿,你懂了没有?
阿乐哥:
真妃儿……
真妃儿:
我唱的就是你,
你要生气,有你的自由。
(她走开唱着“我的老丈夫”等等。)
老头儿:
对了,对了,我记得了;这一首歌儿
还是在我们的时候唱起的头儿,
就这么唱着好玩,
大家都已经听惯了。
从前在卡古尔的荒野,
流浪着的冬天的长夜,
我的马提亚对着火儿,
摇着女儿唱这首歌儿。
过去的那些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