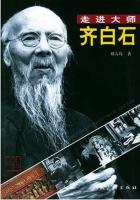“我知道,不过这儿有一个从监狱里调来担任杂差的女助理护士。”
“对,这样的人这儿有两个。那么您有什么事?”
“我跟其中的一个,跟马斯洛娃熟识。”聂赫留朵夫说,“现在我想跟她见一见面,我就要到彼得堡去为她的案子上诉。喏,我还打算把这个东西交给她。这不过是一张照片。”聂赫留朵夫从衣袋里拿出一个信封来说。
“哦,这倒可以。”医师说,态度缓和下来,转过身去吩咐一个系白围裙的老太婆把担任杂差的女助理护士马斯洛娃叫来,“您要不要在这儿坐一下?到接待室去也成。”
“谢谢您。”聂赫留朵夫说着,趁医师对他的态度有了好意的转变,就问他对马斯洛娃在医院里的工作是否满意。
“还好。如果考虑到她过去在什么条件下生活,那就应当说她工作得不坏。”医师说,“不过,现在她来了。”
那个年老的女助理护士从一个房门里走过来,她身后紧跟着马斯洛娃。她穿着一件条子花的连衣裙,外面系着白围裙,头上扎着三角头巾,盖住了头发。她见到聂赫留朵夫,就涨红了脸,仿佛犹豫不定似地停住脚步,然后皱起眉头,低下眼睛,迈着很快的步子沿着过道里铺的长地毯向他跟前走过来。她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本来不想跟他握手,后来还是伸出手握了一下,她的脸涨得越发红了。自从上一次他们谈话,她因为自己发脾气而道过歉以后,聂赫留朵夫一直没有见过她,现在料想她的心情会跟上次一样。可是今天她却完全换了一个样子,脸上有那么一些新的表情:拘谨,腼腆,聂赫留朵夫觉得她似乎对他抱着反感。他把刚才对医师所说的话又说了一遍,讲到他就要到彼得堡去,然后交给她一个信封,里边装着他从帕诺沃带回来的照片。
“这是我在帕诺沃找到的,是一张很久以前的照片。也许您会喜欢它。您就收下吧。”
她轻轻扬起黑眉毛,用她那斜睨的眼睛惊讶地瞅着他,仿佛在问这是什么意思。然后她一言不发地接过那个信封,把它放在她的围裙里边。
“我在那儿见到了您的姨妈。”聂赫留朵夫说。
“是吗?”她冷冷地说。
“您在这儿过得好吗?”聂赫留朵夫问。
“没什么,挺好。”她说。
“不太苦吗?”
“不,不算苦。不过我还没过惯。”
“我为您很高兴。这儿总比那边好。”
“‘那边’是哪边?”她说,她脸上泛起了红晕。
“那边就是监狱里。”聂赫留朵夫连忙解释说。
“这儿好在哪儿呢?”她问。
“我想,这儿的人好一点。他们跟那边的人不一样。”
“那边有许多好人。”她说。
“我已经为梅尼绍夫母子的案子张罗过。我希望他们会放出去。”聂赫留朵夫说。
“求上帝保佑,能这样才好。她真是一个很好的老太婆。”她说,又讲起她对那个老太婆的看法,微微一笑。
“今天我就要到彼得堡去。您的案子会很快受理。我希望原判会撤消。”
“撤消也罢,不撤消也罢,如今在我都是一样。”她说。
“您说‘如今’是什么意思?”
“我只是随便说说的。”她说着,用探问的眼光瞧一眼他的脸。
聂赫留朵夫把这句话和这种眼光理解成她想知道他究竟是仍然坚持他的决定呢,还是接受她的拒绝而改变了他的决定。
“我不知道为什么您觉得都一样。”他说,“不过对我来说,您无罪释放也好,不释放也好,倒确实是一样。不管情况怎么样,我都准备按照我说过的去做。”他坚定地说。
她抬起头来,她那对斜睨的黑眼睛又像是瞅着他的睑,又像是瞅着他的身后,她的整个脸上洋溢着快活的神情。不过她嘴里所说的话却跟她眼睛所说的完全不同。
“您不该说这样的话。”她说。
“我说这话是让您明白我的心意。”
“关于这件事,话已经说尽,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她说着,尽力地忍住笑容。
病室里不知为什么乱哄哄的。传来孩子的啼哭声。
“好像他们在叫我。”她说,心神不宁地回过头去看一下。
“好,那么再见。”他说。
她假装没有看见他伸过来的手。她没有握他的手就转过身,极力遮盖住她的欢乐心情,顺着过道上的长地毯快步走去。
“她究竟起了什么变化?她在怎样想?她有什么样的心情?她是打算考验我呢,还是真的不能原谅我?她是没法把她所想的和所感到的都说出来呢,还是不愿意说出来?她是心肠软下来了呢,还是怀恨在心?”聂赫留朵夫问自己,可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答案。只有一点他是知道的,那就是她变了,她正在发生对她的灵魂来说很重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不但把他同她联结在一起,而且把他同促成这个变化的人联结在一起。这样的联结使得他欢快而激动,心里充满温情。
马斯洛娃回到病室里,那儿有八张儿童小病床。她听从护士的吩咐,开始整理一张床上的被褥。她铺床单的时候把腰弯得太厉害,脚底下一滑,几乎摔了一交。有一个病后正在复原、脖子上扎着绷带的男孩瞧着她,笑起来,马斯洛娃再也忍不住,就往床边上一坐,扬声大笑起来,笑得那么感染人,惹得好几个孩子也哈哈大笑。那个护士生气地对她嚷道:
“你笑什么?你当是你还待在你以前待过的那个地方吗!去取饭来。”
马斯洛娃止住笑,拿起食具走了,到护士吩咐她去的地方去了。可是她临走,跟那个扎着绷带、医师不准他笑的男孩互相看一眼,又扑嗤一声笑出来。这一天,每逢马斯洛娃独自一人待在房间里,有好几次她从那个信封里把照片拉出一点,观摩一下。可是一直到晚上下了班,回到她跟一个助理护士同住的房间,独自一人待在那儿,她才从信封里把那张照片完全抽出来,用爱抚的目光一动不动地盯了好久,仔细地瞧着那几张脸、他们穿的衣服、露台的台阶和灌木丛,而他的脸、她的脸、两个姑姑的脸都是以那个灌木丛为背景的。她看着这张褪色和发黄的照片,总也看不够,特别是对她自己和她那张年轻、美丽、额头上飘着鬈发的脸庞看得入神了。她看得那么专心,竟然没有留意到跟她同住的助理护士走进房来。
“这是什么?是他给你的吗?”身体结实,脾气温和的助理护士弯下腰来,看着照片说:“莫非这个人就是你?”
“不是我又是谁呢?”马斯洛娃瞧着她的同屋伙伴的脸,笑吟吟地说。
“那么这个人是谁?就是他?还有,这个人是他的母亲吧?”
“这是他的姑姑。难道你认不出我了?”马斯洛娃问。
“怎么认得出来呢?我说什么也认不出来了。整个脸完全是另一个样子。话说回来,我看,从那时候起到现在恐怕有十年了吧!”
“不是多少年,而是一辈子。”马斯洛娃说,突然她原来的愉快心情完全消散了。她的脸色变得凄凉,两道浓眉中间嵌进一条皱纹。
“怎么呢,那边的生活一定很轻松啊。”
“是啊,轻松。”马斯洛娃跟着说一遍,闭上眼睛,摇摇头,“比做苦工还不如哟。”
“怎么会呢?”
“就是这样。从傍晚八点钟起到凌晨四点钟正。天天如此。”
“那她们为什么不丢开那种生活呢?”
“她们倒是想丢开,可是办不到。不过,说这些有什么意思!”马斯洛娃说着,霍地站起来,把照片丢在小桌子的抽屉里,勉强忍住气愤的眼泪,跑到外面过道上,砰的一声带上身后的门。起初,她瞧着照片,觉得自己就是照片上那个人,梦一般地想着她那时候多么幸福,想着现在跟他在一起也还是能够幸福。她的同屋人的话却使她想起她现在是个什么样的人,想起在那边她做过什么样的人,总之使她想起过去生活中可怕的情景,而这以前她只是隐约地感觉到,却不容许自己去清楚地领会的。直到现在,她才清楚地想起所有那些可怕的夜晚,特别是想起一个谢肉节的夜晚,她等候一个应许给她赎身的大学生。她想起当时她穿着一件沾了酒迹的、敞着领口的红缎子连衣裙,蓬松的头发上扎着一个红花结,身子疲乏,衰弱无力,喝得醉醺醺的,到深夜两点钟才把客人们送走,趁跳舞休息下来,就在为小提琴伴奏的女钢琴师身边坐下,那女人生得精瘦,皮包骨头,脸上长着紫疱。她开始对女钢琴师抱怨她的生活多么苦恼,女钢琴师也说她厌恶她自己的地位,打算改变一下。正在这个时候克拉拉走到她们跟前来,她们三个就突然决定一齐丢开这种生活。她们以为今天这个夜晚已经结束了,刚要走散,不料前厅里忽然来了些醉醺醺的客人,声音嘈杂。小提琴师就奏起舞蹈的序曲,女钢琴师就使劲按响琴键,弹着卡德里尔舞曲第一节,用的是一个极其欢畅的俄罗斯歌的曲调。有一个身材矮小、脸上冒汗的男人,嘴里喷出酒臭气,身上穿着燕尾服,扎着白领结,不住打嗝,等舞曲奏到第二节,就脱掉燕尾服,走到她面前,搂住她的腰。另一个留着大胡子的胖子,也穿着燕尾服(他们刚从一个舞会上出来),搂住克拉拉。于是他们跳舞,旋转,嚷叫,喝酒,闹了很久……就这样,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三年过去了。她的相貌怎么会不变!而这一切的起因就是他。她心里突然又生出她原先对他的愤恨,一心想辱骂他,责备他。她后悔今天错过机会没有向他再说一遍:她明白他是个什么人,决不会对他让步,决不容许他像从前在肉体上使用她那样现在又在精神上使用她,决不容许他把她变成他表现宽宏大量的对象。她又是怜惜自己,又是无益地责难他,为了扑灭这种苦恼的心境而很想喝酒。要是如今她在监狱里,她就会守不住她的诺言,喝起酒来。然而,在这儿是找不到酒的,只有医士那儿才有,可是她怕那个医士,因为他不断调戏她。可是现在她厌恶那种跟男人的关系了。她在过道里一条长凳上坐一阵,就回到小屋,没有回答同屋人问她的话,为自己的坎坷身世哭了很久。
……
(六)
聂赫留朵夫回到莫斯科以后,头一件事就是到监狱医院里去,把枢密院核准法庭的原判这个可悲的消息通知马斯洛娃,告诉她现在要准备动身到西伯利亚去了。
递交最高当局的状子,已经由律师为他写好,现在他把状子带到监狱里去让马斯洛娃签字,不过他对这个状子所抱的希望很小。再者,说来奇怪,他现在也不希望成功。他已经为西伯利亚之行,为他在流放犯和苦役犯当中生活做好了思想准备,如果马斯洛娃无罪释放,他倒难于想象他应该怎样安排他的生活和她的生活了。他想起美国作家托罗的话,托罗在美国还有奴隶制度的时候说过,在一个使得奴隶制度合法化并巨维护奴隶制度的国家里,正直的公民惟一适当的去处,就是监狱。聂赫留朵夫,特别是在他到彼得堡去过一趟,在那儿见到种种情况以后,恰好产生了同样的想法。
“是啊,在当代的俄国,正直的人惟一适当的去处,就是监狱!”他想。他坐着马车来到监狱,走进监狱围墙的时候,甚至直接体验到这一点了。
医院的看门人认出聂赫留朵夫以后,立刻通知他说,马斯洛娃已经不在他们这儿了。
“那她到哪儿去了?”
“又到监牢里去了。”
“可是为什么把她调走呢?”聂赫留朵夫问。
“她本来就是那么一号人嘛,老爷。”看门人说,鄙夷地笑了笑,“她跟一个医士吊膀子,主任医师就把她打发走了。”
聂赫留朵夫万万没有料到马斯洛娃和她的精神状态竟然同他这样密切相关。这个消息使得他愣住了。他心里的感触近似于人们听到意外的大祸临头的消息以后所生出的那种感触。他心里很难过。他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产生的头一种心情,就是羞愧。首先他觉得自己可笑,因为他居然高高兴兴地认为她的精神状态似乎起了变化。所有她那些不愿意接受他的牺牲的话,那些责备、那些眼泪,总之所有那些东西,他暗想,无非是一个心地已经变坏的女人的狡猾手段,打算尽可能地利用他罢了。现在,他觉得在上一次探监的时候,好像已经看出她有种种的迹象表明她不可救药,如今果然暴露出来了。所有这些想法,都是在他本能地戴上帽子,从医院里走出来的时候,掠过他的脑海的。
“可是现在怎么办呢?”他问自己,“我还要跟她拴在一起吗?现在她既然有了这种行为,我岂不是自由了吗?”他问自己。
不过他刚刚对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就顿时明白过来:他认为自己已经自由而抛弃她,那他所惩罚的并不是他想惩罚的她,却是他自己。他就心惊胆战了。
“不!她发生这件事,不能够改变我的决心,只能够坚定我的决心。她顺应她的精神状态爱做什么,就由她去做好了,她要跟医士调情就随她去跟医士调情,那是她的事……我的本分却是做我的良心要求我做的事。”他对自己说,“我的良心要求我牺牲我的自由来赎我的罪。我已经决定同她结婚,哪怕只是形式上的结合也未尝不可,而且我已经决定跟她走,不管她流放到哪儿去都一样,那么现在我的决心就绝不会改变。”他带着誓不罢休的执拗心情对自己说着,走出医院,迈着果断的步子向监狱大门走去。
他来到大门跟前,要求值班看守去报告狱长,说他希望同马斯洛娃见面。值班看守认得聂赫留朵夫,就好像见了熟人一样,告诉了他一件监狱里的重大新闻说,原先的上尉已经免职,由另外一个严厉的长官接替了他的职位了。
“现在办事严起来了,严得不得了。”看守说,“现在他就在里边,我马上去报告。”
果然,狱长就在监狱里,不多久走出来同聂赫留朵夫见面。新的狱长个子很高,骨瘦如柴,两颊的颧骨突出,动作很缓慢,神色阴沉。
“只有规定的日子才允许在探监室里跟犯人见面。”他说着,眼睛没有看聂赫留朵夫。
“可是我需要让她在一份递交最高当局的状子上签字。”
“您可以把它交给我。”
“我要亲自见一见这个女犯人。以前,我是素来得到许可的。”
“那是以前了。”狱长匆匆地瞟了聂赫留朵夫一眼,说道。
“我有省长发给我的许可证。”聂赫留朵夫坚持说,拿出他的皮夹来。
“请容许我看一下。”狱长说,仍旧没有看聂赫留朵夫的脸。他伸出又长又干瘪的白手指头,食指上戴着一个金戒指,接过聂赫留朵夫递给他的一张公文,慢吞吞地读了一遍,,“请您到办公室。”他说。
这次办公室里一个人也没有。狱长靠着一张桌子坐下,翻看桌上放着的公文,显然准备在他们会面的时候留在这里。聂赫留朵夫问他,能不能同女政治犯博戈杜霍夫斯卡娅见面。狱长干脆地回答说不行。
“同政治犯见面是不许可的。”他说,又埋下头去看公文。”
聂赫留朵夫衣袋里装着那封打算交给博戈杜霍夫斯卡娅的信,感到他的处境像是一个正在打算犯法的人,不料他的预谋被揭穿,遭到了挫败似的。
等到马斯洛娃走进办公室,狱长就抬起头来,没看马斯洛娃,也没看聂赫留朵夫,只是说一声:
“可以谈话了!”说完,他就继续专心地看公文。
马斯洛娃又是从前那样的装束,穿着白上衣和白裙子,扎着白头巾。她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看见他那冷冰冰的、气愤的脸色,就涨得满脸通红,不住用手指摸索上衣的底边,低下眼睛。她的窘态,依聂赫留朵夫看来,证实了医院看门人的话。
聂赫留朵夫有心像上次那样对待她,然而他不能够照他所打算做的那样伸出手去同她握手,现在她在他的心目中变得极其讨厌了。
“我给您带来一个坏消息。”他用平稳的声调说,没有看她,也没有朝她伸出手去,“枢密院把上诉驳回了。”
“我早就知道会这样。”她说着,声调奇怪,仿佛在喘气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