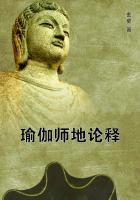不知过了多久,虞珮耳畔传来打斗的声音,蹭蹭地兵器碰撞声吓得她一颤,眼睛微睁,白亮的剑光划过,她赶紧继续闭眼。
这都是什么地方?战场不成?乱世?想到她睁眼所看见的打斗,她决定先装死。她可不要被当成敌人給误杀了。
如果她没有记错,刚刚系统说目的地是南国,那么,从某个角度来说,她应该算是南国人!她目前所在的位置也应该是南国才对!这样来看,在南国的土地上,应该是南国人更占优势,可是,这两方哪一方才是南国一方呢?
虞珮陷入了苦恼。她分不清敌友。
来不及想清楚,弄明白,一个重物突然死压在虞珮身上。好重!虞珮在心中呐喊,不知是哪个倒霉鬼被杀了,恰好又被扔在她身上。五脏六腑颤抖的感觉,直让人想将肠子肺腑全都吐出来。
被压的难受劲还没过,虞珮又感觉到一股带着腥味的热流从手臂流过。一抖擞,不是血是什么?她忍。
一阵脚步声整齐有序地向打斗方向行来,不一会儿,一人铿锵有力道:“左祁,不要反抗了,带着你的部下赶紧投降,我还能求皇上给你们个痛快!”
“呵呵!是吗?”叫左祁的反问道。
“那当然,我石筌说话算话!”
“你的话能听就奇了怪了!”又一个声音响起,不过腔调略显粗犷。
“石将军,不要根他们废话,这群叛逆者早该死了!”一个士兵恶狠狠地说道。
“哼!今天就是你们的死期,过不了多久便是湛陵阳的死期!”石筌举起右手下令,“将这群叛逆者一网打尽,一个活口不留,杀!”
一群兵器碰撞声再次响起,只是比最初强了不少。
虞珮躺在那儿装死,脚步声从她耳畔整齐划一地跑过。
点点冷汗冒出,吓得她凝神屏息,生怕被发现或是被踩着后被发现……
弄了半天,虞珮才知道自己白想了那么久,原来这两方都是南国人,这是统治者与反叛者之间的争斗,用虞珮的话来说,算是内讧。
感觉打斗声离自己越来越远,虞珮便起了逃跑的念头。此时不跑,更待何时?万一他们打完了收拾尸体时发现她是活的怎么办?给补上一刀可就不好玩儿了,那她便是实实在在的尸体了。
思及此,虞珮微睁开双眼,试图看一看周围的情况。瞬间瞪大眼,这就一个比较大的露天庭院罢了,也是她多想,以为是沙场一类,还得自己想办法找路。
虞珮估了一下,离她最近的士兵大约有十米远,好机会。虞珮一把推开身上压着的士兵,从地上爬起来,也顾不得擦拭手臂上的鲜血,拔腿就准备开溜。
一步,两步,一股力道突然猛地拉虞珮的胳膊,虞珮一个不稳,便向后栽倒在地,待她反应过来,脖子上已经感受到了一丝冰凉。
虞珮一愣,侧眸一瞧,一柄利剑恰好横在自己脖子上。
持着剑的人一声不吭,眼角上扬,定定地从上到下将虞珮端详一番,金色瞳孔渐渐变得深不见底。
虞珮侧眸瞧着,乍然一看间,心神便被眼前的一双瞳孔给吸了去,金瞳妖冶,却被眼前之人内敛,妖冶中凭多出几分深沉,五官精致,让人挪不开眼。
那张脸一笑,明明可以颠倒众生,却偏偏……死气沉沉地……将她看着!
“你看够了没?”虞珮没好气地瞪着眼前持剑人。
宽大的紫色衣袍穿在持剑的男子身上,将男子的身形完全裹住,也显得瘦削,然而与那把闪着寒光的利剑搭在一块儿,则显得那么地格格不入。
男子眼神扫过虞珮的眼,这双眼纯粹地黑,纯清亮泽,望向他的时候,他清晰地在她眼中看到了不屑。
男子顿了顿,哼笑了声,“看人的是我,与姑娘何干?”
虞珮瞟了眼挂在自个儿脖子上的剑,将白眼生生的给憋了回去。真是应了那句古话,“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看得是她,岂能与她无关?还是说……在他眼中,只要自己想做,便没有别人不同意或是反驳的梗。
若是如此,这人也太过目中无人了些。
虞珮歪头看他,见他神色如常。伸出手指搭在剑上,向自个儿脖子的反方向推。
男子眼神一闪,却是没动。
推了几下,见剑依然紧贴着自己脖子,虞珮眼底黯了黯,拿下手。看男子蛮单薄,然那手劲儿真是没话说。她那般用力,剑竟是纹丝不动。
这样一来,也就消了逃跑的念头。
男子眼角溢出一丝笑意,金瞳一闪,波光流转,宛如落在凡间的妖孽,似邪非邪。
虞珮愣愣地定在那儿,暗骂自己无用,抬眸瞪了男子一眼。
男子止了笑,嘴角却仍带三分上扬,“你想让我放了你?”反问的话被他说得肯定十足。
虞珮嘴角一撇,“换你来?”你被人用剑抵着脖子试试?
没听见吭声,脖子上一轻,那把剑从虞珮的视线中消失。
对上虞珮疑惑的目光,男子轻笑,“我不需要。”
他的确不需要。不需要向虞珮证明什么,也不需要虞珮放过他。而虞珮却需要证明她的身份,一个不在男子对立面的身份。
身后的打斗声顿然停止,虞珮扭头看去,场中白烟弥漫,凭借着超于常人的视力,隐约间可见一片青色的衣衫下摆,在烟雾中消失。
听得石荃一声粗暴的嗓音:“妈的!居然放烟雾弹跑了!”
烟雾消散一半,“追!别让他们跑了!抓一个赏十金!”
虞珮再扭头过来,眼前的紫衣男子已然消失不见。
待到烟雾完全消散,虞珮定睛一瞧,院中零零散散摞了一堆尸体,横七竖八,血液肆流。
忍不住哆嗦,心中一阵恶寒。
只是在一个庭院中就能逝去那么多人,若是在战场上呢?真正的两军交战,哪个不是上万的兵马?算下来,岂不是更多!虞珮不敢想象。
她不是悲天悯人的人,也不是同情心泛滥之辈,只是单纯地觉得,战争无情罢了。
庭院中弥漫着一股血腥的气味,虞珮低头看着自个儿手臂上已经干涸的鲜血,强压着呕意,用故去士兵未沾血的衣角将手臂上的鲜血抹去,直到擦到手臂泛红,她才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