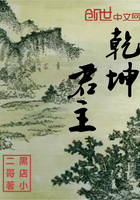那年月兵荒马乱灾祸连连,四里八乡的人纷纷背井离乡讨生活,好多人活活饿死在路上做了他乡野鬼,可就是这样外出的人还是接二连三的,因为待在家里饿死的更多,而我们村里的人却没有离开家乡一步。
我们村一眼望去四面白茫茫一片全是水,村子就像汪洋中的一条船,水里有数不尽的鱼、藕、慈菇、菱角,这就是大伙活命的本钱,浅水处还生生不息地长着一眼望不到头的菖蒲芦苇,它们可以用来编席子、篮子、帘子,好换点油盐,所以尽管外面风雨飘摇,大伙还是稀一顿稠一顿地侥幸活了下来。
乱世之中有这么一处地方自然成了人人眼红的风水宝地,不久远近饿急了的人开始来偷,才开始村里人尚不以为意,认为水里的东西是吃不尽用不完的,他又能偷多少?可时间一长村里人发现满不是这回事,金山再高也有挖光的时候,再这样下去自个的生存将受到越来越大的挤压,毕竟乱世里自保才是第一位的,于是族长马五爷发出号令:成立护荡队,誓死捍卫这碗饭。为了防止有人私下里同情、接济外乡人导致后果不可收拾,马五爷还订立了相当残酷的铁规矩。
护荡队由清一色的男子组成,个个人高马大孔武有力,他们撑着小船带着家伙时时刻刻在水荡里巡逻游弋。那船与别处不同,一眼看去就像饺子一样又细又长两头尖翘,不识水性的人若是冒里冒失地一脚踏上船这头,船那头便会高高翘起来,像要覆过来一样,把个人吓得半死,实际上这船又平稳又轻便,水乡人用长篙一撑短橹一摇,船便会像箭似地往前飞蹿,它是水乡人出门必备的工具。这种船也只有水乡人会做会驾驭,外地方的船总是又大又笨,速度跟小船没法比。
仗着船快,更仗着水乡人的强悍,一时鱼虾蒲苇被偷的事件少了许多,大伙正庆幸,哪知这天马二哥竟遇上了这么一个胆大包天的贼。
那天是马二哥巡逻,正是盛夏时节,微风贴着水面迎面吹来,送来一阵阵清凉凉的水汽,还裹着荷花、菱角花和各种水生植物的清香,各色水鸟在碧绿的高高的芦苇丛中自由自在高低掠飞,时不时有大鱼跃出水面,发出“泼剌剌”的一声响。马二哥坐在船尾用短橹不急不慢心情颇好地划着水,那尖尖的船儿便在一道道迷宫似的水巷里悄无声息地绕来绕去,当拐过一个大弯时马二哥大吃一惊,前面竟有一船一人!
船是条宽头宽尾粗大笨拙的外乡船,此时舱中一大半码放着绿蒲,一小半是白嫩粗大的荷藕;人和马二哥差不多岁数,二十五六的样子,光着个上身,肋骨根根可数,显然挨饿不是一天了,乌黑的湿淋淋的皮肤被太阳一晒亮晶晶的。
碰到贼了!马二哥手疾眼快,一把抄起用来打野鸭大雁的鸟铳,手搭扳机大喝一声:“别动,动就打死你,跟我进村!”
见马二哥神兵天降威风凛凛,那贼的一张黑脸吓得煞白,双眼直盯着马二哥却既不求饶也不反抗,反抗是没用的,马二哥的块头比他大多了,何况手中还有一支枪,实际上马二哥也是十里八乡最有名的生死不惧血气刚猛的汉子。只见那贼神态平静地说了一句话:“丫头快要饿死了,我没办法!”
马二哥没听清,又喝问一遍:“你叽咕什么?快跟我走!”
那精瘦的贼还是平静地重复道:“刚生的丫头要饿死了,我真的没办法,你让我把这船东西送回去救她们娘儿俩两条命,我就跟你走,要杀要剐随你,我说话算数!”
贼这样子竟是把他的生死置之度外了!马二哥这回听清了,慢慢的竟把枪口垂了下来,因为他想到了自个的儿子,他刚刚生了个大胖小子,是一家人的心头肉,更是马二哥的掌上明珠,现在听这贼这么一说向来刚强的他忽然软了心,都是刚刚做父亲的人啊,若是自个的儿子挨饿呢?可转念又想到马五爷的规矩不由得犯难了,左思右想翻腾了老半天终于长叹一声,挥挥手说声:“你走吧,不要让旁人看到——这是最后一次,下次再让我看到,可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那贼显然想不到马二哥竟然放他一马,顿时激动得浑身都哆嗦起来,回过神后火速掉了船头就走,一边走一边顺风撂下句话来:“我叫六指,因为右手天生多一指,你这大恩我日后是一定要报的。”
一晃又过去了好多节气,恍惚间已是深秋时节,秋风萧瑟百草枯黄,荡里的蒲早就给大伙割尽了,又给勤快的婆娘们全编成席子换了油盐,此时的荡里只剩下一排排像森林一样的干硬的芦苇,秋风一吹,满天芦花飞扬。这天马二哥撑起了新娘船,族长马五爷的孙子迎娶了外乡一个女孩,正是黄昏时候,马二哥和几个汉子卖力地撑着一条大船,船中坐着马五爷一大家和好多迎亲送亲的人们,新娘子自然坐在舱中,一身新衣一顶红盖头,世道更乱了,可人们还是要吃饭生存下去。一船人说说笑笑,向往着晚上到马五爷家海吃海喝一顿,还要闹他个天翻地覆,不提防间船行进了一段尤其杂乱静寂的水域中。
忽听得耳边一声尖利的呼啸,随即从芦苇丛里流星似地冲出几条小船来,船上人个个用黑布蒙着脸只露出一双双眼睛,齐刷刷地放声大叫:“快留下过路钱来!”
不好,遇见土匪了!片刻的慌乱之后马二哥他们几个男子汉并不示弱,飞速抄起鸟铳、长篙准备决一死战,这样的情形他们也不是第一次碰到了,水乡的长篙一头都包着尖锐的铁钻头,耍起来不亚于一支长矛。这时马五爷颤着声音开口了:“大伙不要乱来,他们人多家伙多,再说喜事大日的,不作兴流血!”
马二哥定睛一看,可不是嘛,只见四周围的小船上有好多支鸟铳正对着他们,蓄势待发,一旦打起来自家这边肯定不占上风。
这时当头一条小船上挺立一人喝道:“放下家伙,乖乖地把值钱的东西全交出来,我们只要钱不要命,不听话的话,那就命钱一齐收!”
马五爷面如死灰一挥手,马二哥只得恨恨地扔了手中长篙,大伙也双眼冒火地放下武器,舱中娇弱的新娘子早就吓得哭出声来,只听得大伙心里猫抓似的难受。这时那条当头小船已告拢来,只听“托”的一声响,那个打头的蒙面土匪伸手一按大船的船舷猱身跃上,右手一柄明晃晃的钢刀,左手一个篮子,吆喝道:“挨个把钱和值钱的东西放进篮子!”
大伙毫无办法,只得哭丧着脸掏出钱,连新娘子娘家人给的压箱子钱也掏了出来,当那蒙面人走到马二哥面前时马二哥双手握拳,膀子上脖子上青盘暴暴,咬牙说道:“我没钱,你看着办吧……”
却听得那土匪口中“咦”了一声,蒙着黑布的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然后听他问马二哥:“这船上是你什么人?”
马二哥没好气地回他:“是我兄弟娶的新娘子,怎么着?还打什么主意?”
那土匪看上去迟疑了一下,忽又放下已是满满当当的篮子,说声:“打扰了——还记得六指吗?”说着刀交左手摊开右手晃了晃,赫然六根手指头,然后纵身下了大船,对众强人说:“今天遇上朋友了,大伙让条道,”众强人一听轰然答应,小船一下子向两边分开,显然这家伙是他们的头。
眨眼间形势陡转,族长他们全愣住了,马二哥也愣住了,忽然明白过来,脸一下子涨得通红,厉声对那正要掉船离去的土匪头子,也就是六指喝道:“你等一下!”
六指一听马二哥的声调有点异常,便问:“你还有事吗?”谁知马二哥并不回答,而是大步走到族长面前,躬身说道:“族长,有件事我一直隐瞒住了没说,今天不得不说了——在夏天时我曾犯下大错!”
马五爷心里正高兴马二哥救了众人躲过一劫,一听这话大奇,问道:“你做得很好啊,我正要谢你哩,错什么错?”
马二哥一指那土匪头子六指,说:“夏天我巡逻时曾撞见他偷东西,可是我一时心软放过了他,五爷,现在请按规矩处罚我!”
众人一听脸色就变了,因为都知道私自放走贼的后果,那是要剁掉一个手指头的,却见马五爷沉吟着说:“即使真的如此,那……就功过相抵吧!”
马二哥却固执地摇摇头,说:“这是两码事,就是因为我当初放了他,他才得以存活下来从而做了土匪抢劫乡邻,这一切全是因我而起,我不仅没功反而有罪,所以必须受罚。”又掉头对那六指说道:“我当初救的是一个奄奄一息的女娃子的一家,而不是一个为害四乡的贼,早知今日,我是连一根芦柴、一段小藕也不会给你的,还有,今天你放了我,明日我却不会再放过你的。”说完再无二话,把左手食指伸出来搭在船沿上,右手一扬,“咚”的一声响,刀光血影中,那食指竟给一刀剁了下来直掉入河中。
四面的土匪们一时个个呆若木鸡,想不到马二哥是如此的血性、无畏,马五爷他们更是既吃惊又暗暗叫苦,心想你马二哥这不是没事找事吗?那六指既已放过咱们了,你又触犯他干什么?心里正怕着,却见那六指用力一拱手,说声:“好男儿,我今天承教了,”说罢掉船就走,一转眼的工夫就消失在茫茫的芦苇荡中了。
从此以后十里八乡就恢复了平静,再也没有土匪骚扰。
荡中菖蒲芦苇青了又黄黄了又青,也不知轮回了多少匝,这天马二爷的儿子娶亲,欢天喜地炸过鞭炮、拜过堂、小两口进了洞房,众人个个红脸关公似地散后,偌大的院子心里只剩下两人,一个是马二爷,另一个是他的亲家公。那亲家公喷着满口的酒气说:“这真是老天指定的姻缘,我那闺女注定是你家的人,因为就是你马二哥当年救了她的小命,嘿嘿,你那一根断指也救了我,不然的话我还不知怎么个下场哩。”
当年的马二哥,现在的马二爷也一脸醉意的笑。这两个人一个九根指头,一个却生了十一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