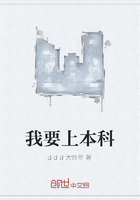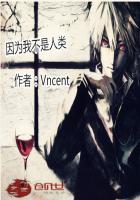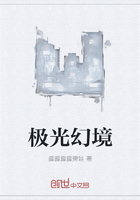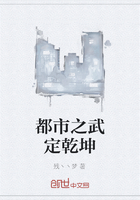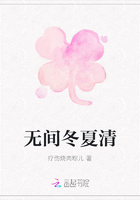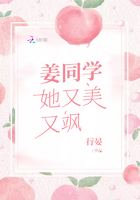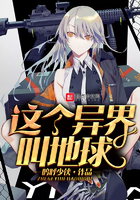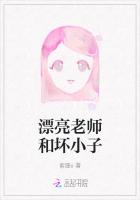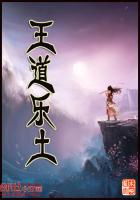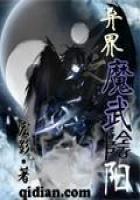大约在“文革”结束后的三五年间,具体应是公元1977-1982年,已记不得通过什么途径,知道并基本读全了中国古典小说集“三言二拍”。回想当时的心情是复杂矛盾的,因为总觉得那不是什么好书,其中诸多情节描述,对处于青春期的我而言,隐秘、新奇而刺激,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有意回避谈论此书。步入大学,或许学医的缘故吧,古今中外各色书籍多有涉猎,特别对“性”的朦胧及好奇渡过后,逐渐由痴迷文学转入冥思哲学、宗教性话题。也就在这一时期,头脑中经常纠缠着一些类似这样的问题:“中国话本小说中为何那么多涉及和尚、道士的故事呢?而故事中的僧尼为何多与神汉、媒婆、老鸨、盗贼沆瀣一气、令人不齿呢?”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步,新中国在“四清”、“文革”之中已经被砸烂捣毁、铲除殆尽的寺庙禅院,陆续又在黄河上下、大江南北的风水宝地、幽深僻静处,重生再建,生根开花了。现如今,不仅是凡名胜古迹处必能见到出家修行者的身影,即使在繁华都市、稠人广座之间,亦能觅得其足迹了。于是,一段时间以来,在我有着始终挥不去的这样子疑问:“儒、释、道在中国文化史中的地位孰重孰轻、利弊何在?其今天各自形制及发达有何价值和意义?”
戊子年春节假期,走亲访友间,徜徉书市,购得中华书局2007年1月北京第1版、季羡林著《佛教十五题》。每年正月里的光景,一贯是远实务而尚交情的,而吾性原本愚拙,近年交际愈稀,故多有空闲,得以静观其书。期间,却常有“耳目一新”、“茅塞顿开”之觉悟。
过去在探究民俗学之中,看到过利用溯求方言土语的特色,来考证文化风貌和历史形迹者。而今,在研究宗教哲学的著述中,能读到像季先生这样通过从语音学及经卷源流之中,发掘佛学/释教西来的路径,及其在中国变更演化之因由者,确乎少见,甚至未见。故于新颖感受之外,更因其研究方法的科学严谨而崇信。
一本书不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即使问题仅由某个人提出),但一本书能够引导某人或某些人,找准和最终解决了自我或同感或疑惑或困扰的问题。这样一种事实,虽不是俯拾皆是,但也应屡见不鲜。过去和现今的中国,都不乏研究和关注儒、释、道学问及其流派、思想和典籍的人们,对于其中诸多问题的解惑方法,见仁见智,也不足为怪。然而,凡学习者除了须有固有的虚心且具批判能力的眼光及态度外,如能总结心得并能够明了自我“心结”、“征候”得以解除的原委。那么,如此作为,起码从个人角度上,则是明确信念、坚强意志的物质和精神性财富。
前日朋友公司乔迁,有幸被邀,随喜。登其府邸,迎面所见,条几上供奉的已非财神,而是至尊如来了。问询朋友,何以如此?答曰:“信佛了。”
此段情节虽为个案,却也印证了季先生上文书中所论:“人之生存除物质生产和生产人(生育繁衍)的需要外,信仰则是不可或缺的……”
(2008年2月24日夜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