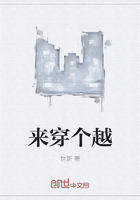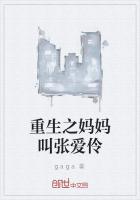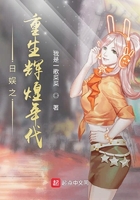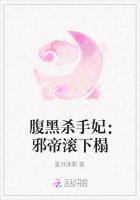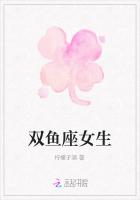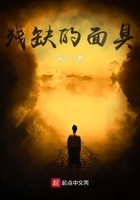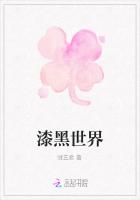“天涯”微论“水晶城堡”之中,我的拙文《“大学日记”摘抄(1989)》下面,因有在汉文书法方面颇有造诣的lfbifenban君的跟帖曰:“虽然和您有一定的年龄差距,但您所记录的点点滴滴尤其是您的所思所想,让我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如握,问好。”
鉴于我自己曾经夸下海口,在有些论坛中凡我的帖子下面,一旦有来言,则必须有回应的。所以,恰逢周末在家,针对原文章思路,附会网友跟帖,回复如下。又因整理独立成篇之故,略加充实。
lfbifenban老弟的这份感受,起码我自己不觉得意外。
因为,我们在年龄上虽有差距,但总是生活在同一时代里面。在当下这一时代里,近三十年来的经济生活变化是显而易见的,而这里面却有一种迟滞或言一直没有根本转变的东西,尤其自九十年代初至于今始终如一,这就是思想禁锢。那么,这里所谓的禁锢或说束缚、桎梏是如何表现的呢?其是有形还是无形的?其为蓄意营造,还是虚张声势,或就是无中生有?……其实,只要生活于我们这个时代,凡能够认真思考类似一些问题者,也就不难从现实生活中遇到并发现一些“相通”、“类似”或所谓“英雄所见略同”的看法、见解和认识。那么,又如何去看待存在于这些观点里面的诸多感慨、现象和问题呢?若是空泛说教,必定毫无意义。故下面举例说明吧。
我觉得针对上面“禁锢”的话题,能够比较真实且容易想象并形象地去说清楚的例子,莫过于清覆灭、民国初年之际,所谓“五四运动”为标记的新文化浪潮了,特别是其运动带给华夏大地一种有史以来最富有朝气和鲜活生命力的文化艺术和思想解放性质的群众性社会化实践。而这一社会实践活动,虽普及的不是完全彻底,但也确实算是具备了一定的广泛性;而这一实践活动的巨大成果,以我个人看法,未来的社会文明一定会给予更加客观而实际的评价,但其评价一定不会像今天一样:“一方面切齿痛恨封建专权的蛮横和残暴,而另一方面却欢呼雀跃朝代更迭,不加掩饰地吹捧和神化某些人物类似历来帝王将相般的奇才异能。”在未来文明的史册中,最可能浓墨重彩的会是廿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涌现出来的一大批各种领域的思想者以及各门类诸多艺术精品的社会价值和文化意义。
另外,虽说自古以来,任何社会的主流眼光和文化主题,总是围绕并主要聚焦在权势争斗的军事或政治舞台上面。但是,历史地去看,好像有一种社会现象确乎一直真实存在着,即愈是在所谓纷争战乱、风雨飘摇的年代里,往往才能够产出艺术佳作和人文典范。而这种像是艺术总是与政治、军事或经济状况,甚至与科学发达水平,都不怎么协调合拍的现象或问题。其究竟在启发和昭示着什么道理呢?其实,这一切也正表明了人类社会中的“艺术行为”有其独特的创作规律性。由此,再进一步研究,也就不难发现关于“艺术”这一独特规律性中的个性特点/本质/特质,则完全可以通过类似的每一时代中的经典作品内容及其作者之行为举止,来加以诠释,并给予分析说明。所以,也就是从这一角度和层面的研究而言,一切人文“艺术”之活得灵魂,也就是艺术的生命力,也可说艺术作品所产生的时代性社会价值和文化意义,其必定在于抗击一切没落、腐化、愚昧、懦弱和僵化的物质或精神性枷锁,其一定旨在唤醒人们追求光明、自由、公正、祥和之个性和社会生活的激情、热血及其行动。由此,也就不妨直言,艺术从来就是根植于现实生活,甚至从来就没有离不开过神仙皇帝或说一切富贵权势者的青睐、资助或迫害。但是,一切伟大的艺术佳作及其创作者,在其精神和骨子里面,也从来就没有投降或屈从过任何来自世俗的压力,尤其是来自权贵者的好恶或名利上的诱惑。而那些艺术大家及其作品内容,甚或作品中的人物,也一定总像是所谓的天马、神仙一样,超越了时空限制,在天地、苍穹或银河、宇宙之间,自由徜徉,指点江山;或如同幽灵、病毒一般,穿梭于自然世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在物质、精神或宏观、微观之中,明察秋毫、激扬文字。
是的,历史的进程“不可能”是一帆风顺。这儿的“不可能”,不仅仅因为社会前沿性人物的“艺术”思想高度如同其他领域的智慧头脑一样,即便在其个性化世界性问题的理论水平上已经达到了“思辨圆满”的高度,但世界上群体思想和自然与社会的整体物质水平,却不会因为思想家头脑中的“一厢情愿”,而在一夜之间达到相应的高度。于是地球上,也就必然会不时地在局部地区生活中出现文明程度的反复波动、复辟倒退和类似戏剧样式“历史惊人相似”的重复演出。针对这样一些历史倒退的社会事实,如果人们总是把其不良后果和责任一味推卸在过去人们的行为和思想身上,而不是科学地去分析其中的客观性因果和根源。那么,这样的群体文化思想如果不说是“极其反动和错误透顶”的话,也一定是处在一个十分低级的认知水平上面。
最后,因从lfbifenban老弟书法作品上,就我而言,虽说看不出艺术道路是否跌宕起伏的影踪,却看到了令我钦佩的超乎一般人的坚持、毅力和韧劲。所以下面,谈一点过去曾闲扯过的关于画家陈丹青先生关注过的“民国范”的话题。
就今天而言,如果没有真正接触过大约出生在1890-1920年之间的一代人,也就是那些身心经历过“五四”风潮直接或间接深刻影响的一拨人。眼下的人们,单凭想象一般是不容易去把握那一年代他们一般通过私塾、学堂、教会或各类识字班教育或有过拜师学艺、登门造访等经历而成就的文化人和工匠们的性格品质,特别是凝集于他们身上的一份固执、倔强、恬淡、坦然或可说成是一种骨气、傲气、涵养、洒脱、自负、自信样子的姿态和气度。而这样子的个性品质,起码在“文革”前后的各单位“军转干部”或近二三十年的“学员、学院派”领导身上,都是不容易看不到的。而在新中国,尤其眼下的基层领导们身上,所给予人们最“高大上”的形象,如果不再是“大老粗”或阳奉阴违的做派,也就剩下“服从、服从、绝对服从”或“先圆、后滑、再又圆又滑”的榜样力量了。
今晨起,见老弟跟帖,一日忙活家务,抽空书写上文。此刻斟酌再三,故贴之。诸多偏见,切磋而已。
(2014年11月8日星期六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