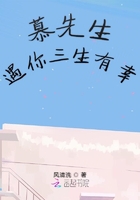天黑之前,哈娜和我先吃了饭,待在玛格丽特的房间里。日落时,纳森牧师出现在门口。玛格丽特指给我看墙上一个用来窥视的小孔,我便盯着那个小孔瞧,同时手捂住哈娜的嘴巴。牧师长得人高马大,但头明显太小。他的皮肤苍白而有些光泽,就像抹了鸡蛋清。他双眼深陷,耳朵对于身高来说显得很是小巧精致。他整个人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发酵过度的巨型面包。不过我得屏息静气,因为他环视房间时目光十分锐利,我肯定地感觉到他已经从这个窥视孔中看到了我。家里的每件东西他都要清查一遍,用手指摸摸桌布,试试每把椅子的关节,举起白镴杯子掂一下重量。
艾伦不久之后进门,从一开始我就不喜欢他。他肤色黝黑,有一个像姨夫那样的高额头,但脸窄得像野兔。嘴唇丰满,跟双眼不成比例,嘴跟眼靠得太近,很难显得高兴。他脸上是一副品尝浸过醋的面包的表情,我非常相信他是那种能从欺负小孩或毫无必要地吓唬小动物中获得快感的人。
牧师赞美了姨妈的厨艺,并援引《圣经》来为自己的贪吃辩护。“你知道,图萨克夫人,”他说,食物从嘴里溅到桌上,“在《以赛亚》的第25章第六节,我主的仁慈也是通过餐桌上的面包体现出来的。美食的确是上帝赐予我们的心灵盛宴的绝佳伴侣。”听到这一番话,人们还以为姨妈端上来的是天使的面包,而不是这炖烂了的味道辛辣的羊肉呢。他在嚼肉时,不时伸手从嘴里抽出软骨和肥肉,油乎乎的手直接擦在裤子上。终于,出于对自己声音的敬畏,牧师闭上了嘴巴,专心致志地吞咽起来。不过,因为姨夫和艾伦也很想发表高见,所以他们经常一个人还没讲完,另一个人已经开始了。有时候这三个人都在讲话,听起来就像是赶集时的荷兰商人。
我的眼皮开始沉重起来,直到我听到牧师说:“看起来天花已经过去了。上个月只死了六个人,三个来自同一个贵格会家庭,有一个跑了。我们大家都要感谢上帝帮我们除掉这些异教徒。”
“你有没有听说隔壁几个镇上的情况如何?”姨妈问,同时手拧着桌布。
“还没有,图萨克夫人。这恶劣的天气把我们都囚禁在自己家里。但我最近收到了一封来自波士顿同行的信。他说天花来了。还有……前所未有的骚乱……也开始了。”他最后来回摆动自己的手指,像是一群飞散的鸟。
“骚乱?”姨夫问道,嘴角往下一撇。
“巫术。妖术和咒语。我的同事认为,病情在力量上已经减弱,但在巫术方面却在提高。同样,沼泽地里肮脏的湿气开始上升。他叫我记起了不到两年前波士顿南部地区一次天花爆发,有一位约翰?古德温先生,是个泥瓦匠,他全家都被恐怖的巫术给害了。我说‘恐怖’,是因为科顿?马瑟在写一个叫做格拉佛的女人时就用的这个词,这个女人被控告做了这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