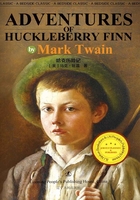她头一次觉得跟周围的人有一种亲密感,觉得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跟他们一起忧虑,一起痛苦,一起决断。对,他们是忍无可忍了!怎么能不经一番斗争就放弃南方这片美丽的土地呢?南方太让人爱恋了,怎么忍心看到它任凭北方佬的蹂躏呢?这些北方佬对南方人恨之人骨,巴不得把他们碾成碎末。南方这块乡土太珍贵了,怎么能把它交给沉醉于威士忌和解放之中的那些无知的黑人呢?
想到汤尼的突然到来和匆匆离去,她便感到自己跟他非常亲切,因为她回想起当年父亲离开爱尔兰的往事一那也是在夜晚,也是匆匆出走,也是发生在杀人之后,虽然这对他本人或对他的家人来说不能算谋杀。她个性中有杰拉尔德的性格一烈性子。她回想起自己开枪打死那个正在抢劫的北军时欣喜若狂的心情。他们大家身上都有这种烈性子,这种性子就隐藏在他们和蔼有礼的外表下,一触即发。他们所有人,她认识的所有男人,都是这样的,连睡眼惺忪的阿希礼和一向为琐事焦躁不安的老弗兰克,也都隐藏着这种性格一一旦需要,这种性子可以变得极为激烈而杀气腾腾。甚至包括瑞特,尽管他是个丧尽天良的流氓,也因为一个黑人“欺侮一位上等女人”而把他杀了。
弗兰克浑身湿淋淋地咳嗽着走进屋子时,她腾地站起来。
“哎,弗兰克,这种日子究竟还要过多久啊?”
“只要北方佬还恨我们,我们就要过这种日子,宝贝儿。”
“难道谁都没办法了吗?”
弗兰克用一只疲倦的手抹了一下湿淋淋的胡子。“我们正在想办法呢。”
“什么办法啊?”
“现在何必谈它?等我们干出点成绩来了再谈也不迟。可能要等好多年。也许一也许我们南方永远就这样了。”
“哦,那可不行。”
“宝贝儿,睡去吧。你一定是冻着了。你在发抖呢。”
“这一切究竟要到何时才能结束呢·”
“要到我们大家都重新有选举权的时候,宝贝儿。要到每个为南方战斗过的人都能为一个南方人或一个民主党人投一张选票的时候。”
“选票?”她绝望地喊道,“当那些黑人都丧失了理智一当北方佬毒害了他们的心灵,让他们都来跟我们作对的时候,选票又有什么用呢?”
弗兰克继续耐心地解释给她听,但是选票可以医治困难的观念实在太复杂,她没法领会。她愉快地想道,乔纳斯·威尔克森再也不会对塔拉庄园造成威胁了,她在想念汤尼。
“哦,他们方丹家真可怜!”她喊道。“只剩下亚力克了,他们含羞草庄园的事又那么多。汤尼为什么会这么糊涂一为什么不等到夜里没人看见时动手啊?明年春天,能看到他帮家里犁地不是比看到他在得克萨斯更让人高兴吗?”
弗兰克伸出一只臂膀,搂住她。平时,他搂她的时候总是怯生生的,好像预感到她会不耐烦地甩开他,但是今天晚上,他的眼睛里却流露出一种深沉的神情,他有力地搂住了她的腰。
“现在有很多事情都比犁地更要紧,宝贝儿。给黑人一点颜色看看,教训教训那些叛贼便是其中之一。只要还有像汤尼那样的好小伙儿,我看我们就可以不必太为南方的前途担心了。好,我们睡去吧。”
“可,弗兰克一”
“只要我们团结在一起,对北方佬寸步不让,总有一天会取得胜利的。你可爱的小脑袋就别担忧这种事情了,宝贝儿。这些事让我们男人去操心吧。也许我们这一代人看不到这一天了,但将来它终究会到来的。等北方佬发现他们连削弱我们都办不到时,他们就会疲惫不堪,不想再跟我们纠缠不清了。到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居住在一个像样的世界了,可以养育我们的儿女了。”
斯佳丽想到了韦德,还想到一个搁在心里巳好几天的秘密。不,这个世界上只有憎恨和不安,只有痛苦和潜在的一触即发的暴力,只有贫穷、磨难和不安全感,她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在这样一个一团糟的世界里成长。她决不能让自己的孩子知道这一切。她要一个安全而有秩序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她可以朝前看,并且知道前面有一个安全的前景;在这个世界上,她的孩子只知道温柔和热情,只知道精美的衣裳和丰盛的食物。
弗兰克觉得这样的世界可以通过选举来实现。选举?这跟选举有什么关系?有教养的南方人是再也不会有选举权了。要想防止命运可能带来的灾难,这世界上只有一件东西是可靠的一那就是金钱。她兴奋地想,他们必须有钱,而且必须得有很多钱,才能防止灾难降临。
突然,她告诉他,她怀孕了。
汤尼逃跑后的几个星期里,佩蒂姑妈家多次遭到一批批北军士兵的搜查。他们随时都会闯进房屋里,事先没有一点警告。他们涌进所有房间,不时盘问,把壁橱一只只打开,戳戳碍手碍脚的衣服,还朝床下张望。军事当局巳听到风声,说有人让汤尼逃到佩蒂小姐家去,所以他们认为他一定还藏在那里,或者在附近什么地方。
结果,佩蒂姑妈因为时时刻刻担心会有军官带着一队士兵闯进来,竟害起了彼得大叔称之为“神经紧张”的慢性病。弗兰克和斯佳丽都没有向她提起汤尼来待过一小会儿这件事,所以即使这位老太太想泄露点什么,也实在没有什么可泄露的。她情绪紧张地表白说,她这一辈子只见过汤尼一回,那还是1862年圣诞节的时候。她说的绝对是实话。
“而且,”为了表示主动配合,她会气喘吁吁地对北军士兵补充说,“那会儿他正醉成一摊泥!”斯佳丽因为是在妊娠初期,身体不适,心情也不好,所以对那些穿着蓝制服闯进她的私室、见了喜欢的小摆设就拿走的北军,一方面觉得非常可恨,另一方面因为怕汤尼的事会连累大家,十分担忧。现在,监狱里巳关满了人,都是因为比这更加微不足道的原因而被抓进去的。她知道只要被他们抓住一点儿证据,不但她和弗兰克,而且连清白无辜的佩蒂都会给关进牢里去的。
近来,华盛顿那边正掀起一场“没收逆产”以偿还合众国战争债务的运动,这使斯佳丽一直痛苦不堪、忧心忡忡。再加上现在亚特兰大又盛传说凡是触犯军法的,财产都要被没收,所以斯佳丽更加忐忑不安,生怕她和弗兰克不但要失去自由,而且连房子、店铺、锯木厂都要断送掉。即使他们的财产不被军事当局侵占,要是她和弗兰克进了监狱,又有谁来替他们照料生意呢?那不等于断送掉了吗?
她怨恨汤尼给他们带来这些麻烦。他怎么能对自己的朋友干出这事来呢?阿希礼又怎么能把汤尼往他们这儿送呢?以后如果再有人找她帮忙,只要会引得北军像黄蜂似的向她涌来,她是决不会再管了。是的,无论谁来找她帮忙,她准会让他吃闭门羹的。不过,当然,阿希礼例外。汤尼短暂来访后的几个星期里,她经常因外面街上的各种声响而从不安的睡梦中惊醒,担心阿希礼可能也正在受到追捕,也要从这里逃往得克萨斯州,因为他们曾帮汤尼这么干过。她不知道他目前的情况,因为他们不敢写信到塔拉庄园把汤尼那天夜里来过的事告诉他们。他们的信也许会被北方佬截获,这样连那座庄园也要遭殃了。但是,几个星期过去了,他们没有听到什么进一步的坏消息,于是他们知道阿希礼可能没事了。后来,北方佬终于不再来骚扰他们了。
但是,甚至这一令人宽慰的情况也没能让斯佳丽摆脱恐惧。这种恐惧始于汤尼来敲门的那一刻,它比围城时呼啸的枪林弹雨更让人心惊胆战,甚至比战争末期谢尔曼的军队更让人毛骨悚然。那个狂风暴雨之夜中汤尼的到来,仿佛把她眼睛前一副仁慈的眼罩扯掉了,迫使她真实地看清了自己不稳定的生活前景。
1866年寒冷的春天来临了,她环顾四周便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也意识到了整个南方所面临的形势。她可以为生活操尽心,也可以比以前的奴隶更努力地干活,她可以设法克服一切困难,还可以凭借自己的毅力去解决她平生从没遇到过的问题。但是,尽管她历尽了千辛万苦,尽管她作出了很大的牺牲,尽管她足智多谋,但她那付出巨大代价得到的初步一点点成果,任何时候都是可以被夺走的。一旦发生这样的事,她既没有法律上的权利,也得不到法律上的补救,有的只是汤尼咬牙切齿地提起过的那种临时法庭,以及那种为所欲为的军事法庭。现在,只有黑人才有控告权和索赔权。北方佬巳经使南方屈服了,他们想让它永远屈服下去。南方好像被巨人的毒手颠覆了,从前曾经统治过南方的人,现在比他们以前的奴隶还要无依无靠。
佐治亚州到处都驻扎着北军的重兵,亚特兰大驻军的数目更大。各个城市驻军的指挥官权力都极大,甚至操有对老百姓的生杀大权,而且他们也在使用这种权利。他们可以凭借任何理由或者无缘无故地监禁市民,剥夺他们的财产,并绞死他们,他们的确是在这么干着。北方佬就营业方法、佣人工资的支付、公众和私下场合的言论、报刊上的文章,制定了种种自相矛盾的章程,并以此来折磨和迫害老百姓。他们还规定了倒垃圾的时间、地点和方式,规定了以前邦联政府里的人的妻女什么歌可以唱,所以假如有人胆敢唱《狄克西》或《美丽的蓝旗》之类的歌,罪名只会比叛逆轻一点儿。他们还规定,市民必须先宣誓效忠然后才能到邮局去取信;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甚至规定了新婚夫妇必须先发一些可恨的誓才能领到结婚许可证。
报纸的嘴也都被封住了,凡是涉及抗议军事当局残暴和腐败的舆论,一律禁止刊登。胆敢提出反对意见的,则用判刑监禁加以压制。监狱里关满了有声望的市民,而且关在那里的人都没有早日得到审讯的希望。陪审制度和人身保护法实际上都被废止了。民事法庭虽然仍在勉强受理案子,但是完全受军人的支配。军人可以干涉法庭的判决,所以市民若不幸被逮捕,性命实际上就掌握在军事当局手里了。被捕的人确实很多。只要稍有一点煽动反政府的嫌疑,或被怀疑与三运党有关系,或者有黑人控告某个白人对他无礼,就足以把他送进监狱。不需要人证和物证,只要有人控告就行了。而且有解放了的黑人事务局在那里怂恿,还怕找不到控告的黑人吗?
现在黑人还没有获得选举权,但是北方巳经决定他们应该有选举权,同时还决定他们在选举中应该对北方表示友好。黑人知道这些情况后,认为没有什么是他们不该享有的了。黑人无论爱干什么,总有北军作后盾,而白人敢说黑人一句坏话,就非倒霉不可。
从前的奴隶现在都成了天之骄子。由于有北方佬撑腰,那些最卑贱、最愚昧的分子现在都出人头地了。他们中较体面的阶层根本瞧不起这种自由,他们和白人主人一样都在吃着苦。成千名家仆,当初他们属于奴隶中最高级的,现在仍然留在旧主人家中,干着过去比他们低下的人干的体力活。还有许多忠心耿耿的农奴,也不愿享受这种新自由,但是在一群群闹得最凶的“解放了的黑人渣滓”中,大部分是农奴出身。
在以前的农奴制时代,在家里和院子里干活的黑奴是瞧不起这些下等黑奴的。就像母亲那样,南方其它庄园的女主人也是先让一帮黑崽子接受一番训练,经过筛选,挑出其中最好的,让他们担任比较负责的职位。那些被派到田里去干活的,都是些最不想学、也最没能力学,同时也是最没干劲、最不诚实、最不可靠、最恶毒、最野蛮的黑奴。而如今把南方闹得民不聊生的就是这个黑人社会中最低微的阶层。
这些以前干农活的黑人,因为得到解放了的黑人事务局那些无法无天的冒险家的帮助,又受到北方人对南方人宗教狂热般的憎恨的鼓动,摇身一变,都身居要职了。他们智力低下,在那些职位上的所作所为,自然就可想而知了。就像把一群猴子或小孩放在许多珍贵的东西中间,这些东西的价值是他们无法理会的,于是他们就无法无天起来了一这也许是因为他们对破坏有一种变态的乐趣,也许只是因为他们的愚昧无知。
不过这些黑人,包括那些最愚昧的在内,也还有值得称道的地方,那就是他们中间真正怀有恶意的只是极少数人,而这极少数人即便是当奴隶时通常也是“下贱的黑鬼”。但是就整个阶层而言,他们的思想都像儿童那么幼稚,容易受人指挥,还因为很久以来养成的习性,惯于听从命令。以前,向他们发号施令的是他们的白人主人。现在,他们换了一批新主人,即解放了的黑人事务局和提包客,而他们发布的命令是:野你们与白人是同样的人,所以你们就照白人的样子去干吧。等到你们可以替共和党投票的时候,你们就可以得到白人的财产了。现在白人的财产也等于是你们的。如果能拿到手,你们就尽管拿好了!”
因为受这些谎言的迷惑,自由成了永远没有终结的愉快经历一天天吃吃喝喝、游手好闲、偷鸡摸狗、神气活现,就像在过狂欢节一样。乡下的黑人都涌进城来,农村都没人种庄稼了。亚特兰大挤满了黑人,但是仍有成百上千的人在涌进来,都是些新论调教育出来的懒惰而危险的分子。在城里由于都挤在肮脏不堪的小屋里,以致他们中流行着天花、伤寒、肺痨。从前做奴隶的时候,他们习惯于一生病就受女主人的照料,现在根本不懂怎么护理自己和其他病人。过去,他们依赖主人照看他们的老人和孩子,现在对于那些不能自主的人他们没有一点责任感。至于解放了的黑人事务局里的那些人,只对政治感兴趣,顾不上向他们提供以前庄园主给的那种照顾。
那些被遗弃的黑人孩子,像发了疯的动物一样满城乱跑,直到好心的白人把他们带回到自己的厨房里去养活。许多从乡下出来的老年黑人,都被自己的小辈给抛弃了,他们待在这个喧闹的城市里,丧魂落魄,惊慌失措。他们坐在街檐的石头上,向过路的上等女人哀求:野太太,行行好吧,替我写个信给费耶特县我的老主人,说我在这儿。他会来把我这个黑老头儿领回去的。哎哟,天呀,这自由我受够了!”
解放了的黑人事务局见涌进城里来的黑人巳多得成了灾,才意识到自己过去的政策有误,便设法将他们送回到他们过去的旧主人那儿去。他们告诉那些黑人,说如果他们愿意回去,那是以自由工人的身份回去的,有书面文契保护他们,工资也有明确规定。于是那些年老的黑人都高高兴兴地回去了,这就加重了那些贫困不堪的庄园主的负担,然而他们却不忍心把他们赶出门去。至于那些年轻黑人,便都留在了亚特兰大。他们是不愿干什么活儿的,哪儿都不愿去。他们现在肚子吃得饱饱的,干吗要去干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