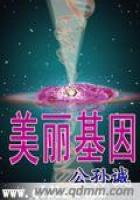“嗯,一定有用一一定有一这是个很好的庄园啊!你的钱决不会白丢掉的。等明年收起棉花来我就还你。”
“我倒觉得靠不住。”他朝椅背上一靠,将两手插进裤袋,“棉花的价钱在跌,现在的日子难过,钱紧得很呀。”
“哦,瑞特,你在跟我开玩笑吧!你知道自己有几百万呢!”
他用眼睛窥视着她,眼神里充满着极大的恶意。
“这么说来,你一切都挺好,并不怎么缺钱用。哦,我听了很高兴。我巴不得老朋友们都好。”
“哦,瑞特,看在上帝的分上……”她发急了,勇气和镇定都瓦解了。
“小声点儿!我想你不见得是想让北方佬听见吧。别人有没有告诉过你,说你的眼睛像猫——黑暗中的猫·”
“瑞特,别这样!我把一切都告诉你吧。我确实急需这笔钱。我刚才说的一切都是骗你的,一切实在都糟得很!父亲他一他一精神失常了,自母亲去世后,他一直都那么呆呆的,一点都帮不了我。他简直就像个孩子。而且现在家里是一个干农活的人都没有,棉花没人种,吃饭的人倒有十三个。还有那税款一要的很高。瑞特,我全告诉你了。这一年多来,我们都差点饿死了。哦,这你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我们从来都没吃饱过,早上醒来是挨饿,晚上睡着也是挨饿,这日子可真受不了了!再加上身上没有暖和的衣服,孩子们老是挨冻、害病,还一”
“你这身漂亮衣服是从哪儿弄来的?”
“是用母亲的窗帘改做的。”她回答道。这话说出来很丢人,但她心里实在是着急,一时竟编不出谎来。“如果单单是挨饿受冻,我是能挺住的,可现在一现在提包客提高了我们的税款,而且这笔钱得马上付。我只有一块五元的金币,此外是什么都没有。我一定得筹到这笔税款!你明白吗?如果我付不出这笔钱,我就会一我们就会失去塔拉庄园。我们无论如何不能丢掉塔拉!我们决不能放弃它!”
“那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告诉我这一切,偏要先来折磨我这颗易动感情的心呢?凡是涉及美貌女人的事情,我这颗心一向是很脆弱的。不,斯佳丽,你别哭。除了这套把戏,你什么手段都使用过了,这我可受不了。现在我既然巳发现你要的是我的钱,而不是我这个颇有魅力的人,我的感情巳经由于失望而受到了伤害。”
她知道每当他这样嘲讽自己也嘲讽别人时,往往吐露的是肺腑之言,所以她急忙抬起头来看着他。难道他的感情真的受到了伤害?难道他当真有意于她?刚才在看到她的手掌之前,他难道是真的打算要向她求婚?或者是仅仅像以前那两次一样,再次提出那种令人作呕的建议?假如他真的对她有意思,那她说不定还能收服他。然而,他那双贼溜溜的眼睛正在折磨她,一点不像是个情人,接着他轻轻地笑了。
“我不喜欢你的抵押品,我不会经营农场。你还有别的可做抵押的东西吗?”
哦,终于又谈到这个话题上来了。机不可失!她深深地吸了口气,与他的眼睛正面相对。这时,她振作起精神,去办这件她最担忧的事,并且也顾不上做出媚态来卖弄风情了。
“我一还有我自己。”
“是吗?”
她下颚的纹路紧绷成了四方形,眼睛转成了翡翠的颜色。
“记得围城时有天夜里在佩蒂姑妈家门廊上的情景吗?当时你说一你说你需要我。”
他毫不在意地往椅背上一靠,看着她紧绷的脸,黝黑的脸上的表情深不可测。他眼睛深处有某种东西在闪烁,可他不吭声。
“你说一你说过你从来不曾像要我这样迫切地要一个女人。你如果仍然要我,你可以得到我。瑞特,我会对你百依百顺的,可请你看在上帝的分上,开一张支票给我吧!我说话是算数的。我可以赌咒,决不食言。哪怕你要我写张字据也行。”
他古怪地看着她,脸上仍是那种深不可测的表情。她急匆匆地说话时,无法看出他是高兴,还是反感。要是他能说句话就好了,说什么都行!她觉得自己的脸渐渐变得火辣辣的。
“我得立刻得到这笔钱,瑞特。他们要把我们赶出门,爸当年那个该死的总管要来占据这个地方,而且一”
“等等。你怎么知道我仍然要你?你怎么知道你自己值三百块钱?女人大多没有这么高的价。”
她的脸一直红到了发根,这一下子她可真是被羞辱到了极点。
“你为什么非这么干不可呢?你尽可以放弃那个农场,住到佩蒂帕特小姐家去。她那房子有一半是你的嘛。”
“哎呀,我的天哪!”她喊道,“你傻啊?我不能放弃塔拉庄园。那是我的家,我决不会放弃它!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决不放弃!”
“爱尔兰人真要命,”他一边说着,一边放平了椅子,又把手从裤兜里抽了出来。“他们总把许多微不足道的东西看得很重,比如土地。天底下的土地到处都一样。好吧,斯佳丽,让我来把事情说个明白,你这次来,是来跟我做买卖的,我给你三百块钱,你就愿意做我的情妇。”
“旦”
是。
既然这句令人厌恶的话说出来了,她反而轻松了,希望又在她心里滋长起来。他刚才说“我给你三百块钱”。这个时候他的眼睛里射出一种恶魔般的光芒,好像有什么让他觉得乐不可支似的。
“不过,以前我厚着脸皮向你表述同样的意思时,你却把我赶出了大门。还臭骂了我一顿,说你不想养上‘一窝崽’。不,亲爱的,我并不是要揭你的伤疤,我只是对你脑子里的怪念头感到惊讶。你这么做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快乐,而是为了不让豺狼跨进你的家门。这就证明了我的一个论点:一切美德都不过是代价问题。”
“哦,瑞特,看你说了个没完!如果你存心侮辱我,那就继续这么做好了,但钱可得给我。”
现在她觉得呼吸轻松多了。既然瑞特是这种人,他自然会尽量折磨她,侮辱她,以报过去受尽种种轻蔑之仇,发泄刚才受到耍弄的气愤。好吧,由他折磨、侮辱她吧,她受得了,她什么都受得了。为了塔拉庄园,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有一会儿,她想象着在那仲夏时节,午后的天空湛蓝湛蓝的,她懒洋洋地躺在塔拉庄园浓密的三叶草坪上,仰望不断翻滚着的似城堡般的云彩,白花的香气阵阵扑鼻而来,耳畔是忙碌的蜜蜂发出的悦耳的嗡嗡声。这午后时分,这寂静的环境,以及从盘旋上升的层层红艳艳的田野里传来的隐隐约约的马车声,都值得她付出这些代价,她还愿意付出更多。
她抬起了头。
“你打算把钱给我了吗·”
他的神情好像在自得其乐,但他说出的话却冷酷之中带着温和。
“不,我不打算。”他说。
一时间,她无法让自己的思维适应他的话。
“即使我愿意,也不能给你。我身上一个子儿都没有。我在亚特兰大一块钱也没有。不错,我有点钱,但不在这里。我不想告诉你钱放在了什么地方,到底有多少。不过,假如我设法给你开张支票,这些北方佬便会像野兽见到猎物似的扑过来,这样你我就都拿不到这笔钱了。你觉得怎么样·”
她脸色发青,显得很难看,鼻子上的雀斑也都突然显了出来,嘴唇扭曲得就像杰拉尔德大发雷霆时的模样一样。她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发出语无伦次的喊声,以至隔壁房间里嗡嗡的谈话声都戛然而止了。瑞特像一头豹子,迅猛地走到她的跟前,用他那只有力的手捂住了她的嘴,手臂紧紧地搂住了她的腰。她发疯似的想挣脱他,想咬他的手,踢他的腿,并发出尖叫,以发泄心头的愤恨、失望和自尊心受到伤害的痛苦。她弯下身子,拼命想从他那条铁箍般的臂膀里挣脱出来,她的心都快要蹦出来了,她穿着的紧身褡绷得她透不过气来。他紧紧地抓着她,动作粗暴得让她发痛,那只捂住她嘴的手残酷地掐进了她下颚的肉里。他那张黝黑的脸一下子变得煞白。他瞪着忧虑的眼睛把她抱起来搂在怀里,坐了下来,将她放在了自己的膝上,可她仍然在他手里挣扎着。
“亲爱的,看在上帝的分上,别这样!小声点!不要叫!再叫他们马上就要进来了。你一定得安静下来,你非要北方佬看到你这副模样不成吗?”
无论谁看见她都不在乎,她只恨不能将他杀死,别的她什么都不在乎。她突然觉得一阵头晕目眩向她袭来。她透不过气来。他仍然把她的嘴捂着。她的紧身褡像铁圈越箍越紧。他双臂搂着她,她则怀着绝望的怨恨和怒火拼命地挣扎着。接着,他的嗓音显得越来越微弱、模糊,他俯视着的脸庞在一层让人讨厌的迷雾中旋转着,这迷雾越来越浓,她终于看不见他了一什么都看不见了。
等到她昏昏沉沉地苏醒过来,发现自己疲惫不堪、浑身无力、神情恍惚。她仰躺在椅子上,帽子都掉了。瑞特正拍着她的手腕,那双黑眼睛正焦急地盯着她的脸庞。那位和蔼的青年军官拿着一杯白兰地正往她嘴里灌,结果泼翻了,酒顺着她的脖子直往下淌。其他几位军官无能为力地在一旁走来走去,交头接耳地挥舞着手。
“我想一我刚才一定是晕过去了。”她说,她觉得自己的声音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发出来的,不免吃了一惊。
“把这个喝下去。”瑞特说着把白兰地送到她嘴边。现在她想起来了,虚弱地朝他怒目而视,但她太虚弱了,连发火的力气都没有了。
“请看在我的面上喝下去吧。”
她喝了一口便呛着了,接着咳了起来,但他依然把杯子送到了她的嘴边。她喝了一大口,那股热流一下子就让她喉咙里火辣辣的。
“我看她现在好些了,先生们,”瑞特说,“多谢各位了,她得知我要被处死就吓得晕了过去。”
那群穿蓝军服的人满脸窘态,清了清喉咙便拖着缓慢的步子走了出去。那位青年军官在门口停了下来。
“还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吗?”
“没有了,谢谢。”
他走出去,随手关上了门。
“再喝一点吧。”瑞特说道。
“不。”
“喝一点吧。”
她又喝了一口,当即觉得全身暖和起来,体力渐渐恢复了,两腿也不发抖了。她推开酒杯,想站起来,但他一把将她按了回去。
“你放开,我要走了。”
“你还不能走。再等一会儿。说不定你又会晕过去的。”
“我宁可晕倒在马路上,也不愿跟你一起待着。”
“我不管你宁可怎么样,反正不能让你晕倒在路上。”
“让我走吧。我恨你。”
听她这么一说,他脸上又露出了一丝微笑。
“这话才像你说的。你现在一定感觉好些了吧。”
她放松地躺了一会儿,尝试着激起一些怒气来支撑自己,以鼓起劲来。但她太疲惫了,疲惫到既无法恨,也无法考虑任何事情的地步。失败像一块铅沉沉地压在她的精神上。她把所有一切都拿来孤注一掷,现在却输得精光。甚至连自尊心都输掉了。她最后一线希望也山穷水尽了。塔拉庄园完了,家里人也全都完了。她闭上眼睛,仰卧了很久。这时候她听到他就在旁边喘着粗气,同时那白兰地的酒力也渐渐地渗透到了她的全身,她似乎感觉到了一点温暖,力气也好像大了一点。后来,她终于睁开了眼睛,看到他的脸,心里又燃起了怒火。她那对浓眉紧紧锁在一块儿,这时瑞特脸上又泛起了熟悉的微笑。
“你现在觉得好点了吧,这一点从你紧皱着的眉心可以看出来。”
“不错,我是好些了。瑞特·巴特勒,你这个人真可恨,是个流氓,在我见过的人中只有你是流氓!我刚才一开口,你就很清楚地知道我打算说什么,你也知道自己不能把钱借给我。可是你却让我往下说,让我把什么都倒出来。你完全可以避免让我这么做一”
“避免让你说下去,那我便什么都听不到了。不,我才不会那样做呢。这儿可供消遣的东西太少了,我从来还没见过这么有趣的事呢。”他突然发出一阵嘲弄的笑声。听到这笑声,她猛地站了起来,抓起了自己的帽子。
他蓦地按住了她的双肩。
“你还不能走。现在你是不是觉得好了,可以把话讲清楚了?”
“放开我!”
“我看你是好了。那么你只回答我一句话。你要打主意的猎物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他的眼睛敏锐而机警,仔细地观察着她脸上表情的变化。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准备用这种办法试一试的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你是否还要算计别的男人?你说。”
“没有。”
“我不信。我才不信没有五六个做候补的人呢。肯定有人会接受你有趣的建议的。这我可是挺有把握的,我可以给你提一点小小的忠告。”
“我不需要。”
“不需要,我也要提。现在我能给你的似乎也只有忠告了。听着,这可是一条非常好的忠告。当你想向男人索取什么东西的时候,千万别像刚才对我那样毫无保留地和盘托出。你一定要想法子做得委婉些、圆滑些,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这种手法你过去懂得,而且还非常精通。可是你刚才提出拿一拿抵押品来向我借钱的时候,看上去简直跟铁钉一样生硬。我记得跟别人决斗的时候,对手就站在二十步之外,他那双眼睛就像你刚才那样,让人看了很不舒服。这种眼神是决不会在男人心里引起热情来的。这决不是对付男人的办法,亲爱的。你把早年所受的训练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用不着你来教训我该怎么做,”她一边说着一边疲倦地戴上帽子。她不明白,这个人脖子上巳套着绞索,对她可怜的境遇,居然还会这么谈笑风生。她甚至都没注意到,他紧握着拳头的双手把裤袋塞得鼓鼓的,仿佛拼命在跟自己的无能为力作斗争似的。
“别灰心,”在她结帽带时,他说。“等我上绞架的时候,你可以来看我,那时你准会觉得舒服多了。到那时,我们俩的旧账就可以一笔勾销了一包括这笔账。我一定会在遗嘱里提到你的名字的。”
“谢谢。可是要是他们一直拖着不送你上绞架,那付税款就来不及了。”她说,声调突然变得跟他一样恶狠狠,她是故意这样的。
她从那幢房子出来时,天正下着雨,天空是一片暗淡的油灰色。广场上的士兵都进那些临时营房中躲雨去了,街道上空无一人,也见不到任何车辆,她知道自己得走老远的一段路回家去了。
她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前走着,白兰地的酒力渐渐消失了。冷风吹得她瑟瑟发抖,冰凉的雨点针剌般打在她脸上。佩蒂姑妈的薄斗篷不一会就被雨给淋得湿透了,湿乎乎地贴在她身上。她知道那套天鹅绒衣服也快淋坏了,帽子上的几根羽毛也都湿漉漉地耷拉着,就像长在塔拉庄园潮湿鸡棚里的公鸡尾巴上一样。人行道上的铺路砖七零八落的,有时好长一段路上干脆全都没了砖头,走在上面烂泥直没到脚踝,鞋像是让胶水给粘住了似的,后来甚至连鞋都从脚上掉下来了。每次她弯下身去把鞋子重新穿上时,裙边都碰到了泥浆。她压根儿没想绕过泥潭,而是让那沉重的衣裙从泥浆里拖过去。她能感觉到那湿淋淋的衬裙和裤子裹在脚踝上冷冷的,可她也顾不得刚才曾拿来进行赌博的这套衣服给弄得不像样子。她只觉得心灰意冷,并且是既沮丧又绝望。
她对家里人说了那么多豪言壮语,现在哪还有脸回塔拉庄园去见他们?她怎么对他们说,他们全都得到别处去?那红色的田野,那高高耸立的松树,那黑沉沉的沼泽地,还有在那一片雪杉的浓荫下静悄悄地埋着母亲的寂静墓地,这一切她怎么舍得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