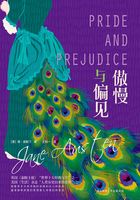灯光摇曳,人影双叠。
尚且不知被林公溥发现问题的陈省之正看着秋蓉写毛笔字,嘴里忍不住称赞:“秋蓉,你这进步真是神速,你看这几个字遒劲有力,不让须眉。”
秋蓉正欲谦让,只听陈继庭在帐内呢喃:“杀……杀……”
二人不由失笑。秋蓉忙起身给陈继庭盖被子,陈省之则在一旁笑道:“继庭这孩子,人小鬼大,聪明伶俐,以后必能成大器。”
秋蓉边给孩子盖被子边说:“先生高风亮节,人中翘楚。秋蓉虽然口中不说,但心里真的是感念先生之品行。”
“你看你看,怎么说着说着就沉重了呢,你不嫌弃省之身份,不怕被我拖累,这些年来,一直在我身边照顾我,让我没有后顾之忧。我才要感谢你呢!”
“先生您是成大事者,秋蓉一介妇孺,不懂政治革命,但这些年来也耳濡目染对于先生所为之大业有了些许了解,知道是功在千秋的一件大好事。精密谋事秋蓉是不擅长,也只能为先生洗衣做饭,让先生有更多精力投身兴中大业。”
“这就够了。其实我还要感谢苍天将你送到我身边,要不然我怎么会有继庭这个可爱的儿子,怎么会有机会享受这天伦之乐。”陈省之说着感激地看着秋蓉,秋蓉将视线躲开。
陈省之搬起被子铺在地上,秋蓉却拦住了:“你……你在床上睡吧,老是打地铺,我……我真于心难忍。”
陈省之道:“没事儿,我习惯了。”
秋蓉则说:“睡床上吧,我相信你。”
这次,陈省之没有拒绝。
秋蓉和陈省之分别睡在陈继庭身侧,两人都没入眠。
秋蓉开口道:“省之,这些年你受的委屈太多了,我真的不能这么自私,林小姐对你痴心一片,此情不渝,你还是把她娶过门吧。别再这样委屈自己了,你知道,我们虽然有夫妻之名,却无夫妻之实,我不能再看着你这样对待自己。”
陈省之平淡道:“秋蓉,睡觉吧。”
秋蓉却爬了起来:“不,你一定要答应我,要不我这心里真的愧疚难安。”
陈省之叹了口气,还想说什么,忽然一阵巨响,房门被一脚踹开。随后一队官兵冲了进来。陈省之尚未反应过来,刀就架在了脖子上。
领头的官老爷大喊一声:“捉拿乱党,若敢反抗,格杀勿论。”
陈继庭被这喊声吓醒,躲在秋蓉身后,紧张地看着这一切。众人七手八脚地将陈省之捆绑起来。
秋蓉急了,一下冲过来护在陈省之面前:“你们到底凭什么抓他?”
官老爷硬着语气说:“就凭他是乱党。”
陈省之将秋蓉拉到自己身后,挺身护住她:“你们这不是血口喷人吗……”
不待陈省之说完,官老爷举着陈省之写过的有关兴中会的资料,砸在他脸上。陈省之愣住了,瞬间明白了什么,他凛然瞪了官老爷一眼,官老爷不禁后退了一步。
“有什么事儿跟我说,跟我妻儿毫不相干。”
“相不相干,到了衙门再说!”
清兵们押着陈省之和秋蓉便往外走。一路上,陈省之被五花大绑地押着,他偷偷挣扎着绳索。秋蓉抱着继庭在兵丁的推搡下走在陈省之跟前,她关切地望着陈省之。陈省之的目光碰到秋蓉的目光,显得有些惭愧。
陈省之小声说:“秋蓉,对不起,让你们母子受连累了。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都记得我的话,跟我撇清关系……”
话毕陈省之大声对官爷喊:“请你们放了她们母子,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官老爷却命令道:“把他嘴给我塞上。”
兵丁上去给陈省之嘴里塞东西,忽然陈省之飞起一脚将兵丁踢翻在地,从兵丁手里抢过一把刀反手将另外一个兵丁砍倒。
随行的清兵大乱,纷纷抽刀抵抗。
秋蓉抱着继庭焦急地要往上冲,被一个清兵用刀逼住。陈省之一改往日秀才的文弱,变得骁勇起来,但终究寡不敌众,背上被清兵砍了一刀,摔倒在地。清兵将陈省之围困起来,剑戈齐进,陈省之身上伤口累累,满脸血污。
眼见性命攸关,陈省之被激起了斗性。他奋起反击,杀出一条血路,纵身跳进河里。清兵对着河面连发火枪,只见河水中泛出了一圈殷红。
秋蓉和陈继庭冲到桥头,撕心裂肺地喊叫:“省之!”
清兵上前欲将秋蓉拉开桥边,陈继庭急了,冲上去对着拉扯秋蓉的清兵就是一口,清兵一巴掌将陈继庭打翻在地。秋蓉不顾自身安危,连爬带滚扑上去护在陈继庭身上,这时清兵的刀砍下来,劈中秋蓉后背,鲜血飙飞……娘儿俩一路被押往了衙门牢房,后背血肉模糊的秋蓉趴在地上昏死过去。
陈继庭摇着牢房的门使劲地拍打,哭声凄厉:“救命啊!来人啊!快救救我娘,我娘要死了……求求你们,快救救我娘!”牢房里并无人回应,陈继庭哭喊得快断气了。
林舒得知陈省之的事情,几乎发了疯,披头散发地拿着一把刀追在林公溥身后:“你说,是不是你给官府告的密?”
林公溥大汗淋漓,一屁股坐在地上:“算了算了,你要砍要剐随你了,但是你不能冤枉哥哥。省之和我是至交,我怎么能做出这么丧尽天良的事儿呢!”
说到这里,林公溥突然话锋一转,“他是乱党的事儿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我,我怎么知道。”
“那就好,那就好,唉,知人知面难知心啊!没想到他能做出这么大逆不道的事来,这可是杀头的死罪啊!幸好你没嫁给他。”
林公溥松了口气,回头却看见林舒将刀丢在地上,一屁股坐在他身侧。
“不管他是什么人,我心意已决,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现在他生死未知,我这辈子绝不他嫁。”随后林舒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说道,“哥,求你跟官府的人说说,把秋蓉和继庭放了吧,不管陈省之做了什么,都跟她们孤儿寡母没关系,现在陈省之八成是死了,人死百了,这事儿就过去吧。”
林公溥为难道:“这官府也不是我开的。”
林舒一把抓起地上的刀,林公溥吓了一跳,往后挪着身子。林舒将刀逼在自己脖子上,猛地一拉,脖子上就渗出鲜血来。
林公溥慌忙应道:“好,好,好……我答应你,我答应你还不行吗?”
手起刀落,林舒将头发削掉大半,她含泪给林公溥磕了个头,说道:“哥,小妹从此削发为尼,终身不嫁!”说完站起身踉跄而去。
林公溥整个人傻在了那里。
无奈之下,林公溥只好想法子帮妹妹这个忙了。他来到监牢,看见不忍睹视的惨状,捂着鼻子不停地扇手,对衙役不满地发着牢骚。
衙役讨好道:“我们也不知道是员外你的妹妹呀,真是一场大误会。”
林公溥没好气地说:“胡说八道,我妹妹怎么可能跟乱党搅在一起呢,你们分明是抓错人了。”说完哼了一声,摆摆手,进来两个家丁将秋蓉扶了起来。
回到林府,经过大夫的一番救治,秋蓉终于缓了过来。
林公溥忙走到床前,见状长长松了口气:“总算醒了,秋蓉,你要有个三长两短,你说我怎么向我死去的兄弟交代啊!”
秋蓉面色苍白:“你,你是说省之他……他……”
林公溥一脸苦相:“八成是遭难了,我派人去河里打捞了好几天,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唉,没想到省之他,他竟然能干出这样的事儿来……”
听到这个讯息,秋蓉的眼泪悄然流了出来。
林公溥劝道:“秋蓉,你也别太伤心了,省之他这是一时糊涂才做了这大逆不道犯上作乱的事儿,我知道你和他不一样,这以后你们就放心地在我这儿住着,有我在,不会再有人欺负你们,衙门那里我也打点好了,他们不会追究你们娘儿俩的,你就好好放心养伤……”
秋蓉虚弱地应了声谢。
做了这件事后,林公溥突然觉得自己很开心,一脸喜气地走进自家院子,可金凤正双手叉腰地站在那里。她上来就撕扯林公溥,抓林公溥的耳朵,林公溥生气地推开金凤。
金凤兀自站稳身子,张口就说:“我问你陈省之的事儿是不是你告的密?”
林公溥一愣,生气道:“你脑子有问题啊!他是我的兄弟,我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儿……”
金凤哼道:“兄弟?恐怕你根本就没当他是兄弟。”
“你说的什么胡话!”
金凤依然不依不饶:“你打的什么如意算盘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借官府的手把陈省之除了,不就是想把秋蓉娶进这个家吗?这些年你什么时候死心过!”
林公溥生气地拉扯着金凤进屋:“你这个疯婆子……”
金凤挣脱林公溥的手,狠狠地说:“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做梦都喊那个狐狸精的名字,你说,你不是这么打算的是什么,你早就视陈省之为眼中钉了……”
林公溥恼怒地捂住金凤的嘴,把她拉进了屋里。
从兵部尚书郎文府上回来后,唐端一脸冷峻地在大厅踱步。夫人看着唐端,惴惴不安。唐端心中感慨:这次真是走了一步险棋。现在皇上和太后明着母子一派,暗地里却是斗得你死我活,在这种情况下做臣子的若稍有不慎,站错队列,哪一方都得罪不起,都是掉脑袋的事儿!多亏自己及时把穆厚坤等人想刺杀太后的事儿秘密禀报,要不非得受到牵连。只是眼下乱党闹事,朝廷命他彻查,以赶尽杀绝。想到此处,唐端愈发烦闷起来。
唐夫人也跟着担忧:“哎呀,到底怎么了,你走来走去的,看得我头晕。”
唐端叹了口气,压低声音:“我这是在担心……逆子。”
唐夫人惶恐:“你是说翱儿,他怎么了?”
唐端赶紧做了一个阻止的手势,嘘了一声:“隔墙有耳,小心提防。今日朝廷责令我清除乱党,其中必然用心良苦,逆子和乱党不清不楚,我早有耳闻,现在朝中派系林立,各霸一方,拿不准哪一伙借机下绊,挖下陷阱让我跳。”
“你是怕他们利用翱儿做文章?”
“正有此虑。”唐端沉思片刻,“赵恩龙这步棋倒是可以走一走。”说完便拉着夫人去找被他关起来的唐翱……几天后,唐府的结亲队伍在唐五等兵丁的护送下向湖北进发了。唐翱被五花大绑地绑在轿子里,哭笑不得。唐端则在轿中气定神闲地闭着眼盘算着什么。
一段行程后,唐端终于推着五花大绑的唐翱进了赵府,赵恩龙忙迎了上来。
“唐兄,你这是为何?”
唐端怒道:“不孝之子,我给绑来了,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赵恩龙摆摆手,叹气说何苦如此。这时五花大绑着的唐翱客气地上前见礼,言辞之间仍称他“赵伯伯”。
赵恩龙呵呵笑着,示意下人给唐翱松了绑:“以后要改口叫岳父。”
唐翱却道:“我不同意这门亲事。”
赵恩龙怔住:“贤侄嫌弃我家婉儿?”
唐翱正色道:“我和小姐面都没有见过,当然谈不上嫌弃,只是觉得你们为了两家结姻,全然不顾我们的感受,你们是为了政治目的,却要葬送我们的情感。”
赵恩龙不怒,反倒哈哈大笑:“贤侄思想进步,思维活跃,快人快语,话说的虽然在理,但未必是真,婉儿从小老夫视为掌上明珠,且和你父早有婚约,这是沿袭传统,怎可说不顾你们相互之情感呢?”
唐端解释说:“恩龙兄不要在意,小儿信口雌黄,胡言乱语,你我岂能让他坏了约定?此次我缚子前来就要和你当面商定他们的婚事。”
赵恩龙笑道:“我也正有此意。”
见二位长辈铁了心要成全这门亲事,唐翱心中气急,索性转身向外走去。
唐端示意唐五跟上,主仆二人走到赵府花园时,唐翱气得指着唐五鼻子久久说不出话。突然看到赵婉带着丫鬟从远处走来,他忙放下手指装作赏花的样子。
赵婉径直走到唐翱面前:“是唐公子吧,你好。”
“你是……你莫非是那个与我指腹为婚的赵小姐。”唐翱上下打量一番,赵婉大约十八岁上下的样子,穿着小西服和马靴,一看就知道是留学回国的。
赵婉含笑点头,唐翱看着略有些愣神,忽而惊喜道:“我以为赵小姐是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大家闺秀,没想到这么洋气。”
这时丫鬟插嘴说:“我们小姐刚从国外留学回来。”
赵婉大方地说:“唐公子,有什么需要就跟我说。”
“需要?”唐翱看看唐五,“我需要自由,你能帮我吗?”
“没有绝对的自由,你我都一样。”
“算了,就知道你没办法。你不要跟着我,我要一个人逛逛。还有,我爹是认了你当儿媳妇,但是我可没有认……”唐翱说完转身就走。
此时京城戏院外,唐允急匆匆地走出来,身后跟着一个家丁。就在不久前,家丁赶来禀报说唐翱被定为乱党,京中已发布通缉文告。
“这事儿千万不能耽搁,快快回府,收拾行囊,我要马上出发,要是晚了我弟弟的性命休矣。”唐允说着快步欲行。
家丁忙拉住唐允:“大少爷,家里没你不成,你要是信得过小的,这送信的差事就交给我了,我跑一趟。”
唐允想了想,伸手拍拍家丁的肩膀:“那就拜托你了,火速送到驿站,飞鸽传书。”
待家丁离开后,唐允再也无心看戏。他正准备回家,突然一声爆响,胸口中了一火枪,血肉飞溅,烟雾缭绕。马祥祺从暗处举着火枪走来,脸上满是阴鸷冷笑。唐允挣扎着掏枪反击,马祥祺猝不及防,转身疾跑。
闻讯而来的杨雨奇率众将马祥祺包围,几支火枪齐刷刷地对准了马祥祺,马祥祺无力反抗,只得被生擒活捉。
杨雨奇忙让兵丁抬起唐允:“快送唐公子去医院!”
厅堂上,赵恩龙将唐府家丁送来的纸条递给唐端。唐端扫了一眼,却不动声色。赵恩龙有些按捺不住,来回踱了几步之后,询问起唐端的看法。唐端故作轻松地说这根本不用理会,分明是朝中有人陷害,接着又叹息起唐允沉不住气,以为天大的事儿,还飞鸽传书,白白落人话柄。
赵恩龙接话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们说二少爷和跟乱党不清不楚,这我当然也不相信,但是人言可畏,就怕二少爷在劫难逃。”
唐端呼地站起来:“你放心,出了多大的事儿唐某一人担着,绝不连累你!”
赵恩龙搓搓手,讪笑道:“我不是这个意思。再说了,现在唐翱是我的女婿,再大的事儿也不能让你一个人担着,我们是一家人。”说完又继续踱步思忖着。
唐翱一脸懵懂,吊儿郎当地再次走进来时,看见两人脸色不善,欲言又止。
赵恩龙突然停住脚步,对唐端说:“我倒是有个主意。”随即他压低声音,“当下要紧的是将翱儿藏起来,别再授人以柄。现在我手里正好有几个派遣留学日本的生员名额,不如让唐翱假冒湖北生员……”
听到最后一句话,唐翱来了精神,一步跨上前去:“我去!”
被带回京城大牢的马祥祺,经过一番严刑拷打,已浑身是伤昏死过去。
杨雨奇站在暗处冷冷地看着这一切,待马祥祺被凉水激醒后,他立即换了一副表情,急匆匆走进监牢,喊道:“住手!”
衙役们忙住手,疑惑地看着杨雨奇。
“还不松绑……”杨雨奇嗔怒道。
衙役们忙冲上去将马祥祺放了下来,马祥祺腿一软跌坐在地,衙役们将他扶在坐椅上。杨雨奇挥挥手,示意周围人退下。他将桌上的酒倒在碗里,递到马祥祺面前。
马祥祺骂道:“狗官,要杀要剐你快点动手,老子不稀罕。”
杨雨奇云淡风轻地笑着说:“死到临头还这么嚣张。朝廷正在彻查乱党,我也是身不由己。”又是一番威逼利诱之后,杨雨奇亮出底牌,“我也不给你绕弯子,本官受步兵统领荣大人所托,有意结交一下江湖奇人,看你性情豪爽,有情有义,有意引荐你,不知道你意下如何。”
马祥祺没答话。
杨雨奇继续道:“要想报仇雪恨,东山再起,就得忍辱负重,你莫不是不想报仇了?”
“我做梦都恨不得血刃唐门那些狗贼。”马祥祺厉声咬牙。
“那就对了,识时务者为俊杰。只有受命于荣大人,你的仇才有可能报,你要是不想,那我也没办法,只好公事公办。”
马祥祺不再说话。
杨雨奇趁热打铁:“你知道李鸿章李大人吧?”
当今谁不知道此人?马祥祺抬头疑惑地看着杨雨奇,见他做了个杀的手势,心中不禁咯噔一下:“你是让我去刺杀他?”
杨雨奇一字一顿道:“卖国之贼人人得而诛之。”
确定去日本学习的唐翱心情变得大好,在赵府花园内随意漫着步。他走过亭廊看见月光下石桌上坐着一人,走近才看清是赵婉,桌上孤灯独照,摆着酒壶,看起来似乎有点萧瑟。
赵婉端酒明眸皓齿地望着唐翱:“为公子饯行!”
唐翱没说话,也不端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