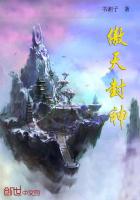1.居敬处世,内专外齐
孟子说:“有礼者敬人。”敬人,是一种修养,也是对待别人的一种态度。《左传》中说:“敬,身之基也”,“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
敬,作为对人对事的一种道德要求,首先,要自敬,用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自己,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自敬,在外表上要严肃、整洁,干净利落,在内心则要有恭敬之态度。其次,对别人要尊敬,无论对方官大官小,无论对方贫与富、长与幼,都应该恭敬有礼,不可轻慢。
为了求得治学之道,曾国藩向多个在京的名人求教。其中唐鉴告诉他要以朱子之书为宗,把它当作一门课程,认真研修。后来,倭仁告诉他,“研几工夫最要紧”,从此,曾国藩就严格按照二位前辈的要求,悉心研究理学,同时把理学贯彻到自己平时的行动中去,个人修养、待人接物都以此为据。
曾国藩一方面仔细研究理学家们所探讨的“敬”字的深刻涵义,另一方面又做出了自己的解释。道光二十二年(1842),曾国藩在一篇日记中这样记载:“从本年十月立志自新,专门立下课程,从‘敬’字开始做起。”并为“敬”字做出自己的解释:“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如日之升。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验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后来,曾国藩又做出了具体的描述:
“内而专修纯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平天下,“敬”之效验也。程子谓上下一于恭敬,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气无不和,四灵毕至,聪明睿智,皆由此出。”
在这里,对内强调心无杂念,谨慎小心,对外强调严肃整齐,庄重有礼,干事情则兢兢业业,毫不轻率,做到了这一切,就可以达到物顾人和,天下太平之气象,也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理想世界。
修身是一个人要做的最基本的事情,宋儒把修身工夫发展成了一个完备的理论体系。从外表、待人接物,以至内心世界的克制,都有详细的要求。曾国藩认为,居敬,对个人来说,有两方面的要求,可以达到两方面的效果。对内则求专静统一,以养大体,对外则整齐严肃,以养小体,如此下去,才会日渐强健。
曾国藩一生官至要职,加上军旅生涯,政务、军务缠身,为此常常感到筋疲力尽,在日记和给朋友的书信中也常表达这种无奈心态。曾国藩常常把这种状况,归之于自己在“居敬”上面修养不够。天天忙于俗务,名利时时缠身,要想修身养性,怎么可能呢?道光二十三年(1843)正月,曾国藩在日记中说:
“是日请客,至亥正方散。倦甚,勉强支持,仅乃了事。向使以重大之任见属,何以胜任?《记》云:“君子庄敬日强。”我日日安肆,日日衰尔,欲其强,得乎?譬诸树木,志之不立,本则拔矣。是知千方万语,莫先于立志也。”
同年二月,曾国藩再次在日记中谈到自己疲倦无力的状况,并再次强调“居敬”对一个人身心修养、精神面貌的重要性,论述颇为详细:
“倦甚,不能看书,眼蒙如老人。盖安肆日偷,积偷之至,腠理都极懈弛,不复足以固肌肤、束筋骸。于是,风寒易侵,日见疲软,此不能居敬者之不能养小体也。又心不专一,则杂而无主。积之既久,必且忮求迭至,忿欲纷来。其究也,则摇摇如悬旌,皇皇如有所失。总之,日无主而已。而乃酿为心病,此不能居敬者之不能养大体也。”
在曾国藩这样的理学家眼里,读书跟做学问、做人是一致的、相通的,书中讲的道理就要在自己做人的实践中去体验。因此,曾国藩在这里说,读书要在“敬”、“恒”二字上下功夫。
尽管曾国藩以理学家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做人、做学问、做事,无不遵循“敬”字,但他对自己仍不满意,他曾对一位朋友说:“国藩平生‘不敬’、‘无恒’二事,行年五十,百无一成,深自愧恨……仆待人处事,向多失之慢;今老矣,始改前失,望足下及早勉之。”这种不满意显示出他不断追求更高境界的进取之心。他的一生,就是在这样的“不自足”的驱使下,不断更上一层楼的。
不但在外做官要敬,在家中也要常常存敬之心。家是一个人生命、事业的出发点,能否在家中获得一个好的成长环境、好的基础教育,将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前途。曾国藩在家教中非常注意“敬”的培养。
他在家书中说:
“家中兄弟子侄,总宜以‘勤敬’二字为法。一家能勤能敬,虽乱世亦有兴旺气象;一身能勤能敬,虽愚人亦有贤智风味。吾生平于此二字少工夫,今谆谆以训吾昆弟子侄,务宜刻刻遵守。至要至要!家中若送信来,子侄辈亦可写禀来岳,并将此二字细细领会,层层写出,使我放心也。”
曾国藩很清楚,自己的这一家族之所以出现兴旺之象,是上代祖先们不断努力进取的结果,作为后辈,只有将这一传统流传下去,才能使家业保持兴旺。同时,敬重长辈,也是晚辈对长辈为家族振兴作出贡献的一种认可,一种景仰,从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来说,更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在家学会敬养父母,走上社会才会知道尊重他人,才能处理好人际关系。同时,一家之中有了“勤、敬”的门风,也才会赢得族人乃至邻人的敬重,这关系到一家之声誉。无论从个人发展、家族声望来说,“敬”都是不可或缺的家教内容。
除了不断提醒自己的几个弟弟在“勤、敬”上做好表率,督促子侄们认真践行之外,曾国藩对自己的儿子更是严格要求,一点也不马虎,并时时以自己为例加以警示:
“吾有志学为圣贤,少时欠居敬工夫,至今犹不免偶有戏言戏动,尔宜举止端庄,言不妄发,则入德之基也。”
这里,曾国藩告诫儿子曾纪泽要举止端庄、说话谨慎,不要整天嘻嘻哈哈,自己首先要严格要求,有让人值得尊敬的根本,别人才会尊敬。
对于亲友中出现的不肖之徒,曾国藩就写信给儿子,让他不要学人不好的一面,要谨小慎微,心中有知耻敬畏之心,然后说话、行事才会知道什么不该做、什么可以做。否则,由于自己的不慎,别人久之已经习惯,对你的所作所为根本不在乎,不尊重你,那你的成长就既没有了动力,也没有了压力,就会归于堕落。
除了谆谆教导自己的兄弟、子侄们以敬持家,以敬修身之外,曾国藩也非常注重自己的表率作用,言传不如身教,自己不正,怎么能正人呢?对于自己表现出来的不敬的行为、言语,曾国藩常常在日记中表达出警省、自责之意,意在提醒自己。
2.静以修身,勤于早起
《易经》中说:“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乐记》中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老子说;“致虚静,守静笃。”孔子说:“仁者静。”
“静”不单纯是哲学概念,还是助益人立身处世的智慧术语。“静”之一字,蕴含着奥妙无穷的人生真谛和成功谋略。
对“静”的妙用体悟最早的是诸葛亮,他在诫子书中谆谆告诫儿子,无论修身、立志、治学,都要以“静”为本: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欲静也,才欲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
在这段话中,诸葛亮提出了“静以修身”的概念。北宋理学家周敦颐更进一步提出了“主静”说。曾国藩的“静”字功夫,就是从“主静”来的。
刚考中进士之时,和许多幸登金榜的士子们一样,曾国藩也踌躇满志,得意非凡。但他一旦为官,由于治国平天下的志气一时无法伸展,也由于初入仕途缺乏为官经验,更由于耐不住翰林的清苦和孤寂,这时的曾国藩脾气极其暴躁,动辄就申斥仆人。曾国荃被接到京城随他学习,也因无法忍受他的脾气愤而归乡。正是在这个时候,他拜了唐鉴和倭仁为师,精研理学。唐鉴首先就告诉他:“静”字功夫最为重要。曾国藩也由此得到了修身要诀。
唐鉴针对曾国藩“忿狠”的缺点提出了“主静”的建议。曾国藩听了他的教诲,也觉得“静”字功夫正是他所缺乏的。倭仁指教说:“心静则体察精,克治亦省力。若一向东驰西鹜,有溺焉而不知,知而无如何者矣。”也是让他从“静”字下手。
曾国藩悉心听从两位师友的教导,首先遵照唐鉴指示精熟《朱子全书》;然后以倭仁为榜样,订立十二日课,使自己每天做事有章可循,有据可依,三是每天反省自我,详记日记,检讨自己的过失。但是对于好动不好静而性情又刚狠的曾国藩来说,“静”宇功夫也不是那么容易练成的。在动与静之间,恕与忿之间,他忍受着巨大的煎熬。
为了遵守十二“常课”,他专门找人刻印了一些簿子,上面列出详细的表格,每天他都要在表格中填写“常课”的内容。此外,他坚持写日记,练习书法文章。以致这些成了他一生的习惯,从来没有放弃,直到去世。
周敦颐认为,天地诞生之前的“无极”本来就是静的,因此人的本性也是静,只是由于后天染上了“欲”,才破坏了“静”的状态。只有通过“无欲”的功夫,才能实现“静”的状态。“静以修身”的要点就是制欲窒忿。曾国藩也确实是这样做的。他极力控制自己的奢欲、权欲、****,以俭朴为信条,以淡泊为依归,戒除淫思,甚至与朋友开玩笑都被他认为是可耻之事而痛加自责。
曾国藩效法倭仁把静坐看作克己的不二法门,他在给自己规定每日必做的功课中就有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念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卵之镇。”起初却苦不堪言,但曾国藩仍坚持了下来,不过“静坐”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与倭仁的静思己过已经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了。从此以后,曾国藩依旧坚持静坐,每当心思烦乱之际、疾病加身之时,坚持静坐,则可调和血气,缓和情绪。后来,曾国藩又补读了《老子》和《庄子》二书,深受道家虚静无为思想影响,“静坐”便由修身之法转变为养生之术了。
“静坐”是一种积极的休息方式,有利于调整人的情绪和机能,养精蓄锐,恢复和增强自身的抗病能力。
曾国藩深受“静坐”之益后,便将之视为养生金方。他一生遵守家法,不信医,不吃药,更不愿吃补药。即使生病,也多靠自身调解得法。他认为,静坐一次,就等于吃一剂汤药。
曾国藩认为静坐可以治肝病、眼病、气喘病,他还向亲友推荐传授静坐之法,直到去世前不久,仍坚持静坐。
早起具有重要的作用,首先能锻炼一个人的意志,其次,早起焕发精神,吃早饭营养充足,白天做事效率较高。再次,早起能够充分考虑好一天要干的事情,对所要做的事情根据轻重缓急予以合理安排,从容应对,所以俗话说“一日之计在于晨”。如果一个群体、军队,都能早起,则显出一番振作有为的气象。
曾国藩恪守曾氏家风,也正如《朱子治家格言》里所说的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在湘军中也是如此。要整顿湘军时,也以早起为重要要求。他在军中,每天凌晨即起,然后召集幕僚将领,一同吃饭。许多人没有早起习惯,颇以为苦,李鸿章初到曾国藩幕下,因为晚起而受曾国藩责备,实则不愿早起的并非只有他一人。
李鸿章当时以早起为苦,若干年后,他才感到受用无穷。曾国藩去世后,李鸿章对曾国藩的女婿吴永说:“我老师实在厉害,从前我在他大营中,从他办事,他每天一早起来,六点就吃早饭,我贪睡总赶不上。他偏要等我一同上桌。我没办法,只得勉强赶起,胡乱盥洗,朦胧前去过卯,真受不了。迨日久勉强习惯了,习以为常,也渐觉不甚吃苦。所以我后来办事,亦能起早,才知道受益不尽。这都是我老师造就出来的。”
曾国藩总结为人、用兵、治家、居官的失败规律,都离不开一个“惰”字。因此必须加以克服。他还说过“百种弊病皆从懒生”,认为懒惰是恶行、疾病的根源。“勤者,逸之反也”,“动,所以儆惰也”,克服懒惰,要靠“勤”字。
同治九年(1870)十一月,曾国藩在一篇“习劳而神钦”的伟论中谈到了“勤则寿,逸则天”的养身之法,认为勤不但可以兴家办事,还可养生。
曾国藩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认为懒惰不仅为败事之兆,还是致病之源。“劳则善心生,佚则淫心生”,“天下百病,生于懒也”,“百种弊病皆从懒生”,这些都是他亲身体验的结果。这些病既包括为人办事的毛病,也包括身心的问题。
一个人勤劳,不但锻炼了意志、毅力,在劳作的时候集中精力乐在其中,反而觉得很愉快,所以曾国藩称“勤”是生动之气,而惰则是衰退之气。如果贪图安逸,说明此人没有远大理想,没有为实现理想而努力奋斗的意志,实则百无聊赖,心灵空虚,并无快乐可言。为了填补空虚,他可能要采取一些不好的行动,养成更坏的习惯,由此走向末路。
曾国藩自己戒掉了烟瘾,也与勤奋有关。他认为,吸烟使人志气颓靡,百事俱废,当然无法勤以治事。他说,“绿营兵弁大半吸食洋烟,正是‘勤’字反面。”除吸烟外,其他不良嗜好也是“勤”的反面。何璟升任山西巡抚,曾国藩就告诫他:“激励之法,则以‘勤’字为先,又以远声色、屏嗜好为‘励’字之本。”勤劳之人,不良习惯必少,亦因此之故。
即使是早起,也有增益身心作用,如果行之有常,“其功实能长精神却疾病。”他对曾纪泽说:“起早尤千金妙方,长寿金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