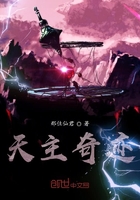如果死后确实有来生,你也许会问:为什么这么难以记得或者说它根本不记得呢?在《伊尔的神话》中,柏拉图讨论过人为什么没有对前生的记忆。在柏拉图的书里,伊尔是一位士兵,他被认为已经战死沙场,他似乎经历了死而复生。当他“死去”时,他看到许多景象,同时被训令复苏过来,以便把死后的情况告诉别人。就在他要回来之前,他看到那些正准备出生的生命,在恐怖、烟雾弥漫的热气中移动,通过“遗忘的平原”就是寸草不生的荒凉沙漠。当夜幕低垂时,柏拉图告诉我们:他们就扎营在“失念河”边,失念河的河水无法用任何器皿来装。他们每个人都被要求喝这种水,有些人还糊里糊涂地喝了很多。每一个人在喝水的时候,就忘掉了一切。伊尔本人被禁止喝水。醒过来时发现自己就在火葬场的柴堆上,所以还记得他所听所见到的一切。在道教的论证中,这种故事更是多得惊人,我们这里不必引述。
在佛教看来,天空的光明即是一种空性,在眼睛里的天空中,没有中心,没有圆周,只有纯净、赤裸的本性(或者说直觉)露出曙光。
透过佛教的修行,我们可以逐渐稳定心性.因此它就不再只是我们绝对的本性而已,而成为日常的事实,按我们习惯的说法,就是担水劈柴,无非妙道。如此,我们的习气越分解,禅定和日常生活间的差异就越小。渐渐地,你就像一个可以穿过玻璃门走到花园的人,不受任何隔碍而走入那绝对的般苦、涅槃世界。凡夫俗子的心因此而找到了自己的基础,他对死亡的恐惶因而也就被有效地减弱,于是他可以越来越轻松地安住在心性的明光之地。
一切宗教所希望的其实正是未来世界免于残酷和恐怖,人类得以生活在心脏的终极快乐,透过我们的努力而获得实现。这就是目前中国哲学界所最常关注的话题:终极关怀。
藏族宗教神学家索甲仁波切在《西藏生死书》中描述道:伟大的上师顶果钦哲仁波切,于1991年9月27日,在不丹的滇普圆寂,享年82岁。见过他的人,没有人会忘记他像一座高大、庄严的山,身上散发出最深厚的温柔宁静,以及自然丰富的幽默感,使得他虽然高大,却不会令人生畏。那种安祥和喜悦正是最高体悟的象征。
西方人也许会惊奇地发现西藏有这么多的转世者,而他们大多数是伟大的上师、学者、作家、神秘家和圣贤,正是这样一群神神秘秘的人,对于佛法和社会都有杰出的贡献。他们在西藏历史上,扮演着中心的角色。我们宁可相信这种转世的过程不只限于西藏,也发生在其他一切国家一切时代中,正像帕斯卡尔和詹姆斯在信仰面前的赌博一样,我们不妨按中国人的说法,对上帝、天和道进行一次赌博。这样,在我们看来,历史上出现过的许多艺术天才、精神领袖和人道主义者,他们虽然做的是与科学家不同的事业,却同样帮助了人类的前进。例如甘地、后期的爱因斯坦、林肯、德蕾沙修女、莎士比亚、圣法兰西斯、贝多芬。这些人的贡献不同,但我们都可以承认他们是菩萨。至少,当西藏人一听到这些名字时,假如他是有教养有文化的人,听懂了这些人的故事,会立刻称这些人都是菩萨。
既然各大文明都有宗教的根底作为文化的基础,中国人不是例外,西藏人更不是例外。
凡是有真正同情心的人都会承认西藏人在苦难中摸索数千年的精神价值。
这也是消极的宗教与积极科学的意义和共同价值。
有平衡就有冲突,有冲突就意味着内中的分裂。这就为目前达赖和班禅的分裂奠定了一定的历史阴影性文化基础。宗教的不幸,莫过于宗教领袖的不和,若加以政教合一的实际影响,这就会铸造成为民族的不幸。十三世纪达赖时,由于英帝国主义的挑拔离间,达赖和班禅之间已经产生了一定的隔阂。辛亥革命后,由于出现了政治权力的一度真空,二位活佛的不和就导致了1924年11月15日晚九世班禅从藏区出逃,转入内地。直到20世纪50年代后,在中央政府的协助下,班禅在国外所从事的分裂即西藏独立活动,一直对藏民的心理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直到现在,这件事仍然在西藏社会不安一的重要因素。加之近年来台独势力的嚣张,并与达赖国际社会上悄然呼应,对祖国的统一大业构成了严重的不利影响。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人类精神文化宝库中的重要遗产之一,藏传佛教文化蕴藏着无穷的智慧,还有待我们认真甄别,充分汲取,它是青藏文化的一份独特的奉献。
青藏文化中确实弥漫着宗教的和神秘的烟云,但也不乏科学的精神和理性的光芒。我们相信,一个能在宗教领域显示卓越才华,充满无限智慧的民族,也一定能以崭新的姿态,再创辉煌,与我国各族人民一起,步入迷人的21世纪。
三、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
汉代派王昭君到荒蛮的大漠与匈奴和亲的佳话,到了唐代,在青藏高原的冰雪王国来了一次重演,文成公主嫁给了藏王松赞干布,这是关于中国版图合法性的一次巨大的宏观叙事。
西藏有史记载的历史是从松赞干布开始的。
正像宗教是神话的续第一样,政治是历史的延伸。历史的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政治就会在质变中粉墨登场。在象雄文化的末期,它的割据性“十八王”政治就只能让位给真正的藏王松赞干布了。就像成吉思汗之于蒙古族一样,松赞干布也可以说是藏民族的“一代天骄”;他是一位有雄才大略的人,是一个半人半神式的政教合一型的领袖,是一个韦伯式的“克瑞斯玛”人物。政治上的雄才大略和宗教上的善爱慈悲不同,后者代表人类天使的一面。前者代表人类世俗的一面。我们得学会区分这一点,学会这一点,以便使政治成为政治,宗教成为宗教。政治和宗教的分离也许是我们这个民族未来最深刻的心灵变革之一。因为让上帝管凯撒的事,正像让凯撒管上帝的事一样荒唐。当我们一方面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另一方面又说“人人可以成圣贤”;“人人可以成尧舜”时,我们实际上在犯一个逻辑错误。
藏族的历史非常悠久,早在商、周的金铜铭文中,就有青藏高原上藏民活动的记载。羌族如果确系藏族的一支甚或惟一祖先,那么藏族史也就大体上是清楚的。但无论如何,到了唐代以后,藏地民族的历史脉络是清楚的。正像全人类最早的日食是靠汉文记载下来的一样,西藏的许多历史史实也是靠汉文记载下来的。
在这之前所发生的一切,我们只能通过口耳相传的故事来补充了。可是正是这口耳相传的故事,最能见出一个民族的性格底蕴和文化秘密。正像通过阿凡提我们可以了解维吾尔族人的性格重要方面一样,关于格萨尔的传说也能帮我们了解西藏人的性格特征。但当真实的历史老人登场时,它似乎也喜欢编造出一系列的故事以壮声威。当然,时间老人的淘洗已经使口耳相传的故事变成了各民族文化的金子。关于松赞干布的传说,也仍然值得一叙。
据说在很久以前,雅碧河谷居住着一群牧人。一天,人们发现了一个雄姿英发的年轻人,由于这小伙子与当地人的言谈举止很不相同,放牧的人们不知该如何善待这位英俊少年。于是就派人去向领导人汇报。作为领导人的长老听了汇报,很严肃地派了12个聪明的巫师,去探问那英俊少年的来历。这青年用手指向天上一戳,他们立即明白了,原来他是从天而降的“天神之子”,这让他们分外高兴。于是,这12位中为首的一位立即用最高的礼遇——趴在地上伸长脖子,让这位尊贵的青年骑在自己的脖子上,其余则簇拥着抬到了长老面前。
此后,这喜讯便立即在青藏高原传了开去,人们纷纷前来,以一睹“天神之子”的风采为快。大家看他果然英俊潇洒,就民主公推他为领导。这就是后来被叫做“吐蕃”部落的首任当家人。人们把他尊称为“聂赤赞普”,意思是“用人脖子当宝座的英杰领袖”。从那时候开始,历史上就把藏王称为“赞普”。从他开始到吐蕃王朝的建立,共传了32代,第33代传人就是松赞干布。
松赞干布吐蕃赞普(617~650),吐蕃王朝缔造者。汉文史籍称作弃宗弄赞、弃苏农或器宗弄赞。7世纪初叶,继其父囊日论赞为赞普。即位后首先平定内部贵族叛乱,既而兼并青藏高原诸部族,一举完成其祖、父所开创的统一大业,建立奴隶制政权,定都逻娑,建宫殿于布达拉山。松赞干布的功业迅速改变了冰雪王国的面貌。他在位期间,励精图治,制定一系列法律、职官、军事等制度;努力发展经济,统一度量衡制;积极开创文化事业,创造文字,引进佛教,开始翻译佛经。除致力于王朝内部建设外,还积极寻求建立和发展与周边部族的睦邻友好关系,以巩固和发展新生的吐蕃政权。先迎娶尼婆罗墀尊公主入蕃,继而又与唐文成公主和亲,先后修建大昭寺、小昭寺。松赞干布还十分注重吸收汉族文化和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多次遣贵族子弟至长安学习汉学,又从汉地引进医药、数术、工艺等知识。他在位期间对吐蕃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及加强与周边民族之间的联系,均有重大贡献。
唐贞观二十三年(649)唐太宗卒,唐高宗即位,封其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等,并携刻其像于石,列于太宗昭陵。唐永徽元年(650)松赞干布卒于彭域(今西藏彭波),唐朝遣使臣鲜于匡济贲资书入吐蕃吊祭。因松赞干布最早引入佛教,后世藏文史书将其与墀松德赞、墀祖德赞并称为吐蕃时期“三大法王”。
从松赞干布的人生经历来看,他确实是西藏历史潮流上非同小可的人物。松赞干布父子很像罗马帝国的凯撒和他的外甥屋大维,前赴后继,终于成就了一番辉煌的事业。
文成公主(?-680)唐太宗之女。唐贞观年间(627649),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派遣大相噶尔东赞为请婚使者,赴长安请婚,唐太宗以之女文成公主许嫁松赞干布。并诏令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为主婚使,持节护送文成公主入蕃。文成公主途经吐谷浑境时,受到吐谷浑河源郡王诺曷钵和弘化公主的热情款待。松赞干布率群臣亲自到河源附近柏海(今青海玛多县境)迎接文成公主一行,他以子婿之礼谒见江复王李道宗,然后与公主一道同返逻娑,并于玛布日山(今拉萨布达拉山)专建宫室安置公主,至今布达拉宫尚保存有他们成婚洞房遗址。文成公主到拉萨后主持建造小昭寺,安放自长安带去的释迦佛像(后移至大昭寺)。公主知书识礼,博学多才,笃信佛教,兼通卜之学。入蕃时,除携带一尊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外,还携带了大量的其他物品。同时,中原地区的医药、历算、纺织、造纸、酿酒、制陶、碾磨等也都传入吐蕃;传说她还随带工匠5500人及谷物、牲畜多种。对吐蕃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唐蕃关系的加强,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永徽元年(650)松赞干布卒后,她继续在吐蕃生活了30年,教吐蕃妇女纺织、刺绣,深受吐蕃人民的敬爱。去世以后,其事迹在藏族地区以戏剧、壁画、民歌、传说等形式广为流传,影响深远。
文成公主虔信佛教,她在喇嘛教被认作为绿度母的化身。度母,藏语叫“卓玛”,在藏传佛教中,它的意思是观音化身。在藏区受到极大的崇敬,是度众生的伟大母亲。现在布达拉宫仍存有文成公主的塑像。文成公主带去的释迎牟尼像至今可仍保存在拉萨的大昭寺。
文成公主的名字不仅载入史册,而且一直活在藏族人民的心中。藏族人民在怀念文成公主,用两个节日来纪念她:一个藏历四月十五日“沙喝达瓦节”,即公主到达拉萨的日子;另一个是藏历十月十五日,相传是公主的诞辰。在拉萨的布达拉宫和大昭寺内,至今还完好地保存着相传是唐代传下来的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塑像。
在今大昭寺前,有一传说为文成公主亲手栽植的柳树,人称“公主柳”。清代杨睽《咏柳》诗曰:“一株灵和树,婆娑倍可怜。根种依佛土,栽植记唐年。”小昭寺与众不同地坐西向东,以便她随时随时可以摇望一下那远在天边的大唐故土。小昭寺在大昭寺的北面不远,清代在此为官的孙士毅赋《小昭寺》诗曰:大昭北去小昭迎,金瓦流辉玉砌平。不信西来归净土,却因东向往神京。”在这小诗的后面,孙士毅特意加注曰:“小昭寺门向东,因唐公主思故乡也。”于是自从公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
64年,唐王朝遣宗室江夏王李道成持节送公主入藏,松赞干布专为公主营造城邑,立屋宇,以为居处。
四、藏式建筑
民居被认为是历史文化的物质载体,宗教则是文化的基本质量,民居也就被视为宗教的物质载体。聚落的形成与分布一般与宗教、贸易、生产等因素相关,而藏族民居聚落的形成、分布与宗教的关系更密切。凡有寺院的地方,其周围必形成民居聚落;寺院历史越悠久,规模越大,其周围的聚落也越庞大。
如果说“文化是一种通过符号在历史上代代相传的意义模式”,那么作为符号载体的宗教就可以说是文化的基本质量。而住宅建筑——民居,则被人们认为是历史文化的物质载体,是民族精神的物化体现,更因为其相对稳定性和对民族文化的保留,而被誉为社会历史的“活化石”。宗教作为“文化的基本质量”,在藏族民居上有强烈的表现。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的民居能比藏族民居更具有宗教色彩。聚落的形成与分布一般与宗教、贸易、生产等因素相关,而藏族民居聚落的形成、分布与宗教的关系更密切。凡有寺院的地方,其周围必形成民居聚落;寺院历史越悠久,规模越大,其周围的聚落也越庞大。
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家庭的物质设备包括居处、屋内的布置、烹饪的器具、日常的用具,以及房屋在地域上的分布情形,这一切初看起来,似乎是无关轻重的,它们只是日常生活的细节罢了。但事实上,这些物质设备却极精巧的交织在家庭的法律、经济、道德等各方面”。藏族民居丰富多彩,藏南谷地的碉房、藏北牧区的帐房、雅鲁藏布江流域林区的木构建筑各有特色,就连窑洞也能在阿里高原上寻见。西藏民居的历史十分久远,四千年前的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已有了丰富的建筑遗存。
藏族最具代表性的民居是碉房。
碉房又称锅庄,一般是藏族农区的居住建筑,牧民在冬季牧场修建定居点时直接借鉴了碉房的形式。这在拉萨等大城市较为常见,其外形端庄稳固,风格古朴粗犷;外墙向上收缩,依山而建者,内坡仍为垂直。碉房一般分两层,以柱计算房间数。底层为牧畜圈和贮藏室,层高较低;二层为居住层,大间作堂屋、卧室、厨房、小间为储藏室或楼梯间。若有第三层,则多作经堂和晒台之用。碉房具有坚实稳固、结构严密、楼角整齐的特点,既利于防风避寒,又便于御敌防盗。墙壁粉刷成白色,阳台、窗前种植花草,在高原晴空万里的衬托下显现出一种迷人的油画般的绚丽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