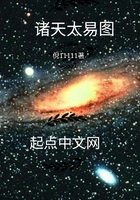这份依恋使我觉得任何其他娱乐都是多余和无聊的。我除了去戴莱丝家以外,哪儿也不去,她的家几乎就成了我的家。这种深居简出的生活对我的工作大有裨益,不到三个月我的歌剧的词和曲就几乎全部写好了,只剩下一些伴奏和少数中音部没有写就。我非常讨厌剩下来的这种单调乏味的工作,便建议菲里多尔来做这事,并承诺会给他一点报酬。他来过两次,给奥维德那一幕加上了一些音符。但他耐不住这工作的枯燥乏味,况且完工的日子遥遥无期,收益也不一定有保障,于是他就再也不来了。我只好自己完成了这项工作。
歌剧写好之后,接下来要做的是如何将它兜售出去,这个任务比写歌剧更为艰巨。在巴黎,倘若你要遗世独立,你注定会一事无成。当我从日内瓦回来的时候,果弗古尔介绍我认识德·拉·波普利尼埃尔先生,现在我想让他助我一臂之力。波普利尼埃尔先生是拉莫的麦西纳斯式的保护人,而波普利尼埃尔夫人则是拉莫的学生,她对老师毕恭毕敬。可以这样说,拉莫完全是他们家的主宰者。我估摸着拉莫应该会很乐意支持他的一个弟子的作品的,就想把自己的作品送给他瞧瞧。但他拒绝看谱,说他不会看谱,看起来太吃力。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就建议可以将曲子奏给他听,并找了一支乐队来演奏。我自然是求之不得。拉莫总算同意了,不过嘴里还是嘀嘀咕咕的,反复说什么这曲子不可能好到哪儿去,因为作者没有经过专业训练,音乐素养是自学得来的。我挑出五六段最精彩的曲子,他们给我找了大约十个合奏的乐手,又找了阿尔贝、贝拉尔、布里朋内小姐做歌手。序曲一奏响,拉莫便盛赞起来,暗示这曲子不可能出自我手。每奏一段,他都显出极不耐烦的的样子。但在听到了男声最高音那一段,歌声雄壮宏亮,伴奏绚烂多彩时,他再也按捺不住了。他粗暴地斥责我,说他听到的曲子有些部分极为精彩,似乎出自艺术巨匠之手,而其余的部分则相当地低级幼稚,像是音乐外行写的。他的这番评论让所有在座的人都有些不快。确实,我的作品的质量忽高忽低,参差不齐,就像所有那些未受严格训练的人仅凭才气写成的一样。拉莫声称我是个没有才华和品位的可耻的剽窃者。可在场的其他人,特别是这家的主人并不这么认为。当时黎希留先生常和拉·波普利尼埃尔先生见面,他听人说起过我的作品,表示希望从头到尾听一遍,如果效果不错,可以拿到宫廷中去演奏。就这样,这部作品便由宫廷出钱,在宫廷娱乐主管博纳瓦尔先生家里,用大合唱队和大乐队演奏了。弗朗科尔担任指挥,演出的效果很惊人。公爵先生不停地高声喝彩,在《塔索》那一幕中的一段合唱完毕之后,他起身向我走来,亲切地握着我的手,说:“卢梭先生,这段和声真美妙,我从来没有听过比这更美的了,我要把这部作品拿到凡尔赛宫去演奏。”波普利尼埃尔夫人当时也在场,却一句话也没有说。我们邀请了拉莫,可是他没有到场。第二天,波普利尼埃尔夫人在梳妆间接待了我,她的态度很冷淡,还极力贬损我的作品。她说尽管刚开始的时候黎希留先生被我作品中浮华不实的东西所迷惑,但是他很快就省悟过来了,她建议我不要对这部歌剧抱任何希望。不久公爵先生到了,他说话的口气却和波普利尼埃尔夫人明显不同,他对我的才能恭维了一番,似乎仍然打算把我的作品拿到宫廷去给国王欣赏。他说:“只有《塔索》这一幕不能在宫里演出,必须另写一幕。”我闻令而行,马上回去闭门修改起来,不到三个星期就另写了一幕来代替《塔索》,主题是赫希俄德得到一位缪斯的启迪。我想方设法把我的才华发展史的一部分以及拉莫对此的嫉妒写进了这一幕。新写的这一幕没有《塔索》气势磅礴,却更加舒展,音乐也同样庄重典雅,而且写得好很多。如果其他两幕能和这一幕水平相当的话,全剧一定会非常出色。但当我正要将全剧杀青时,另一个工作迫使我将它搁置起来。
在丰特诺瓦战役后的那个冬天,凡尔赛宫庆典不断,这段时间有好几部歌剧要在小御厩剧院上演。伏尔泰的剧本《那瓦尔公主》就是其中之一,它由拉莫配乐,并刚刚作了修改,易名为《拉米尔的庆祝会》。它在题材上的变化,要求好几场幕间歌舞都要更换,词和曲也都要改写。问题是很难找到能胜任这个双重任务的人。伏尔泰和拉莫当时都在洛林紧张地从事歌剧《光荣之庙》的创作,抽不开身。黎希留先生想到了我,建议我承担起这个任务来。为了使我能搞清我该做哪些事情,他还把诗和音乐分开寄给我。我首先想到的是只有征得原作者的同意我才能着手修改歌词,因此我就此事给伏尔泰写了一封很客气甚至可以说是很恭敬的信。下面就是他的答复,原件见信函集A第一号:
1745年12月15日
先生,迄今为止在一个人身上无法兼得的两种才能同时集于您一身,对我而言,这就是两条很好的理由,让我敬重您和力图爱您。可是我要为您感到委屈,因为您把这两种才能用在了一部根本就不值得的作品上。几个月前,黎希留公爵先生给我下达命令,让我在短时间内写出几场死气沉沉而且支离破碎的戏的琐屑而差劲的梗概,以配合跟这场戏完全不协调的歌舞。我一挥而就,写得又快又差。我将这糟糕的草稿寄给黎希留公爵先生,本以为他不会采用,或者得由我改一下再用的。很幸运,它现在落到了您的手里,那就请您随意处置吧,我已经将它忘得一干二净了。它只是一个草稿,写得又那么仓促,其中肯定有不少错误。我毫不怀疑您已经全部改正了。并且补足了所有的不足之处。我记得,在诸多愚蠢的错误之中,有这样一条,就是在连接歌舞的几个场景中,我忘了交待那位石榴公主是怎样从监狱来到一座花园或宫殿的。因为为她举办宴会的是一个西班牙贵族,而不是一个魔术师,我觉得不能像变魔术一样处理情节。先生,请您再核查一下这个段落,因为我记得不大清楚了。请您看看是否有必要让牢门打开,使我们的公主被从那儿领到特意为她准备好的一座金碧辉煌的美丽宫殿中去。我深知这一切都没有任何价值,一个有思想的人不应该一本正经地做这些无意义的事情。但即便是针对这样一场无聊的幕间歌舞,既然我们想尽量减少不快,那就应该处理得更合乎情理一些才行。
我完全信任您和巴洛先生,希望很快就能有幸向您致谢。专此即颂。
令人一点也不奇怪的是,与他后来写给我的那些傲慢无礼的信比较起来,这封信写得实在是太客气了。他以为我是黎希留先生的座上红人,因此他那广为人知的世故和圆滑促使他对一个不知底细的刚出道的人也极为客气,不过当他知道了我有多大分量时,情况就不一样了。
我既得到了伏尔泰先生的授权,又不必顾忌一心想贬损我的拉莫,因此就甩开膀子干了起来,只用两个月便完成了任务。我在歌词方面下的功夫不多,只是尽量让人觉察不到风格上的差异,我相信自己已经做到了这一点;而在音乐方面,我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因为它更难。除了要写好包括序曲在内的几支过场曲子之外,我负责处理的全部宣叙调都很困难,我必须用少量的句子和快速变调将调子大不相同的一些合奏曲和合唱曲连缀起来,从而可以对任何曲子都不作改动和移调,我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拉莫指责我破坏了他的曲子。这只宣叙调我写得很成功,它音调适宜,雄壮有力,尤其是变调很灵活。一想到我能有幸和伏尔泰与拉莫这两位名家以这种方式合作,我的才情就迸发了出来。我敢说,在这项无名无利的、公众毫不知情的工作里面,我几乎始终与我的两个榜样不相上下。
这个剧本按我修改的样子,在歌剧院里排练了。三个作者只有我一个人到场。伏尔泰不在巴黎,拉莫没有来,或者是有意躲起来了。
第一段独白很凄凉。开头是这样的:
啊,死神!来了结我这苦难的一生吧。
我的音乐当然要和它相对应。可正是在这一点上,波普利尼埃尔夫人对我大加指责,她尖酸刻薄地说我写的是一段哀乐。黎希留先生很公正,他说应该先查一下这段独白的词儿是谁写的。我把他寄给我的手稿拿给他看,证明是伏尔泰写的,于是他说:“这么看来,过错全在伏尔泰一人身上。”在彩排过程中,凡是我改动过的地方,都遭到了波普利尼埃尔夫人的猛烈抨击,而受到黎希留先生的辩护。然而,我的对手实在太强大了,我被告知自己的作品有多处需要修改,而且还必须征求拉莫先生的意见。我非但不能得到梦寐以求的,而且确实应该享有的夸奖,反而落得这样一个下场。我万分沮丧,伤心欲绝地回到了家里。由于过度疲劳和悲伤,我病倒在了床上,一连六个星期都出不了门。
拉莫要对波普利尼埃尔夫人指出的那些地方进行修改,便派人来找我,向我要我那部大歌剧的序曲,以替代我刚写的那一个。幸好我觉察到了他的奸计,就拒绝了他。由于离公开上演只剩下四五天时间,他来不及写个新的序曲,于是只好保留我写的这个序曲。它是用意大利风格写成的,当时在法国还不大为人所知。然而,它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据我的亲戚和朋友缪沙尔先生的女婿,御膳房瓦尔玛来特先生告诉我,音乐发烧友们对我的作品非常满意,而且听众们也辨别不出哪些音乐片断是我写的,哪些是拉莫写的。但拉莫和波普利尼埃尔夫人串通一气,想尽各种办法来阻止别人知道我也参与了该剧的写作。在散发给观众的歌词本上,一般会给出作者的名字,但是这一回上面只有伏尔泰一个人的名字,拉莫宁可不署自己的名字,也不愿看到我的名字和他的名字并列在一起。
等我身体稍稍好些,能够出门了,我就想马上去见黎希留先生。但是太晚了,他刚刚起身奔赴敦刻尔克部署开往苏格兰的部队去了。等他回来之后,我却又懒得找他,心想这已经太晚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因此也就失去了我应得的荣誉和报酬。我的时间,我的劳作,我的烦恼,我的疾病以及治病所花的钱,都没有得到任何的回报或补偿。尽管如此,我始终认为黎希留先生对我很有好感,并且很赏识我的才华。但是,只怪我自己命运蹇涩,再加上波普利尼埃尔夫人从中作梗,使得他的好意没能发生作用。
这个女人对我如此反感,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一直在竭力地向她释放善意,还经常登门拜访她。果弗古尔为我点明了其中的缘由。他对我说:“首先,她和拉莫的关系非同一般,她是拉莫公开的赞助人,因此不能忍受任何人跟拉莫竞争;其次,您一出生就担上了一项罪名,使得她对您憎恶不已,永远也不会原谅您,那就是您是日内瓦人。”接下来,他给我详细地解释了一下。于贝尔神父也是日内瓦人,是拉·波普利尼埃尔先生的密友,他曾经极力劝阻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娶她做妻子,因为于贝尔神父对她的为人了如指掌。婚后,她便对于贝尔神父恨之入骨,连带着恨起所有的日内瓦人来。果弗古尔又对我说:“尽管拉·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对您有好感,但别指望他会支持您,因为他太爱他的妻子了。她对您如此的憎恨,而且她既凶恶又狡猾,您和这一家子是一辈子也处不好的。”我接受了他的意见,死了这条心。
几乎在同一时期,这位果弗古尔先生又给我帮了一个大忙。我那值得尊敬的父亲刚刚过世,享年约六十岁。要不是因为我当时处境艰难、步履维艰的话,我会为父亲之死感到更加哀痛的。在他生前,我没有想过向他要回母亲遗产的剩余部分,并让他一直享用着这笔财产的微不足道的收益,在他死后,我就没什么顾忌了。不过,问题是我缺少有关我哥哥的死亡的合法证明。果弗古尔先生主动答应为我解决这个难题。在诺尔姆律师的大力帮助下,这个难题真的解决了。由于我急需这点小钱来改善经济状况,而这件事情能否办成,其形势不是很明朗,因此我焦急地等待着最后的准确消息。
有一天晚上,我一回到寓所,就看到一封应该跟这件事有关的信。我浑身颤抖地拿起这封信,想拆开,同时却在心里为自己的这种焦急感到万分羞愧。我暗暗地对自己说:“怎么!让雅克竟会被私利和好奇心制服到如此地步吗?”我随即将信放回到壁炉台上,脱掉衣服,平静地躺下,睡得比平时还香甜。第二天,我起得很晚,也没有再去想那封信了。到穿衣服的时候,我又看到了那封信,于是我从容不迫地拆开它,发现里面有一张支票。我的心里顿时乐开了花。不过我感到最快乐的是我终于控制住了自己。在我的一生中,类似的情况出现过好多回,由于时间有限,此处不能细表。我把这笔钱寄了一小部分给可怜的妈妈,想到我本该跪着奉上我的全部款项的那种幸福时光,我不禁潸然泪下。她给我的每一封信都暗示着她的生活困苦不堪。她还寄来了成堆的配方和秘诀,声称我可以用它们致富,同时也给她带来好处。对困苦的感受压榨着她的心灵,消弱着她的理智。我寄给她的那一点小钱又落入了缠在她身边的那帮浑蛋的手中,她一点也没有享受到。我感到异常气愤,因为我不想跟这帮浑蛋分享我的活命钱,特别是在我试图将她从这些人的手中解救出来的努力失败之后更是如此。后面我会谈到这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