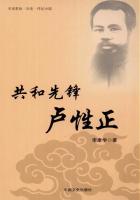“过年两天(元旦和初二),我整整写了两天文章,叫做‘关于十年来设计研究事业中几次方针政策错误的意见’,给他们去北京造反的人带去做参考。”
(《家信》1967年1月5日)
“这两天也忙着译书,既应之,则做好之。也是帮助一所生产起一点点绵力吧。今日已译完,约25000字,再校两三天即可交稿。所以前天没有给你写信。”
(《家信》1967年1月18日晚)
“这两天写字写太多了,每天五千字以上,晚上写这封信竟有手腕发酸的感觉了。”
(《家信》1967年2月27日晚)
但他并不满足于这些事情,他希望做的是真正的技术工作。
“我这里住着,一批批送走不少人了。现在也不去查第几周了。只是皮夹子里,1966年日历用完后,自己画一张1967年1月1日历时才记起,这已经是来一所第29周了。这个下午还是打算看看书、写完信后还打算再读一遍元旦社论,太重要了。我这个在医院、疗养院住惯了的人,又多了这么一次长住招待所的经历!真是想不到的事。”
(1967年1月5日)
“我倒是很想回来,一方面是游离于运动之外很不好*,另一方面长期不工作也很难受。我很希望回来搞具体工作,如64改装,自己画图或拉算尺,也动手去画模线……再也不想光动嘴不动手地浮在上面了。”
(原信注:*在一所参加这边的运动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不是一所成员,而过去又是当权派。)
(1967年2月9日)
“我自己,当然也想回去,既抓生产,又闹革命,两件大事。但是,我希望从十所角度出发,最好能向这边军管小组来一封信,要我回去,但仍提出要求先定性……只有当军管小组认为短期内不能定性,但可以先回去时,所里再同意我带着问号回去。我自己,带着问号也可以愉快地工作……
我仍在学习,在译文章,心情仍在中上状态。有时也着急想回去,但有时又想,大概也差不多了。大学4月也要上课,那么这批教授的问题也该提到日程上来了,中央一管,什么都好办了。我估计3月中对于类似我的问题总会有所动静。再来35个7天是无论如何不需要的。”
(1967年2月27日晚)
“35个7天”是他到沈阳49天时提及的一个计算方法。
“又是星期天了,记得是夏至前一天离开家的,而今天是立秋后一天了,前后刚好7个星期,七七四十九天了。好在我是出差住招待所住惯了的,也是住医院住惯了的,倒也还没有什么太特殊的感觉。”
(1966年8月9日)
“计算着来此已11周,77天了。仍每天自己看书,没有一个人找我谈一句话(来此后仅第二周常委和工作队找我开过一次小会,此外,无一负责人和我谈过话,我也不去找)。看来,在这里虽然用不着70个7天,但至少也得17个7天,这就是说,再住一个半月是完全有可能的。”
(1966年9月8日)
“今天是厂星期五,这个第14周就这么过去了,下一周,第15周也会很好过的,中间有三天放假,放假前还有一两天打扫卫生等。要再开始是10月7号的事了。看来,我的预言(17个7天)是又不够了。”
(1966年9月27日)
从那以后,他仔细地计算着自己在沈阳的时间。
“17个7天是肯定不够了。发个大愿,打算27个7天,刚好到年底吧。”
(1966年10月6日下午)
“2月23日,星期日。这在我的小日历上是第9个月的开始,也是第36周的第1天。换句话说,去年讲的所谓70个7天,真的已经过了一半了。但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真的到70个7天,即到今年的10月下旬去的。”
(1967年2月21日)
无奈中,他用自己特有的幽默揶揄道:
“一所的同志们,如果认真想一想,把兄弟所的一个技术领导干部这么冻结在一所招待所里已经快4个月了,真要过一个冬天也实在是不很合适的。”
(1966年10月15日)
他企盼的是尽快回十所参加具体的技术工作。他认为,自己的科研路线等问题主要是在一所,只要一所能够给一个初步结论,他不是四类干部、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就可以回十所继续工作。至于担任不担任领导干部,他想得不多。即便不担任领导,他仍可以画图或拉算尺,也动手去画模线……
对老保姆的关心
在从沈阳给妻子的信中,徐舜寿对家中老保姆的去留一事做了细致入微的安排。
1958年,苏联十月革命节(11月7日)前,宋蜀碧来到沈阳,与已经带着孩子到沈阳安家的徐舜寿会合。当时小儿子徐源刚1周岁多,而宋蜀碧和徐舜寿都要上班,急需要请一个保姆。正好邻居家有一个保姆,不打算再用了,就被宋蜀碧请到自己家。这个保姆就是家在河北保定的王玉芝大娘。
随着运动的发展,家中请保姆已经被上纲到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高度,有红卫兵组织发令——“限期取缔”。从1966年7月27日提及大娘事起,徐舜寿多次在信中就大娘的事情写了自己的意见:
“招待所面对球场,每夜有游行,烧军衔,烧火箭鞋,化妆品。沈阳在剪辫子,烟酒也不卖了……另外保姆也限三天、七天取缔,所以大娘就早点叫走吧,不必等我了。”
(1966年8月28日晚)
“大娘事,可请她早回去,但要请刘平南他们先去信和公社联系,不要户口落不进!千万不要这边先迁出,那边又落不进,可要注意!她要等我回来,告诉她不必了,我很好,叫她不要不放心。”
(1966年9月13日)
“大娘事如何?你看,是不是必要时可先走?不迁户口(为此粮票,尤其是全国的,得省一些了)。问她好,问孩子们好。”
(1966年9月17日)
“这两天想到王大娘的事,我想还是要走才对。问题是何时,怎样走,我们要负责安排好。户口是个大问题,无原籍同意,宁可人先走,后迁户口。钱,劝她存几百元在阎良,一二百元一张的记名定期存单,带方便,丢了也可挂失,到期可由保定银行转取。一起带现款太不方便。行李,可由阎良买车票托运保定。西安保定车挤不挤得上,可托大姐、张戈早些打听。我看中秋、10月1日过后就行。如太挤可拖一拖,但也不要拖太久了,久了又生变。请她不要等我回了,也不必惦记我的事。告诉她,在这个时代好人是不会遭罪的,而她在我们家住了这么久,我是好人坏人还看不出来?问她好,问孩子们好。”
(1966年9月27日 )
“大娘回去吧。只是钱、户口、路上的照应要安排好。告诉她如果想孩子们,则等过几年可以来玩,住个把月什么的。”
(1966年10月6日下午)
“大娘回去事你的决心我同意。我也主张她回去。公社那边可过一两个月再说,但需请她回去后积极办入户口事(一般人走了粮票只给三个月)。我们不应当从消极方面,因为人们贴大字报说得太不像话了而让她回去;而是从积极方面,锻炼孩子们独立生活和锻炼我们自己出发。”
(1966年10月24日)
“大娘走了没有?她屋子里的旧收音机问她要不要?可以送她带走。问她好吧。”
(1966年10月26日)
“大娘还是走吧,应该这样试一阵,到明年我们如果很忙,照顾不过来时再另想办法。”
“那个旧的无线电,送大娘带回去吧,就是拿的时候小心些,底下缺螺丝。户口事,早些办……”
(1966年11月4日)
一度,他听说铁路运输非常拥挤,写信告诉妻子,让大娘先别走。以后,随着红卫兵停止大串联,火车开始恢复正常秩序。他又叮嘱,“大娘要有人同行才走很对”。这样的关切一直到12月大娘回到保定老家。
对徐舜寿夫妇的关心爱护,大娘牢牢记在心里。在回家后的第一个阳历年,她写了一封信给宋蜀碧,信的开头称宋蜀碧为“亲爱的女儿”。信明显是托人代笔的,但其中的言语情真意切。
“我回忆起来,你们对我的照顾真是体贴入微、无微不至,再也无法挑选。再说你们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把我送到了火车站,对于我衣食、水都是照顾的百般周到,因此使我一帆风顺,平安地来到了故乡,为此望女儿对这方面多加放心为盼,千万不要为我的事影响了你们的工作和健康。就让你们把全部精神投入到紧张的革命运动中去吧。”
在回家半年以后,王大娘又来了一封信,从这封信我们可以知道,在她离开半年以后,徐舜寿和宋蜀碧还在为她寄粮票。
“你的来信全部收到,邮来的粮票全收到了,请放心。接到你的来信我连续去了三次,但都给退回来了,也不知是什么原因,都是地址上的问题,急得我真想坐上火车前去一次,这次7月2号接到你的来信,才按五号信箱去这封信,请原谅。
……
从我回来已经半年了,我是十分想念你们的,现在孩子们身体都很健康,生活愉快,都很活泼吧。你们身体都很健康吧。
现在我的身体很健康,生活很愉快,一切都好,请放心。等以后有时间我一定去看望你们。”
王大娘知道,在信中告诉她“在这个时代好人是不会遭罪的”那个人是好人。但她不会知道,在写下“我是十分想念你们的”时候,那个好人和他的家人正在炼狱中承受着生不如死的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