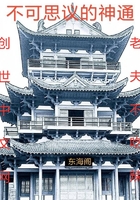“老爷回来了!老爷回来了!轿子已经到大门口了!”当这铺天盖地的喜讯一层层传进咱家大院的时候,咱家混沌得哭丧一样的空气难得地高速流动起来,把这特大的喜讯传递到咱家大院的每个边边角角,连只会穿墙打洞的耗子们都乐呵呵地高声传唱着,“吱吱吱,老爷终于回来了!”
每个人都喜相相的。包括在咱面前恶声半气的咱娘,也急三火四地吩咐蔡嬷嬷给她梳洗打扮,这儿插朵妖冶的玫瑰花,那儿戴上叮叮翠的绿耳环,还要戴上黄灿灿的金手镯。娘啊娘,你也不看看你都啥岁数了,还玩这些小女家家才玩的小游戏,值得吗?瞧瞧你的嘴唇涂得红的,真叫血淋淋的,不知道的人看了,还以为你刚刚生吞活剥了一只带毛的野猪呢。
可惜,咱娘还不满意。那就为了一个小小盘扎头发的簪子,咱娘差点儿就把咱家给掉个个儿翻过来了,这个不行,太俗气,那个太妖艳,那那个太老扎了:“明天赶紧吩咐匠人打几把簪子去,出门连个合适的都没有!”
直到大门的喜信传来:“老爷往二门来了!”二门的看守来报:“老爷过二门了,离三门不远了!”咱娘这才惊慌失措起来,连二赶三地吩咐起来,“快快快!随便哪个给我插一个就行!”蔡嬷嬷一身一身的冷汗,都把老眼给迷花了吧,直接就搁乱蓬蓬的簪子堆里摸捡了一个,手忙脚乱地给咱娘戴上。
哪是什么呀?看见的人都偷偷地捂着嘴儿傻笑,蔡嬷嬷呀,你果真老眼花花了吗?恁么多金的银的黄的白的你不带,偏偏捡了一只碧绿的蛤蟆簪儿戴在咱娘的发髻边缘。嘛意思,还嫌咱爹给咱娘戴的绿帽子不够多而丰富吗,还要咱娘自己向周围的人们广而告之吗?
不过,咱娘压根儿就没有看见,还那么小姑娘似的乐呵呵就迎接咱爹了。咱爹大约看见了,看见了的咱爹大约连眉头都不要皱,皱什么,直接向咱娘坦白:“真对不住,我又让你戴绿帽子了!”
“累了吗?到房里我给你按摩按摩!”咱娘年轻得活像一只叽叽喳喳的小麻雀,贴心地给咱爹掸去并不存在的浮土,还替咱爹捋捋并不零乱的外衣小衬边。回头看见亦步亦趋跟着的蔡嬷嬷,立马张牙舞爪地吩咐,“没有一点儿眼力见儿,还不赶紧快去打些洗脸水来,我要给老爷洗洗!老爷鞍马劳顿的,可辛苦了!”
可是,热闹是他们的,与咱有半文钱的关系吗?咱懒洋洋地躺在咱的小窝里,连下床看看热闹的心思都没有,看什么看,再看就能够帮咱把肚皮糊弄得满满当当吗?不要站着说话不腰疼,饱姑娘不知饿姑娘饥啊,你不晓得,咱的肚皮叫的那叫一个欢,咱恨不能把眼前不多的几件旧衣撕成条条缕缕,一口气都给吞下肚中才好。
咱尝试踌躇了无数次,也没有胆量将这梦想变成现实。不是咱怕把咱的衣服给生吞完了,咱再出门的时候,衣不蔽体地惹人笑话,实在是那旧衣的滋味真的无法下咽啊!又干又涩,还牵牵连连的,咱的小手咋也扯不断。就是不晓得新衣的滋味如何,是不是滑溜到咱勉强能够咽下去的地步呢?
可惜,这品尝新衣的机会大约真的没有了,咱的多到数不清的绸裙布裙,长裙短裙,睡裙正裙,一律被咱娘贡献给咱的那些历来总不相能的姊妹了。剩下的就是这几件仅够咱临时换洗的旧衣了,咱再浪费了,出门真要咱光着身子不成。
怎么办?管他咱爹咱娘的,有后娘必定因为咱那个爹和咱的后娘差不多就是一丘之貉了,要是咱爹不同意,咱娘敢这样拿着鸡毛当令箭骑在咱头上作威作福吗?咱还是老老实实躺在这儿不动吧,直到咱狼心狗肺的娘能够回心转意,能够施舍咱些吃的东西,就是掉在地上无人问津的垃圾食物,或者直接给咱端些鸡们狗们吃的东西给咱也行。到这个时候,咱再想着吃香的喝辣的,那不找死吗。况且,也没有人肯给咱色香味俱全的上等食物啊。
饥饿,疲倦,也行还有难掩的伤感吧,咱又一次昏睡了过去。弥留之际,咱还自己给自己安慰:“睡就睡吧,也许咱就此见了阎大王,咱好好求求阎大王,早早把咱收归地府去,喝过迷魂汤,不上望乡台,直接就给咱托生为大户人家的猫猫狗狗也行,也强似在这人情冷漠的阳世接受咱娘的虐杀!”
“哈里,哈里!快来呀!巴巴给你带黄河鲤鱼回来了!”朦朦胧胧中,谁在叫喊咱娘的那只机灵鬼灵的猫咪。哇呀,黄河鲤鱼呢,千年难得一见的鲜物啊。咱这个地方,山多水少的,不要说黄河鲤鱼,就是司空见惯的鲫鱼也不常见啊。
来的自然是咱那个亲亲的咱爹了——咱不晓得是应该还叫他一声亲亲的爹呢,还是和咱娘一样,直接由娘亲过度成狼心狗肺的后娘啊?毕竟,咱的待遇悬殊太大了!
唉!早知道做个富人家的猫咪都这样光鲜,咱为什么要费尽千辛万苦挤到人间做这个短命的大家小姐呃?哎哟,上帝老爷爷啊,你行行好赶紧把我带走吧,我要赶紧投胎做猫咪,虽然一辈子不能言不能语,至少好吃好喝的离不了咱。还不用学什么针织女工,还不要学着煲汤蒸煮炖炸,自然就有香的辣的供咱大快朵颐。
“猫咪没有在家,它,它,它前几天跟着管家出远门,到咱妹家走亲戚去了!”咱娘惊慌失措地想要阻拦住咱爹,可你那理由实在站不住脚后跟,差不多荒唐得很啊,一只猫咪离家出走,还跟着管家出了远门,你这叫哪门子理由?管家不就跟着咱爹才回来吗,啥时候咱爹这个主家不当家,放任管家替他当家作主呢?
“哼!”咱爹果然是个明白人——顺着以前的旧规,咱暂且叫你一声爹吧。咱爹从鼻孔里恶狠狠冒出一口冷气,脚步巴巴着就往咱的蜗居地方赶来。
咱爹的劲头多大啊,单薄的小门只微微动了一动,也就吱吱呀呀打开了。还咣啷一声重重地磕在墙上,又慢悠悠反弹过来,咱爹也就顺手抵住了。
咱本来不想抬头,咱的头绵软得差不多赶上久晒无雨水滋润的稀软菜秧了。可是,木门的特别响动还是惹得咱匆匆忙忙抬头,正看见咱爹探照灯一样四处探寻的目光,咱爹好是一愣,先是下意识地问了一句:“猫咪呢?”想想大约不对,又立刻补充说,“你怎么住在这儿,谁让你搬到这儿的?”
咱爹的前一句只把咱的心坠落在十八层地狱以下——爹啊,亏得你是咱的亲爹,在你的眼里,我连那只不知所踪的猫咪都不如吗?后一句多少把咱提升到第八层地狱,可咱的心依旧哇凉哇凉的:“爹呀,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咱娘敢把咱这个半个月前还高高在上的小姐一脚踏翻在地,还塞到这个猫咪的巢穴里,仨瓜俩枣地就要贱卖了咱。你真的一点儿消息都没有吗?”
不等咱的腹语编排到底,咱爹的雷霆之怒就喷发了:“来人呢,赶快把九小姐搀扶出来!这还了得,我的闺女不经我同意,咋就给塞在狗窝了。这事儿要我查出谁是幕后主使,小心我扒了他的黄鼠狼皮儿!了得了,这个家还有没有王法了!”
得了咱爹的命令,早有一杆子过去依着咱娘的丫鬟仆妇手忙脚乱地过来抢救咱,可比拿我进狗窝的时候殷勤多了。一边给咱简单收拢头发,一边给咱赔罪:“九小姐,你受苦了!都怪奴才眼拙,你大人不记小人过,抬抬手饶过我们吧。”
我不理会她们的自作多情——要是你们早两天这样识得货色,咱何至于现在连瘦削的脑壳都举不起呢。罢了,罢了,咱这个立足未稳的小姐还是不要摆这没有用的官架子了。哪天爹再出门的时候,咱娘还不把我给丢在猪圈里和哼哼们一起过活吗?
“呀!你们的狗眼瞎了吗?怎么给小姐穿这样破旧的衣服,你们这是打发要饭吃的吗?还不快去给小姐找新衣服出来!”看着咱朴素得比下人更朴素的装扮,咱爹的火气差不多可以直冲上云霄了。
可是,刚才那帮积极得什么的丫鬟仆妇们没有一个人动身,只有一个胆大的大约新来的丫鬟轻轻接了句:“小姐的房里没有衣服,就这几件旧的!”
“啥呀?”咱爹的嗓音真的掉高了八度,“怎么会没有衣服,我给九小姐买的那么多新衣服都去了哪儿?难道它们会自己个儿带翅膀飞了不成?去,赶紧找,一定要最新最新潮的裙子!”
啊呀,爹啊,你还是咱的亲爹啊!刚刚咱的小肚鸡肠,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大不了以后,咱康复起来以后,咱亲自给你钩个手套,就当赔罪了吧。
兴奋、饥饿、激动、伤心、难过……咱又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