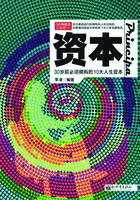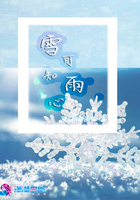春天的一个午后,樱花正开得灿烂。葛怡在夕光里站着,晚风吹着头发,她的声音与洁白的花瓣一起,悠悠地向杨略飘来,一时让他觉得心里有清泉荡涤,脸上漾出微笑的影子。
“我看过一个动画片,女孩和男孩心心相印。男孩喜欢小提琴,要去意大利进修,几年后再回来。女孩愿意等他,却觉得自己没有理想,配不上他,就用了一个月时间,写了一篇故事。故事写完了,她却哭了,知道自己欠缺很多,于是重新回到学校。”
葛怡的眼睛里,闪烁着高天的云彩。她在想动画片里的场景。男孩问:“我们永远在一起,好吗?”女孩抬头,认真地说:“嗯,我觉得这样很好。”目光明亮,背景是矢车菊一样的蓝天。但葛怡没有说出来。
杨略拾了一枚花瓣,洁白中渗出点粉红,娇嫩如葛怡的肤色。但不小心,就有了一道折痕,过不多时,折痕变成棕色,像是残忍的刀疤,让他触目惊心。
美,也这么脆弱吗?他现在越来越恐惧于时间了。
当然,时间也有个好处。车祸一晃儿已是几个月前的事情了,他的腿伤渐渐痊愈,恢复得很好,回到了学校,打篮球踢足球也全无妨碍。但那个关于人生的问题,却并没有随之消失,随着父亲的启发,反倒越发具体了。
饭后在校园里散步时,听着葛怡讲的故事,他内心在想:人生目标需要在实践中寻找,那么,我该实践什么?葛怡是在暗示这个吧?他问道:
“你是不是觉得,我也该试一试?”
“是的。”
葛怡回头看着他,心里却想着:对他的所长,我倒能看得清;可对自己呢,依然是一片茫然。
在她自叹的时候,杨略心里也在翻腾:总说喜欢写作,但我到底写过什么呢?细细检查,除了几篇朝生暮死的豆腐干,似乎也并没有突出的成绩。我不会也和大头一样,也只是夜郎自大呢?但他决意要尝试一下,写部好作品了。
“可是,写什么呢?”
没有答案。天色渐渐黑下去,他们回到了教室,依然是晚自修,依然是熄灯,依然是晨练,日复一日,夜复一夜,时光悠悠地过去。但杨略心里一直存着疑问。写什么呢?自然是身边的故事,他受安妮宝贝或郭敬明的影响,也想写点青春情感小说,但起了个头,就觉得言语粘腻,情节做作,要不就是吸尘器一般,把身边什么七零八碎的事情都堆进去,写了几天就坏了胃口,再也持续不下去。
怕是功力不够吧,那么,看看人家成功的作品,恐怕会有些启示。于是不断翻阅各类小说,名著也读,畅销书也看,希望能有一线灵感。这一天,他在教室里翻阅《苏菲的世界》,脑中忽然灵光一闪。
“我不是也和苏菲一样,收到过神秘来信吗?”
那是初二暑假时,他每日无所事事。一天收到一封神秘来信,谈及理想追求,让他内心深为震动,决定奋发向上。其后神秘来信每月必至,一共十封,全面谈了如何做人。他言听计从,潜心修练,渐渐成了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最后才知道,信是他父亲写的。当时,他是那么感动。
“要是把读信的过程也写下来,加上信件的内容,既真实有趣,又有内涵深度,不是很好的创意吗?”
他脑中一片空明,欢喜得跳起来,立刻拿出纸笔,顿感文思如潮,几乎文不带点,一会儿的功夫,已经把小说的提纲列好,心中无比兴奋,嘴角洋溢着笑容。马斯洛说的高峰体验,是不是这样的呢?
趁着课间时光,他拍了拍葛怡的肩膀,将笔记本递过去。
“你看看这个。”
“什么……呀,小说提纲,你真的要动笔了?”
杨略陶醉于她的惊喜,整张脸都放出光芒来。
“不错,我找到切入点了。这次准能成。嘿嘿,我要把你,还有大头猴哥他们全写进去……”
他觉得天朗气清,思路开阔,几乎看到了小说写成之后的喜悦与满足。于是趁热打铁,教室里不能用电脑,就买了稿纸,立即着手去写,每天抽空写上一段。写作说来简单,付诸实践却是五味俱全。有春风得意、下笔如飞的畅快,也不免有苦思冥想、搜刮枯肠的困顿。但他乐在其中,不仅占用了所有的休息时间,甚至连上课时,他也沉醉在故事情节里。
长话短说,到了夏天再次到来时,杨略历尽艰难,删删改改,渐渐完成了近十万字,又将信件加以润色,加上一些趣味测试,共有十五余万字,俨然一部结构奇异的小说了。
这一天,正是星期六,距离期末考试不到半个月,杨略写完了小说的最后一个字。这是一个神圣的时刻啊,他心里突突地跳。将钢笔仔细地套上笔帽,看着眼前摞着的一大叠稿纸,一时思绪万千,眼睛有些湿润。但他原先想到的豪情万丈,大声高呼,却没有发生。
午后,阳光灿烂,但还不太热,白色的窗帘在微风中轻轻飘摆。小区很安静,只有蝉声悠扬。杨略将书稿叠得整齐,开始从第一页往下看,完全融入了故事中去,沉到往事里去,浑然不觉时间流淌。一个下午过去了,他通读了一遍,又抽出一张白纸,覆在首页,郑重地写上了书名,《你在为谁读书》。这是车祸后心里的疑惑,也是书里力求回答的问题。
然后疲惫与满足一起席卷而来,他站起身,抱着双臂,靠着窗框上,看着窗外的枫杨树,回忆写作的日日夜夜,忽然有种怅惘的感觉,就像葛怡故事的少女一样,自己也远未成熟吧。情节如何安排,对话怎样才生动,都让他捉襟见肘,更不用说思想的单薄,知识的贫乏。这些都要向文学大师们好好学习的。
正想着,手机响了,是葛怡。
“正要找你呢。”他心里想着,旋起一阵欢愉,接起了电话,不由分说,先公布了这件大事。
“……有十五万字呢。”
“哇,太了不起了,得让我拜读一下。”
“没问题,看看我把你美化成什么样子了。
“还真有我啊?”
脆脆的嗓音,让杨略觉得甜蜜,声音愈发柔和了。
“当然有你啦。等书出版了,你也跟着红了。”
那边传来可爱的笑声。
“你终于实践了自己的理想……”
葛怡没有说下去,声音却渗出几丝忧郁。杨略能明白她的心思,就岔开了话题。
“对了,你找我有事?”
“欧阳老师让我通知,说下星期得填个志愿表,明确日后文理分班的事情。”
来得这么快。
“你准备读什么?”
“我正发愁呢。以前就和你说过,我就是什么科目都挺好,但全不冒尖,迟早会出问题,以后我总不能什么专业都念吧。这不,现在应验了。我都希望自己偏科了,越偏越好,一条道走到黑,倒省心了。唉,说什么也晚了,看来又只能听父母摆布了。”
杨略皱了眉头,用手指去捏仙人球上的刺。
“他们怎么说呢?”
“能怎么说啊,当然还是那一套。什么理科生考大学专业选择面大,就业也容易一些。不过读文科的话,大学可以读英语,以后搞外贸,很挣钱。另外呢,考公务员也有优势。唉,反正他们早就给我安排后事了,也没考虑我的感受。”
后事?杨略不由笑出声来。
杨略知道,葛怡的爸爸在市政府里做事,是个处长,官运亨通,据说要升局长了。妈妈是银行经理,大小也算个领导,又管贷款,是个财神奶奶。葛怡说过,她还很小的时候,父母就仗着自己的价值观,开始考虑她以后上什么学校,做什么工作,一切安排得妥妥当当,就差给她选墓地了,偏偏忽略了她的意愿。
“你还笑?”
“我没笑你,我是觉得,要是人生不能自己掌控,一切都听凭别人安排,那多没劲啊。”
“唉,可我想掌控,也得自己有个主见啊。我现在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走。”
“这也是……你别着急,我爸不是正在研究这个吗?说不定他会有好的建议。今天他不在家,过几天就回来。到时候我再问问吧。”
“行。那说说你自己吧,文科还是理科?
“我当然是文科啦。”
“是啊,你一直都挺确定。”葛怡似乎又叹了一声,杨略听得分明。“我现在都不知怎么办好了。”
杨略也想不出什么话来安慰。如果不能给出切实有效的建议,任何安慰都是苍白无力的。
周一杨略起了个大早,到了学校,早读课还没开始,班上同学都在海阔天空地聊天,周末去哪旅游了,看了什么电视,玩了什么游戏,不一而足,似乎全不把选文理科当回事。
杨略碰了碰同桌曾泉的手臂。这家伙生了一张大嘴,正笑得面目狰狞,牙床都露出来了,脸上的肉往上推,把眼睛都挤没了,只剩下一条细缝。
“大嘴,怎么样?选好了?”
曾泉似乎对他的打扰很是不满,皱着眉毛说:“还选什么呀,肯定理科!你没听说吗?人家都是理科学不好的才去学文科!多没出息!当然啦,嘿嘿,某些比较怜香惜玉的秀才,恐怕也会选文科的吧?”眉头往上一耸,冲着杨略诡异地笑。
旁边几个同学会意,都对着杨略嘻嘻奸笑。
杨略一阵脸红,口中说道:“假正经。就你小子,看到美女就失魂落魄,现在倒清心寡欲了?口是心非!嘴巴这么说,心里不知道多想进文科班呢。”摇头晃脑地念道:“到那时节,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曾泉故作老成地摇头,大声叹气:“唉,到底是小鬼头啊,真不懂事。还‘看尽长安花’呢。你要是个穷酸秀才,没钱没势,估计人家是倾国倾城貌,你是多愁多病身,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还落得个‘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你呀,得相思病去吧。”
这二人都竞赛式地背过许多诗文,也背经典电影台词,什么周星驰冯小刚,哪段精彩背哪段。平常交流时,老掉出些典故,走火入魔一般,并以此自娱,虽然常被别人说成神经病,但到底消减了学习的枯燥劳累。如今一年过去,彼此都练得纯熟,一旦开战,就和说相声一般,张口就来,滔滔不绝。二人关系也极好。
不过今天杨略是不客气了。
“大嘴,我怎么一直没发现,你这个人原来这么俗啊?!”
“哈哈,俗?行,我承认,我俗。可女人更俗!”
“你可别一杆子打倒一船人。”葛怡清纯脱俗的身姿在脑中一晃,杨略顿感底气十足。
“你还别不信。听爷爷给你讲讲这个道理。看《动物世界》了吧,一只雌鸟,肯定会选有巢的雄鸟,因为要产卵啊。这女人呢,也一样,特别物质。想想也正常,她得生孩子吧,生孩子得有个窝吧,得有钱买吃的吧。所以啊,现在男人登报纸征婚,肯定写清楚有房有车。一个道理嘛!”
“哼,你说的这种女人,只能说是雌人,母人!”
“好好好,你高雅,你风花雪月,你不食人间烟火,行了吧?可你老婆孩子呢?也跟着你喝东北风,饿着肚子看月亮?你啊,OUT啦!”
“这哪儿跟哪儿啊?和文理分科有什么关系?越说越乱。”杨略说着,心里已有些乱了阵脚。
“一点都不乱。现在什么时代?是理工科的时代。人活一世,不就图个享受嘛。怎么才能享受呢,升官发财呗。要升官,得读理科,你想啊,中央领导里,大部分理工科毕业。要发财呢,眼下什么行业最挣钱?IT业!还是理科。所以说,等咱读了理科,以后升官发财,直升飞机买两架,一架挂着另一架。美女们……”舌头往里一缩,响起咝溜咝溜的吞口水声,“还不乖乖投怀送抱?”
忽然翘了个兰花指,左边嘴角一挑,细声细气说:
“我这叫放长线,钓大鱼,用发展眼光看问题。现在这些漂亮眉眉,就让你们这些酸秀才们先过过眼瘾,啊,好生伺候着,”一拍胸膛,“以后等哥们来迎娶。”又大笑起来,声音尖锐,像金属片刮过玻璃。
曾泉特别喜欢历史,自从得知了当红作家当年明月的事迹,也着实下了功夫,把《二十六史》借来,下课时翻着字典,一页页地啃下去。中外历史了解得不少,说话满嘴的刘邦曹操亚历山大,像程咬金的三板斧,刷刷刷,且不说真实水平如何,先就吓人一大跳。杨略以为他是铁定要读文科的,不料却有这么一套理论。
杨略冷笑道:“大嘴,我看你不该叫曾泉,得叫‘争权’。满脑子功利,没救了!”说罢转身就走,虽然以前二人也常拌嘴,可说话再尖酸刻薄,也总是开玩笑的,翻翻小浪花,从不动真格。今天不知为什么,他却有点当真了,心里着实有几分不快。
他走了一段路,看到葛怡正和几个女生说着话过来,便上前叫住。那几个女生互使了个眼色,知趣地走开,只剩下他们两人。葛怡穿了雪白短袖多褶长裙,只有边缘和腰带上有几处藏青花边,说不尽的清爽可人,让杨略心里亮堂堂的。
“你才来啊。”杨略语气居然有几分埋怨。
“怎么了?”葛怡有些奇怪。
“我都快被曾泉这小子气死了。”
葛怡莞尔一笑,说:“你们两个可是一个逗哏,一个捧哏,天生的相声搭档,哪天不是唇枪舌剑,兵来将挡的。他还能气倒你?”
杨略将适才争论的内容简略说了。葛怡噗嗤一声,说:“你啊,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这种谬论也值得生气?”
“我也知道是谬论,不过还真反驳不过来。”
葛怡双手背在身后,故作正经地说:“很简单啊。他的理论前提是,女人总是依附男人,所以希望男人有钱有势,封妻荫子。可这个前提不正确呀,现在男女平等,女人也上大学,也工作,挣得不比男的少。经济地位一独立,当然可以想爱谁就爱谁,管他有没有钱,有没有地位。”
杨略豁然开朗,说:“对啊,这么简单的问题,我怎么就没想明白呢。”
其实想不明白也很正常,当局者迷啊。曾泉说得无意,他却听得有心,而且硬往自己身上套,觉得日后若是从事写作,肯定不会富裕,葛怡会不会弃他不顾,仗着花容月貌,另投豪门贵族而去呢?这么一想,心里发了慌,哪里还能明辨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