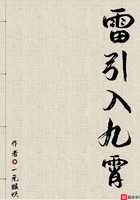教师应当如何授课
当儿童准备好进行感官训练时,应当对其单独授课。教师要小心翼翼地接近她认为准备好学习该课程的孩子——她坐在孩子身旁,挑出一个她认为能够引发孩子兴趣的物品。
这一步也揭示了教师自身的准备是否充分。她应当接受过如何做实验的简单培训。她期待从孩子那里得到的回答是,孩子的内在兴趣会转向使用教师递给他的工具。
这节课叫作唤起注意。如果物品迎合了孩子的内在需求,而且能让其从中得到满足,就会激励孩子延长活动的时间——他们会不厌其烦地操作、使用这个物品。
授课的第一要点是少说多做。讲解不一定非得用语言。通常教师要做的,就是给孩子展示如何使用物品。如果教师必须通过语言向孩子们示范如何运用促进其成长和发展的工具时,讲解也应当简洁。最好的讲解就是用最少的话把任务讲清楚。
话语越少,授课的效果越好。备课时,应当格外留心挑选课上要使用的词语。
授课的第二个要点是简洁。除了绝对真理之外,无须任何其他附加的东西。虽然避免空洞的辞藻已经蕴含在授课的第一要点之中,第二要点中也要涵盖这一点。计数的词语应当是最简单的那种,只表述事实,毫无矫饰。
授课的第三个要点是客观。这就意味着教师得忘却自我,将孩子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到物体上去。多数情况下,短暂而简洁的课程应当包含对物体及其用途的解释。
教师必须观察孩子是否对该物体感兴趣、如何表现自己的兴趣、保持兴趣的时间有多长等。教师不能强迫孩子对她提供的物品感兴趣。如果教师准备的课程短暂、简洁,但孩子仍无法理解教师对该物体的解释时,教师就应当注意两点:首先,她不应当坚持重复授课;第二,她应当避免让孩子知道自己犯了错误,或是没能理解,因为这可能会长期影响儿童的行动意愿,而这正是儿童获得全面进步的基础所在。
举个例子。设想一位教师想给孩子展示红色和蓝色之间的区别。为了引起孩子对物体的关注,她说:“看着,注意了!”如果她想教孩子颜色名称,她就给他们看红色物体,说道:“这是红色。”在说“红色”时,她应该提高音量、放慢语速。然后,她再给孩子展示蓝色,并说道:“这是蓝色。”
为了确认孩子是否听懂了,她说:“给我红色。”或者说:“给我蓝色。”假设孩子犯了错误,教师既不要重复课程,也不要继续坚持,而是要微笑着把色块收起来。
普通教师通常惊讶于这种简洁。他们常说:“任何人都能做到。”然而,我们再次遭遇到跟“哥伦布竖鸡蛋”类似的故事。事实是,这些教师压根儿不会。在实践中,评估一个人的行为是极其困难的,对于接受旧式方法培训的教师而言就更加困难。他们会用大量无用的词语和误导来压垮孩子。
我们借用上述例子来说明。一个普通教师在给一群孩子讲授颜色时,会过分强调这个简单任务的重要性,并迫使所有孩子都听她讲课——或许不是所有人都那么偏执。她很可能这样开始上课:“孩子们,你们能猜到我手上有什么吗?”她非常清楚孩子们猜不到,因而用了一种错误的方式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然后她很可能会说:“孩子们,你们有没有抬头看过天空?你们看到过吗?你们有没有看过夜晚繁星闪烁的天空?没有吗?看看我的围裙吧。你们知道这是什么颜色吗?看看是不是跟天空一样的颜色呢?
那么,现在看看我手里拿的东西的颜色吧。它是跟天空和围裙一样的颜色。
这是蓝色。看看你们周围,见到别的蓝色的东西了吗?你们认识樱桃的颜色吗?灼热的煤块的颜色呢?”诸如此类。
这样,儿童在被提问弄得头昏脑涨之后,又被无数的概念压得喘不过气来——天空、围裙、樱桃等。在这片混乱中,他们发现难以识别物体。
课程的目标是识别两种颜色——蓝色和红色,可是孩子的头脑无法做出选择,尤其是他们无法跟上教师那冗长的讲述。
我记得有次听到一节数学课,老师在教孩子2加3等于5。为此,她用了一个跳棋盘,小球可以放在相应的孔里。木板的最高层可以放2个球,3个球放在下一层,最下面放5个球。我不太记得这节课的具体情形了,但是我记得,老师非得在最上面2个球的旁边放上一个跳舞的纸娃娃。这个娃娃穿着一条蓝裙子,班里时不时有个孩子会说起它的名字:“她叫玛丽蒂娜(Mariettina)。”然后,在下一层的3个球的旁边放着另一个打扮不同的跳舞的小人,名字叫“吉基诺(Gigino)”。我不太记得教师是如何得出总数的,但她无疑花了很长时间跟那些舞人聊天、挪动她们。如果连我都对这两个小人记得比运算过程还要清楚,那么孩子脑子里留下的又该是什么样的印象?通过这种方法他们不但没有学会3加2等于5,还付出了巨大的脑力。
在另一堂课上,一位老师想阐释噪音与乐音之间的区别。她从给孩子们讲一个很长的故事开始。突然,跟她共事的一个人开始大声地敲门。她打断了故事,喊道:“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干吗呢?究竟是怎么回事,孩子们?我的思路被打断了,不能继续讲故事了,我什么也不记得了,必须放弃。你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听到了吗?明白吗?是噪音!这就是噪音!我宁可抱抱这个婴儿。(她拿起一个裹在毯子里的曼陀林。)乖宝宝,我宁愿跟你玩。你们看到他没?你们看到我怀里抱着的这个婴儿了吗?”
有一个孩子大声叫道:“那不是孩子!”其他人也跟着叫起来:“那是个曼陀林。”老师回答道:“不对,不对,这是个孩子,真的孩子。你们要我证明吗?嘘,安静点儿!在我看来,他正在掉眼泪,就要大哭了。或许他是在叫‘爸爸’或‘妈妈’呢?”她摸到了毯子下曼陀林的弦,“你们听到了吗?
你们听到他的声音了吗?是在小声哭还是在大哭大喊呢?”有些孩子说道:
“那是曼陀林。你碰到它的弦了。”教师回答道,“安静点,仔细听我在做什么。”她揭开了曼陀林,轻轻地拨弄琴弦,“这就是乐音!”
无法想象这样一节课最终能让孩子领悟多少教师的意图——展示噪音和乐音的区别。孩子会以为老师想开玩笑,而且会觉得她相当笨,一点噪音就打断了思路,还把曼陀林跟孩子弄混了。这样,教师的形象会深深根植于儿童的脑海中,但课程的目标却不会,背离了教师最初想达到的目标。
很难找到一个按照常规方法备课的教师能上好一节简单的课。我记得有一次,我对一位要用几何插件教孩子们区别正方形和三角形的老师说,她所要做的,就是把木质的正方形和三角形放进框架上相应的空白处,让孩子用手指沿着几何插件和空白框架的轮廓临摹,并且说:“这是正方形,这是三角形。”但在课堂上,教师在让孩子们触摸插件的边缘时说道:“这是一条边,这是另一条边,这是第三条边,这是第四条边。一共有四条边。
现在用你们的手指数数一共有几条边。还有角,数数有几个角。用手指摸摸它们,按一按。一共也有四个角。仔细看看,这是个正方形!”我在课后纠正了这位老师,指出她没有教孩子如何辨识形状,而是在教给他们关于面积、角和数目的概念,这与她应当教授的内容大不相同。但她为自己辩护说:“那是一回事。”但这可不是一回事,她是在对物体进行几何分析和数学分析,而不是区别形状。一个不会数到四的人应当也能学会正方形的概念,即无须学会边和角的数目。边和角都是不能独立存在的抽象概念。
一个木块中真正存在的是一个具体的形状。教师的解释不仅令孩子的头脑混乱,而且更严重的问题是,混淆了抽象概念和具体概念,即数学概念和物体形状的不同。
我对那位老师说,假设一个建筑师要给你展示一座漂亮的圆顶建筑,他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法介绍这幅图:第一种方法,他可以指出这个建筑的环境是多么美丽,各部分是多么和谐。随后,他带你爬到建筑顶端,并绕着圆屋顶转转,让你理解各部分的相对比例,以便你能见识和理解这个建筑的全貌。第二种方法,他可以数窗户的个数,告诉你这个建筑用的是宽檐口还是窄檐口,最后画一幅结构图来阐释稳固性定律,讲解用于计算其构造的几何形状。在第一种情形下,你将会了解圆屋顶的形状;第二种情形下,你什么也无法理解,也无法让圆屋顶在脑海中形成印象。后者会让你以为这个建筑师在跟工程师同伴讲话,而不是跟一个踏上愉快旅程的女士讲话。与此极为相似的情形是,我们不是跟孩子说“这是正方形”,而是让他们触摸正方形,让他们留意它的轮廓,接着,我们为他们做几何分析。传统观念认为这时教孩子平面几何形状太早了,是因为我们塞给他们的是平面几何与数学概念的混合物。但是,对孩子来说,将其区分开来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事实上,我们毫不费力,就能见到正方形的窗户和桌子。儿童的眼睛已经熟悉了周围的各种形状。为了将儿童的注意力引导到某个特定的形状上,就必须让它清晰地突出出来,以便在其脑海中留下印象。正如我们站在湖边,没太注意岸边,突然一位艺术家出现了,惊呼道:
“在峭壁倒影的衬托下,湖岸的曲线多美啊!”于是,原本无趣的景色突然在我们的脑海里鲜活了起来,就像一道阳光照耀下来。我们体验到了一种纯粹的快乐,之前的那种不完美感荡然无存。
这就是我们的使命:投射出一道光束,并传递下去。
最初的授课效果可以跟孤独的徒步旅行者的体验相提并论。当他快乐而平静地沿着林荫小道行走,他的思绪自由地在安静的冥想中漫步。突然,教堂的钟声唤醒了他。然后他更加强烈地感受到了平静。这种平静原本早已占据他的心灵,只是他从前并未意识到而已。
可见,教育者的首要职责是:激活生命,但容许其自由发展。
然而,要想完成这样一个艰巨的使命,需要伟大的艺术。它需要教师能选择合适的时机以及干预的程度。这会有效阻止教师干扰或误导学生,取而代之的是帮助一颗心灵觉醒,使其靠自身努力获得的美的生活。
这种艺术必须与科学方法相结合,因为我们那简单明了的课程与实验心理学的实验极为相似。
教师一旦开始依次触及每个学生的心灵,就像是用了魔杖一般唤醒他们,让他们苏醒过来,她就将拥有这些心灵。她不需要长篇大论,只需要打一个手势、说一个词语就已足够,因为学生们都关注着她,倾听着她。
总有一天,教师会无比惊讶地发现,所有儿童都像温顺的小羊羔一样听她的话。他们不仅会立即对她的每个暗示做出回应,甚至会等待她的暗示。他们会将她视作带给他们生命的人,他们本能地期待从她那里获得越来越多的知识。
经验已经向我们表明这一切。这种集体纪律,几乎是神奇般地实现的,它是“儿童之家”的来访者最为惊叹的奇迹。五六十个孩子,从2岁半到6岁不等。当他们集中在一起时,只要教师打一个手势,就会变得无比安静,安静得如同无人之境。如果一个老师低声向孩子们发出温和的指令:“起立,踮起脚尖走一分钟,再安静地回到你们的座位上。”所有人就会像一个人似的,整齐划一地站起来,尽量不发出声响地执行这些动作。老师跟每个孩子都谈过话,每个人都希望从她的教导中接收到一些微弱的光亮和由衷的喜悦,继续像有了路线的热切的探索者一般,专心又听话。
如果想要乐队集体努力实现和谐一致,音乐会的指挥者就必须逐个训练演奏者,而每一位演奏者也都必须进行自我改进,直到能够正确地遵从指挥者那无声的指挥为止。与之相反,在公立学校,我们总是让一个教授枯燥无味且不和谐的旋律的人来指挥差别很大的“乐器”和“声音”。
同样的事情也在社会中发生:最遵守纪律的人也是那些最完美的人,他们的行为不会偏激、粗鲁、专横。
对儿童心理学,我们始终抱有成见,不够客观。直到现在,我们仍然想用外在的标准来要求儿童,而不是把他们视作“人”,引导他们的内心,从而征服他们。这就是他们从我们身边擦身而过,可我们却不能理解他们的原因。
如果我们把那些试图诱捕他们的花招、训练纪律时的暴力都放到一边去,他们会向我们展示出自己的另一面:他们的温柔那么甜美、纯粹,对知识的热爱鼓舞着他们去克服困难——那些我们以为会阻止他们去努力的困难。
训练差异性、同一性、渐进性
这个过程应当从对比鲜明的少量刺激开始,以便稍后儿童能过渡到大量制作更精良、差别更加细微的物体上。例如,辨识触觉差异时应当从两个极端的平面开始:一个十分光滑,另一个极为粗糙。而在涉及辨别不同物体的重量时,首先应当把这一系列工具中最轻的木块给孩子,然后再给他最重的。辨别声音的大小也可以用如此方法。
在一套逐级变化的物体中,要先拿出处于两个极端的物体。当教孩子们辨别颜色时,颜色最鲜亮、对比最强烈的颜色是首选。例如红色和黄色。
至于辨别形状,圆形和三角形是首选,以此类推。
为了提供更完整的物体差异的概念,把相同的物体放在那些对比鲜明的物体中也是不错的方法。例如,有两套打乱顺序混在一起的乐铃,其中两个声音一样大,两个颜色一模一样。在特征相反的工具中寻找相同的工具,通过不断提示其特征而使二者之间的区别更加显着。
最后一个练习是给工具分等级,就是按照递进的顺序摆放一套被随机打乱顺序的相似物体。例如,一套颜色相同、大小不同的立方体,其大小是按照既定的尺寸增加的,例如边长依次增加1.27厘米。与此类似的是,展示一套黄色物体,颜色从明黄逐渐过渡到暗黄,或是一套长方形,其中一组对边长度不变,另一组对边长度依次递增。这类物体必须根据逐级变化的顺序依次摆放在恰当的位置。
如何开始触觉练习
虽然管理触觉的神经末梢遍及整个体表,但给予儿童的触觉练习却仅限于指端,尤其是右手的手指指端。
虽然实际情况导致了这个必要的限制,但它也有一个有益的教育功能,即能让儿童为日常生活做准备。因为手指是儿童触摸物体时最常用到的器官。
在蒙台梭利教育法中,触觉练习格外有用。正如我们所见,儿童用双手做的各种触觉练习让他们间接地为写字做好了准备。
所以我让孩子们用肥皂在脸盆里洗手,然后将双手放到旁边一个装有温水的水盆中冲洗。接下来,我让孩子擦干双手,再轻轻地搓手。这样准备工作便完成了。然后,我就会教孩子怎样触摸,即教他们触摸物体表面的方法。触摸时,教师有必要握着孩子的手指,引导它们轻轻地拂过物体表面。触摸技巧的另一个细节就是让孩子在触摸东西时闭上双眼。这样,他们就能更好地感受到物体表面的差异。孩子们学得很快,便会立刻表现出对这个过程的喜爱。没错,在做完这些练习后,当我们走进“儿童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