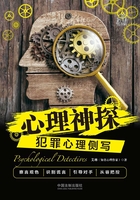具有恋父情结的女孩子,心地一般都比较柔软,即使外在上可能具有高学历、高收入,在社会上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但在内心中,她永远是一个需要被宠爱的小女孩。同样,具有恋母情结的男孩子也有类似情况。恋母的男孩一般没有主见,缺乏进取精神,有时甚至为了讨好母亲而抑制自己的主张。在婆媳关系上,恋母的男性无法忍受妻子说母亲的坏话,常常因此和妻子怄气,甚至导致夫妻关系的裂痕越来越大。
或许,世界上所有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固着的情结,或者是对父亲的,或者是对母亲的;或许是对完美的情结,或许是对成功的情结。
了解自己的情结是为了克服、摆脱它们,让自己能够幸福地生活。对于恋父或恋母的人来说,让自己变得独立、坚强起来是最好的方法。
不仅仅是经济上的独立,要让自己在精神上渐渐独立,将原本的单向依赖变为彼此依赖,互相关怀。
化妆舞会与面具——人格与伪装
心理学中的人格一词,来源于希腊语persona,它的原意指的是演员在舞台上戴的面具,就像京剧演出时演员画的脸谱一样。后来,这一词成为了心理学中的专业术语,表示人在不同社会场景中表现出来的人格。
可以说,一个面具就是一个人格的侧面,所有的面具,包括面具下面那个真实的自我,一起构成了人格的总和。因此说,人格没有真假之分,只有公开的人格和隐秘的人格。
在社会上的公开场合,人们需要和他人和睦相处,不能过分暴露自己的本性,因此就会戴上“亲和”、“有修养”这类面具。人们在追求理想时,不想让人看到内心软弱的一面,因此,就会戴上“积极向上”、“开朗乐观”这类面具。
这些面具会帮助人们实现个人目的,取得想要的成就。但是,如果一个人过分沉溺于扮演的角色,也可能因此陷入“面具膨胀”,让一部分特质占领了人格的全部。
在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中,作者塑造了一个内心充满矛盾冲突,为了飞黄腾达的目的戴着面具生活的人物形象——于连。于连生在一个平民家庭,他最崇拜的人物是拿破仑,可惜,在他出生的年代,拿破仑已经成了过去时。
为了能够像拿破仑一样出人头地,于连想尽一切办法进入上层社会,而达到目的的唯一方法就是穿上黑色教服,成为主教。为了迎合上流社会的标准,他不得不违背自己内心的想法,生活在一连串的矛盾当中。
于连根本不相信上帝的存在,却为了获得主教的位置而装出一副热忱、虔诚的模样;他将《圣经》中的话当作谎言,却又将《圣经》和《教皇论》的拉丁文版本倒背如流;他内心对拿破仑充满了热爱和敬仰,却因为害怕别人知道而烧毁了藏在床垫下的拿破仑画像……为了迎合上流社会的审美趣味,为了达到他改变命运的目的,于连隐藏起内心真正的声音,戴上了一层又一层的人格面具。
如果说,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庞大的化妆舞会,那么每个人都是戴着假面生活。作为向公众展示的一部分人格,假面就变成了社会情境下的自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面具具有欺骗性,甚至常常被人称作“虚伪”,然而,每个人都是在将真我隐藏起来之后才顺利地被群体和社会接纳的。若说虚伪,那么这个化妆舞会不是更大的虚伪吗?
相信,没有人愿意将对外呈现的人格面具定义为“虚伪”,也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是个虚伪的人,因为虚伪是个贬义词。试想一下,一个人真的能做到那么纯粹,一点都不虚伪吗?见到不喜欢,甚至讨厌的人,也要礼貌地问声好,这时候戴的是“修养”的面具;明明不喜欢做一件事,但是为了金钱或者奖赏,还在认真地做,这时候戴的是“积极”的面具;一个人内心很脆弱,害怕和人争论,委屈时想要躲起来大哭一场,却还是笑着对大家说“我没事”,这时候戴的是“坚强”的面具。
就像于连一样,这些面具都违背了自己的内心,却让人与人之间更融洽,社会秩序更稳定。曾奇峰曾经说过:“我不知道的是,有没有这样一种境界的人格,不需要任何防御,‘裸露’着就可以好好地活下去?”从文字中,可见大师的率真可爱,情怀别致。可是,这样的“裸露”的情怀是每个人都能够尝试的吗?
司汤达在《红与黑》中只让于连活了23年,算是英年早逝。短暂的生命中,作者却让他的23岁经历了人生的所有,他曾经有希望、有梦想,并且不择手段地为之奋斗,最后失败,死亡。
可以说,在于连的一生当中,他都戴着面具而活,为了不同的目的以假面示人。到了法庭上,他终于扯去了面具,卸掉了一切伪装,这时人们发现,原来这个手段卑鄙,内心肮脏的家伙是一个不甘平庸,勇于反抗贵族社会的平民英雄。此时的他面对着****的灵魂,发现了最真实的自我,也发现了生命中的真爱。
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的面具,也有很多于连这样戴着面具苦苦挣扎的人。实际上,人格面具本身是没有好坏之分的,就像人民币本身没有价值一样,重点在于戴着面具的人如何使用它。事实已经证明,“坚强”、“亲和”、“有教养”……这些面具能够让人们更顺利地适应社会生活,获得他人的接纳,既然如此,这些面具的存在又有何妨呢?
只有当一个人过分地沉迷于人格面具之中,沉迷于自己扮演的角色,才会发生可怕的悲剧。因为,一个人戴着面具,刻意扮演某种角色的人,容易在角色中迷失原本的自我,失去个性,从而变得茫然。
而且,沉湎于某种角色也会使得真实的自己与角色身份混淆,造成心理冲突。
人在社会中生活,面具是一种保护伞,就像动物的皮毛伪装、颜色伪装一样,可以帮助人们适应环境,保护内心的自我空间。当然,我们也要根据环境及时调整角色,以平常心来面对生活中的虚伪与不真实。这样的话,就能使心理处于一种平和的状态,我们的理想、目标、人生追求才更有希望。
究竟是谁的错——不靠谱的大多数
导演西德尼·吕美特在他的处女作《十二怒汉》中以一个陪审团为主角组织起了法庭上的辩论会。导演在探讨美国陪审团制度和法律正义的同时,也将群体中的“集体潜意识”融入其中,使其成为一部可供心理分析的作品。
针对一个18岁的少年是否杀死继父的案件,12个素不相识的人聚到了一起。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心事。
他们不懂法律,甚至不需要懂任何法律。他们只需要根据法庭上提供的证据,按照一般人的道德评判标准确定一个人有罪或者无罪。
经过冗长而复杂的庭审,法官请求对被告发布最后的裁决。从法庭提供的证据来看,少年一定是杀人凶手。居住在对面的妇女透过窗户看到了被告举起刀杀人;楼下的老人听到被告说,我要杀了你以及随后身体倒地的声音;令被害人致命的凶器和被告曾经买过的弹簧刀一模一样;被告的不在场证词含糊不清,因为他连电影的名字都说不出来。
表面看起来,这是一起板上钉钉的案件,判决被告有罪理所当然。
在法庭上浪费6天时间的陪审员已经厌恶法庭闷热的环境和没完没了的证据展示,他们希望尽快做出决定,然后回家看球赛,或者继续打理自己的生意。
11名陪审员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宣布了被告有罪。只有一位陪审员觉得尚有疑点,坚持提出反对。按照法律规定,陪审团的决定必须一致通过才能最终定罪,因此其余的11个人恨透了这个“搞事”的家伙。
在第12个人的坚持下,陪审团的成员重新分析了案件的疑点。
最后,案件中的五个疑点被一一确认。18岁的少年因为个子太矮,根本不可能“举起刀”从父亲的胸口刺下;由于火车经过时的噪音太大,跛脚的老伯也不可能听清楚“我要杀了你”这句话;跛脚老伯说他花了15秒时间从卧室穿过走廊,看到少年杀人后仓皇出逃,然而,正常人尚且需要41秒才能完成的距离,一个跛脚的老人根本不可能做到,因此他说了谎。至于少年忘记了电影的名字,完全是因为情绪太过紧张,导致大脑一片空白所致。任何人在情绪紧张的情况下,都有可能忘记事情,包括身边的小事。
经过7次表决之后,其他陪审员纷纷推翻了原本的决定,直到最后一名顽固坚持被告有罪的陪审员放弃了立场,少年被宣布无罪。
电影中,导演在每个平凡、普通甚至有些不负责任的陪审员身上发掘出了人性的高贵和正义的力量。可是,身处现实的人们必须看到,一群手握生杀大权的人是这么容易被操纵、被控制、被改变。如果案件本身反过来,少年实际上是无罪的,在大多数陪审员坚持被告无罪的情况下,只有一名陪审员坚持其有罪,并且用尽浑身解数说服了其他人,那么,这些不负责任的陪审员不是更加可怕了吗?
当然,我们要讨论的并不是陪审员与司法公正的问题,而是陪审团成员的“集体潜意识”。古斯塔夫·勒庞在他的着作《乌合之众》中提到,人与人之间的心理极易相互传染,形成一种“集体潜意识”。
正如那11位陪审员一样。只要群体中有人尽心引导,对代表反对意见的整体进行施压,就可能得到其预想的结果。古斯塔夫·勒庞说:“从集体心理上作用的影响,要比从外部对每一个个体施加压力,更容易影响人的判断。”
由此可见,当正义之剑掌握在大多数人手中时,并不见得一定好于少数人。在大多数人中,同样只有少数人的意见在起作用,其他人有的是打酱油的,有的只是保守地选择了人多的一方,有的干脆毫无考虑,选A或B只是个概率问题。因此才有那么多人经常提起一句话:民主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
在集体潜意识的影响下,人们最容易做出的决策就是从众。社会心理学家阿希曾经针对“从众”问题做过一个实验。实验的假设是当聪明的人看到事实时,他会遵从事情的真相,而不是依附他人的意见。
然而,实验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
阿希将被试分为7人一组,其中编号为7的被试是真的被试,其他人都是实验助手。实验开始后,被试与实验助手都坐在桌子旁,并且对实验者呈现的卡片进行判断。实验者会一次呈现两张卡片,其中一张是一条直线,作为标准线。另外一张画三条直线,其中一条和标准线一样长。
被试的任务是判断第二张卡片上的三条直线,哪一条和标准直线一样长。前两次,实验助手按照真相情况作答,到了第三组卡片出现时,实验助手开始“捣乱”:有的人做正确的判断,有的人做错误的判断。于是,真正的被试开始感到困惑,他不知道应该跟随大多数人的错误判断,还是应该做出真实的判断。
统计结果表明,全部被试中有37%选择跟随众人的错误判断,75%的被试至少有一次做出了从众的选择。
很多时候,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无论是心理学上的研究,还是历史的教训也都在告诉我们,创造文明和领导文明的,历来都是少数知识贵族。所以,当群体的潜意识行为代替了个人的有意识行为,文明赖以存在的道德就可能会被野蛮的群体瓦解掉,而那些不无道理的破坏者,就成了彻彻底底的野蛮人。
虽然说,对一种理念彻底的信仰是危险的,但是完全缺乏信仰和主张同样危险。在下面这个不无讽刺的故事中,你可以看见群体的盲从是多么可笑,而这些人,随时有可能成为决策中的大多数。
辛克站在广场旁边的马路上,对着马路对面的公寓楼喊:“黛西,黛西你在吗?我在等你。”公寓楼里没有半点反应,辛克继续喊:“黛西,我知道你在家,我是辛克,我在这里等你。”辛克继续喊了两遍,被一阵冷风呛了嗓子。
辛克咳嗽了一会儿,一位中年男子来到了他的身边。“你在喊谁,黛西吗?”辛克说:“对,我在喊黛西,她应该在家。”中年人笑了笑:“啊,一定是吵架了吧。没关系,我帮你。”中年男人对着公寓喊了一声“黛西”,回头问辛克说:“你叫辛克,对吧?”辛克点点头。
于是,中年男人喊道:“黛西,你在家吗?辛克在这里等你!”中年男人连续喊三声之后,对辛克说:“没关系,我年轻的时候也遇到过这种事儿,过去就好了。她现在还是我老婆。”随后,辛克和中年人一起喊起来:“黛西,黛西,黛西……”
过了15分钟,广场上围过来很多人,没有人来问辛克是怎么回事,但是所有人都在喊:“黛西,辛克在这里等你。”又过了15分钟,辛克的身边围满了人,所有人都向着马路对面的公寓楼喊“黛西,黛西,黛西”。辛克被人群的声音震得耳鸣。他从侧面穿过了人群,离开了广场,向邮局的方向走去。
辛克走过很远之后,依稀还能听见人群的喊声。他心想,下一次,要喊哪个名字呢?斯蒂芬妮?